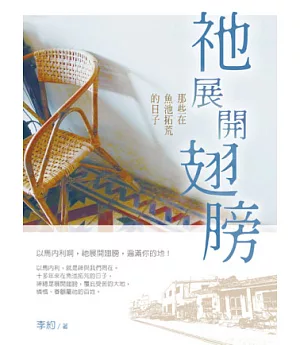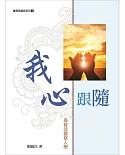幕後花絮
關於《祂展開翅膀》的二三事 余欣穎(《祂展開翅膀》責任編輯)
誰是李約?
新手編輯,很榮幸就編輯到一本好看的書,之所以說好看,是因為作者李約很會講故事。李約李姐不僅口齒伶俐,說起故事來行雲流水,流暢度渾然天成,不用口說故事時,她就用筆講故事。有些故事在我們的筆下,可能只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流水帳,但在她的筆下,卻成為一齣齣富含情感堆疊、情節鋪陳、高潮迭起、令人想知道下回如何分曉的戲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呢?有些事情,細細回想,便發現早有蛛絲馬跡可循。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李姐時,是2006年的校園文字寫作營,李姐那時候擔任小說組的講員。礙於年代久遠加上記性不好,她那時候說什麼,現在似乎忘了差不多了。但印象深刻是,這位傳道人不只會講聖經,還還可以用莫言或一些中國作家的作品,來談時代、苦難與信仰,並且把文學講得這麼平易近人,把人性洞悉得如此透徹,令人感到十分詫異而佩服。
那時,她特別舉張承志的小說《西省暗殺考》為例,清末時發生回民屠殺漢人的慘案,左宗棠被派遣,亦屠殺了不少回民,最終平定回亂。這種記史角度,一直是以漢人的觀點出發的,因而我們從小被教育平定回亂是左宗棠的豐功偉業,卻鮮少從回民的處境來思考這件歷史事件的意義,也忽略了種族間的肅清從來就不是單方面的問題,甚至在歌功頌德間,就沒有去思考不同種族間究竟何謂真正的和平共處。像《西省暗殺考》這種好的小說,就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觀點和架構,讓我們不致落入單一侷限的思考框架裡頭。信仰,非常需要好的小說來幫助我們轉換觀點,跳脫狹隘的群體觀,學習去成就更大的善。
當時,寫作營結束後,我以為就結束了。從沒想過,能夠有機會再跟這樣一位令我尊敬、充滿文學素養的傳道人相遇。
再見李約
再次和李姐碰面,是今年的一月。去年知道自己要編的第一本書,是李姐的《祂展開翅膀》,又被編輯主管告知,一月李姐會北上,屆時可以跟她吃飯,坐下來好好聊聊她的文章要怎麼成書,心中難免誠惶誠恐。見面前的那個週末,我幾乎就泡在她的文字裡,讀過她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這些文章原本是在校園雜誌專欄發表的文章,從2003年一發表,到2010年才停,一寫就是七年,反覆閱讀著她筆下那些人物生命故事的轉變:潔子、阿麗、義仔、春雨、言歡、心裡……,好像也跟著她參與了在魚池鄉村福音工作七年來的更迭變化。
見面的那天,李姐本著她喜歡分享、善於表達、真摯敞開的性格,一見面就不避諱聊起她的同工潔子生病的狀況,甚至說潔子還比她看得開,認為離世就是回到主那裡,在那裡有最好的獎賞,因而遺囑都寫好了,一切從簡,連要獻上的花也可以免了;反倒是李姐這個要照顧潔子的人,要調整服事重心,也需要轉換心情,氣色看起來比潔子還要糟,經常被人誤認為她才是病人。
見面前惡補猛讀李姐的文章,看到她和潔子十八年前,回應神的呼召,一起從同學到同工,從華神完成裝備到魚池正式開拓教會;當時魚池沒有一間教會,她們兩人彼此配搭的情誼,猶如摩西和亞倫、保羅與巴拿巴的同工關係,令我非常感動。如今潔子生病,她和李姐其實都很不好過,但聽著李姐用輕鬆詼諧的方式說著上帝給他們的劇本,以及她們一步步的調整重心、預備離開親手開拓與建造的教會、退居幕後帶領新同工等等不易的挑戰。或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漸漸發現她們離開魚池,並不是所謂的熄燈或結束營業那樣傷感;她們雖然離開,但在那裡所立下的根基,反而是個起點,讓更多的故事得以繼續發展,讓更多新的可能性得以開展,似乎也不覺得那麼沉重了。
魚池鄉的那個午後
第三次跟李姐碰面,則在三月初。
這次是我從台北下到中台灣的魚池,與李姐洽談《祂展開翅膀》的編輯事宜。會想要親自造訪一趟魚池鄉,是因為想要在這本書裡增添一些照片,讓讀者在讀李姐濃厚綿密的文字時,能有些停頓呼吸的空間。平時或多或少有在拍照,想當然也可以從舊有的圖庫中,找一些風景照或是花草照使用,但搜尋時怎麼樣就是覺得不對勁,少了一些魚池當地的味道。因而,很倉促地於前一個禮拜問李姐能否到魚池一趟。熱心的李姐雖然要照顧不停進出醫院的潔子,卻仍迅速幫我們聯絡好魚池禮拜堂的同工,讓我們當天可以借宿一晚,順利成行。
那天,聊了許多。李姐談到她從小就是嗜「字」如命的小孩,照她媽媽的說法,只要有字的東西,她幾乎就會拿來讀。直到有一天,她讀到王安憶曾經用「餵飽自己的雙眼」,來形容這樣的狀態,覺得非常貼切。大學時,她是標準的文藝青年,留著一頭長髮,喜歡穿著長裙。她笑說:「大概就是有點像齊豫那類的氣質吧!」常常泡在咖啡館裡閱讀和寫作,一寫就是八千字。
後來,喜歡俄國文學的隨行企劃同工,和李姐聊了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也談了《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裡面的信仰意涵。我則跟李姐聊起了柏格曼。
電影中的心靈交會
第二次跟李姐碰面時跟李姐提過,她所有的文章中,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來自伯格曼的啟發〉,因為我也喜歡柏格曼。記得當時李姐回我:「她寫過所有的文章,也最滿意柏格曼那篇。」但接下去就帶著不解的納悶與疑惑問我:「但是為什麼?柏格曼很老欸……。」言下之意就是,年輕如我應該不會喜歡那些過氣的老人家,或者也意味著可我太年輕,能夠體會柏格曼在電影裡頭要表達的東西嗎?
這次見面,我有機會跟她說明,為什麼我會喜歡柏格曼。雖然只是一次無意間看到《野草莓》這部電影,發現這位導演的敘事步調,很符合自己看電影能夠思考的速度,也覺得很難得有一位導演,如此認真地去思考關於生命和信仰的問題。
《野草莓》和《第七封印》同一年完成,那個時期柏格曼對信仰的思考雖未明確,還是丟出了某些石頭,泛起了些許可能性的漣漪。他的電影往往反映出他真實人生的紊亂與難解,即便柏格曼自身最終走向虛無,但透過電影,他似乎也比其他人都更認真嚴肅地去看待自己所遭遇的問題。或許若沒有電影,柏格曼的生命會是更加找不到出口。透過電影藝術,柏格曼才會是柏格曼。
不知道為什麼,結束那天的聊天後,李姐突然跟我說:「欣穎,不瞞妳說。一月我們第一次見面,看到妳時,我心中在想,這麼年輕的一位姊妹來編我的書,她會懂得我要表達的嗎?不過經過上次和這次跟妳聊天後,我很感謝主,妳懂的。」
風暴過後的那一株苗芽
年輕時作為一個愛好寫作的人,李姐說她一直記得張愛玲說過的:「出名要趁早。」
歷經魚池十八年的事奉歲月,李姐的寫作風格和動機,都變得和年輕時的寫作非常不一樣。不是為了成名,而是因為上帝要她寫下這些故事。我雖然無從讀到李姐年輕時的文字,但想起了書名會時,曾摘錄李姐的一段文字,表達這種轉變:
走過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寫作階段,經歷事奉底層小人物後,如今更加明白文學與寫作的意義:「原來苦悶的象徵並不是指那種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辭強說愁,乃是經歷過生命的破碎、掙扎、甚至走過苦難和絕望之後的心境,在烽火或者風暴過後滿目瘡痍的凌亂之下,偶然發出一絲綠意,一株小小的苗芽,那個生命的抒發,就是文學的契機。」
李姐如今半百年歲,終於要出第一本書了。而我卻想說,我真的很榮幸,可以成為李姐第一本書的編輯,也可以第一次當編輯,就編到如此精采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