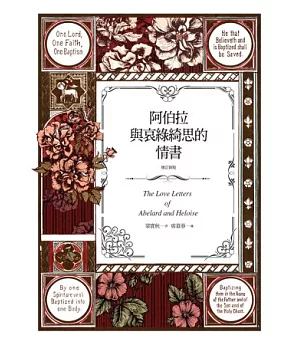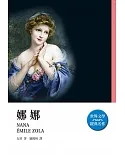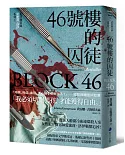序文
人生就是一個長久誘惑——關於阿伯拉與哀綠綺思∕梁實秋
我譯《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The Love Letters of Abelard and Heloise)是在民國十七年夏天,那時候我在北平家裡度暑假。原書(英譯本)為英國出版的Temple
Classics叢書之一,薄薄的一小冊,是我的朋友瞿菊農借給我看的。他說這本書有翻譯的價值。我看了之後,大受感動,遂即著手翻譯。年輕人做事有熱情,有勇氣,不一定有計畫。看到自己喜歡的書,就想把它譯出來,在譯的過程中得到快樂,譯完之後得到滿足。北平的夏季很熱,但是早晚涼。我有黎明即起的習慣,天大亮之後我就在走廊上藉著籐桌籐椅開始我的翻譯,家人都還在黑甜鄉,沒人擾我,只有枝頭小鳥吱吱叫,盆裡荷花陣陣香。一天譯幾頁,等到太陽曬滿了半個院子我便停筆。一個月後,書譯成了。
暑假過後我回到上海,《新月月刊》正需要稿件,我就把《情書》的第一函、第二函發表在《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八號(十七年十月十日出版),並且在篇末打出一條廣告:
這是八百年前的一段風流案,一個尼姑與一個和尚所寫的一束情書。古今中外的情書,沒有一部比這個更為沉痛、哀豔、悽慘、純潔、高尚。這裡面的美麗玄妙的詞句,竟成後世情人們書信中的濫調,其影響之大可知。最可貴的是,這部情書裡絕無半點輕狂,譯者認為這是一部「超凡入聖」的傑作。
廣告總不免多少有些誇張,不過這部情書確是一部使我低徊不忍釋手的作品。這部書譯出來得到許多許多同情的讀者。不久這譯本就印成了單行本,新月書店出版。廣告中引用「一束情書」四個字是有意的,因為當時坊間正有一本名為《情書一束》者相當暢銷,很多人都覺得過於輕薄庸俗,所以我譯的這部情書正好成一鮮明的對比。
其實,寫情書是稀鬆平常的事。青年男女墜入情網,誰沒有寫過情書?不過情書的成色不同。或措辭文雅,風流蘊藉,或出語粗俗,有如薛蟠。法國的羅斯當《西哈諾》一劇,其中的俊美而無文的克利斯將,無論是寫情書或說情話,都極笨拙可笑,只會不斷重複的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一語並不壞,而且是不能輕易出諸口的,多少情人在心裡燃燒很久很久才能迸出這樣的一句話,這一句話應該是有如火山之爆發,有如洪流之決口,下面還應有下文。如果只是重複著說「我愛你」便很難打動洛克桑的芳心了。所以克利斯將不能不倩詩人西哈諾為他捉刀,替他寫情書,甚至在陽臺下矇矓中替他訴衷情。情書人人會寫,寫得好的並不多見。
情書通常是在一對情人因種種關係不得把晤的時候,不得已才傳書遞簡以紙筆代喉舌。有一對情侶在結成連理之前睽別數載遠隔重洋,他們每天寫情書,事實上成為親密的日記,各自儲藏在小箱內,視同拱璧。後來在喪亂中自行付諸一炬。為什麼?因為他們不願公開給大眾看。有些人千方百計的想偷看別人的情書,也許是由於好奇,也許是出於「鬧新房」心理,也許是自己有一腔熱情而苦於沒有對象,於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總之,情書不是供大眾閱覽的,而大家愈是想看。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是被公開了的,流行了八百多年,原文是拉丁文,譯本不止一個。中古的歐洲,男女的關係不是開放的,一個僧人和一個修女互通情書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中古教會對於男女之間的愛與性視為一種罪惡,要加以很多的限制(Rattray Taylor有一本書"Sex in
History"有詳細而有趣的敘述)。我們中國佛教也是視愛為一切煩惱之源,要修行先要斬斷愛根。但是愛根豈是容易斬斷的?人之大患在於有身。有了肉身自然就有情愛,就有肉慾。僧侶修女也是人,愛根亦難斬斷。阿伯拉與哀綠綺思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們的幾封情書流傳下來,自然成為不朽的作品。
中古尚無印刷,書籍流傳端賴手鈔。鈔本難免增衍刪漏,以及其他的舛誤。所以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幾通情書是否保存了原貌,我們很難論定。至少那第一函不像是阿伯拉的手筆。很像是後來的好事者所撰作的,因為第一函概括的敘述二人相戀的經過以及悲劇的發生,似是有意給讀者一個了解全部真相的說明。有這樣一個說明當然很好,不過顯然不是本來面貌。我讀了這第一函就有一種感覺,覺得好像是《六祖壇經》的自序品第一,不必經過考證就可知道這是後人加上去的。
阿伯拉是何許人?
阿伯拉(Pierre Abelard)是中古法國哲學家,生於一○七九年,卒於一一四二年,享年六十三歲。他寫過一篇自傳〈我的災難史〉(Historia
Calamitorium)述說他的一生經過甚詳。他生於法國西北部南次附近之巴萊(Palais)。他的父親擁有騎士爵位,但是他放棄了爵位繼承權,不願將來從事軍旅生涯,而欲學習哲學,專攻邏輯。他有兩個有名的師傅;一位是洛塞林(Roscelin of Compi?gne),是一位唯名論者,以為宇宙萬物僅是虛名而已;另一位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是一位柏拉圖派實在論者,以為宇宙萬物確實存在。阿伯拉自出機杼,獨創新說,建立了一派「語文哲學」。他以為語言文字根本不足以證明宇宙萬物之真理,宇宙萬物乃是屬於物理學的範疇。於是與二師發生激辯。
阿伯拉是屬於逍遙學派的學者,在巴黎及其他各地學苑巡遊演講,闡述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一一一三或一四年間他北至洛昂,在安塞姆(Anselm)門下研習神學,安塞姆乃當時聖經學者的領袖。可是不久他對安塞姆就感到強烈的不滿,以為他所說的盡屬空談,遂即南返巴黎。他公開設帳教學,同時為巴黎大教堂一位教士福爾伯特(Canon
Fulbert)的年輕姪女哀綠綺思作私人教師。不久,師生發生戀情,進而有了更親密的關係,生了一個兒子。他們給他命名為阿斯楚拉伯(Astrolabe)。隨後他們就祕密舉行婚禮。為躲避為叔父發覺而大發雷霆,哀綠綺思退隱在巴黎郊外之阿干特意修道院。福爾伯特對於阿伯拉不稍寬假,賄買兇手將阿伯拉實行閹割以為報復。阿伯拉受此奇恥大辱,入巴黎附近之聖丹尼斯寺院為僧,同時不甘坐視哀綠綺思落入他人之手,強使她在阿干特意修道院捨身為尼。
阿伯拉在聖丹尼斯擴大其對神學之研究,並且不斷的批評其同修的僧侶之生活方式。他精讀聖經與教會神父之著作,引錄其中的文句成集,好像基督教會的理論頗多矛盾之處。他乃編輯他所發現的資料為一集,題曰"Sic et
Non"(是與否),寫了一篇序,以邏輯學家與語文學家的身分制訂一些基本規則,根據這些規則學者們可以解釋若干顯然矛盾的意義,並且也可以分辨好多世紀以來使用的文字之不同的意義。他也寫了他的《神學》(Theologia)初稿,但於一一二一年蘇瓦松會議中被斥為異端,並遭焚燬處分。阿伯拉對於上帝以及三位一體的神祕性之辯證的解釋被認為是錯誤的,他一度被安置在聖美達寺院予以軟禁。他回到聖丹尼斯的時候,他又把他的「是與否」的方法,施用在這寺院保護神的課題上;他辯稱駐高盧傳道殉教的巴黎聖丹尼斯,並不是被聖保羅所改變信仰的那位雅典的丹尼斯(一稱最高法官戴奧尼索斯)。聖丹尼斯的僧眾以為這對於傳統的主張之批評乃是對全國的汙辱;為了避免被召至法國國王面前受訊,阿伯拉從寺院逃走,尋求香檳的提歐拔特伯爵領邑的庇護。他在那裡過孤寂隱逸的生活,但是生徒追隨不捨,強他恢復哲學講授。他一面講授人間的學問,一面執行僧人的任務,頗為當時其他宗教人士所不滿,阿伯拉乃計議徹底逃離到基督教領域之外。一一二五年,他被推舉為遙遠的布萊頓的聖吉爾達斯.德.魯斯修道院院長,他接受了。在那裡他與當地人士的關係不久也惡化了,幾度幾乎有了性命之憂,他回到法國。
這時節哀綠綺思主持一個新建立的女尼組織,名為「聖靈會」(Paraclete)。阿伯拉成為這個新團體的寺長,他提供了一套女尼的生活規律及其理由;他特別強調文藝研究的重要性。他也提供了他自己編撰的聖歌集,在一一三○年代初期他和哀綠綺思把他們的情書和宗教性的信札編為一集。
一一三五年左右阿伯拉到巴黎郊外的聖任內微夫山去講學,同時在精力奮發聲名大著之中從事寫作。他修訂了他的《神學》,分析三位一體說信仰的來源,並且稱讚古代異教哲學家們之優點,以及他們之利用理性發現了許多基督教所啟示的基本教義。他又寫了一部書,名為《倫理學》(Ethica),又名《認識你自己》(Scito te
ipsum),乃一短篇傑作,分析罪惡的觀念,獲到一徹底的結論,在上帝的眼裡人的行為並不能使人成為較善或較惡,因為行為本身既非善亦非惡。在上帝心目中重要的是人的意念;罪惡不是做出來的什麼事(根本不是res——物),實乃人心對明知是錯誤的事之許可。阿伯拉又寫了一部《一哲學家,一猶太人,一基督徒之對話錄》(Dialogus inter Philosophum, Judaeum et
Christianum),一部《聖保羅致羅馬人函之評論》(Expositio in Epistolam ad Romanos),縷述基督一生之意義,僅在於以身作則,誘導世人去愛。
在聖任內微夫山上,阿伯拉吸引來大批的生徒,其中很多位後來成為名人,例如英國的人文主義者騷茲伯來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不過他也引起很多人甚深的敵意,因為他批評了其他的大師,而且他顯然修改了基督教神學之傳統的教義。在巴黎市內,有影響力的聖約克多寺院的院長對他的主張極不以為然,在其他地方,則有聖提愛利的威廉,本是阿伯拉仰慕者,現在爭取到當時基督教區域中最有勢力的人物克賴福的伯納德的擁護。一一四○年在森斯召開的會議,阿伯拉受到嚴重的譴責,這項譴責不久為教宗英納森二世所確認。他於是退隱於柏根底的克魯內大寺院,在院長可敬的彼德疏通之下,他和克賴福的伯納德言歸於好,旋即從教學中退休出來。他如今老病交加,過清苦的僧人生活。他死於附近的聖瑪塞爾小修道院,大概是在一一四二年。他的屍體最初是送到聖靈會,現在是和哀綠綺思並葬於巴黎之拉舍斯禮拜堂墓園中。據在他死後所撰的墓銘,阿伯拉被某些同時人物認為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與教師之一。
以上所述是譯自大英百科全書,雖然簡略,可使我們約略了然於阿伯拉的生平。他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學者,一個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且是熱情洋溢的人。
哀綠綺思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可惜我們所知不多。她生於一一○一年,卒於一一六四年,享年六十三歲。據說是"not lowest in beauty, but in literary culture
highest."(在美貌方面不算最差,但在文藝修養方面實在極高。)這涵義是說她雖非怎樣出眾的美女,卻是曠世的才女。事實上哀綠綺思是才貌雙全的。二人初遇時,哀綠綺思年方十九,正是豆蔻年華,而阿伯拉已是三十七歲,相差十八歲。但是年齡不能限制愛情的發生。師生相戀,不是一般人所能容忍的。但是相戀出於真情,名分不足以成為障礙。男女相悅,私下裡生了一個兒子,與禮法是絕對的不合,但是並不違反人性,人情所不免。八百多年前的風流案,至今為人所豔稱,兩人合葬的墓地,至今為人所憑弔。主要的緣故就是他們的情書真摯動人。
「情書」裡警句很多,試摘數則如下。
「上天懲罰我,一方面既不准我滿足我的慾望,一方面又使得我的有罪的慾望燃燒得狂熾。」性慾的強弱,人各不同。阿伯拉一見哀綠綺思,便「終日冥想,方寸紊亂,感情猛烈得不容節制。」這時候阿伯拉已是三十七歲的人,學成名就,不是情竇初開的奇男子,他的感情已壓抑了很久,一旦遇到適宜的對象,便一發而不可收拾。哲學不足以主宰情感。阿伯拉並不是早熟,他的一往情深是正常的。「愛情是不能隱匿的;一句話,一個神情,即使一刻的寂靜,都足以表示愛情。」他們「兩人私會,情意綿綿。」可以理解,值得同情。
「你敢說婚姻一定不是愛情的墳墓嗎?」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這句話不知誰造出的一句俏皮話?須知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乃是人間無可比擬的幸福。從外表看,婚後的感情易趨於淡薄,實際上婚後的愛乃是另一種愛,洗去了浪漫的色彩,加深了牉合的享受,就如同花開之後結果一般的自然。婚姻是戀愛的完成,不是墳墓。婚姻通常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死而後已。
「假如人間世上真有所謂幸福,我敢信那必是兩個自由戀愛的人的結合。」人間最大幸福是「如願以償」。《老殘遊記》第二十回最後兩行是一副聯語──「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真是善頌善禱。兩情相悅,以至成為眷屬,便是幸福,而且是絕大多數的人所能得到的幸福。不一定才子佳人才算是匹配良緣,世界上沒有那麼多的才子和佳人。也有以自由戀愛始而以仳離終的怨偶,那究竟是例外。如願便是滿足,滿足即是幸福。
「尼庵啊!戒誓啊!我在你們的嚴厲的紀律之下還沒有失掉我的人性!……我的心沒有因為幽禁而變硬,我還是不能忘情。」忘情談何容易,太上才能忘情。佛家所謂「重離煩惱之家,再割塵勞之網」正是同一道理。出家要有兩層手續,剃度受戒是一層,究竟是形式,真能割斷愛根,一心向上,那才是真正的出家。基督教有所謂「堅信禮」,也是給修道者一個機會,在一定期間內如不能堅持仍有退出還俗的選擇。哀綠綺思最初身在修道院而心未忘情,表示她的信心未堅尚未達到較高的境界。
「從來沒有愛過的人,我嫉妒他們的幸福。」這是在戀愛經驗中遭受挫折打擊的人之憤慨語。從來沒愛過,當然就沒有因愛而惹起的煩惱。我們宋朝詞人晏殊所謂的「無情不似多情苦」,也正是同樣的感喟。但是人根本有情,若是從未愛過,在人生經驗上乃一大缺憾,未必是福。因吃東西而哽咽的人會羨慕從來不吃東西的人嗎?
「人生就是一個長久誘惑。」這是一位聖徒說的話。「除了誘惑之外,我什麼都能抵抗。」這是王爾德代表一切凡人所說的一句俏皮話。人生是一連串的不斷的誘惑。誘惑大概是來自外界,其實也常起自內心。佛家所謂的「三毒」貪瞋癡,愛就是屬於癡。愛根不除,便不能抵抗誘惑。阿伯拉要求哀綠綺思不要再愛他,要她全心全意的去愛上帝,要她截斷愛根,不再回憶過去的人間的歡樂,作一個真的基督徒的懺悔的榜樣,──這才是超凡入聖,由人的境界昇入宗教的境界。他們兩個互相勉勵,完成了他們的至高純潔的志願,然而在過程中也是十分悽慘的人間悲劇!阿伯拉對哀綠綺思最後的囑咐是:「你已脫離塵世,那裡還有什麼配使你留戀?永遠張眼望著上帝,你的殘生已經獻奉了他。」這樣的打發一個人的殘生,是悲劇,也是解脫。
我在「譯後記」說George Moore有他的譯本,我說錯了。他沒有譯本,他的作品是一部小說。《情書》之較新的英譯本是一九二五年的C. K. Scott Moncrieff的,和一九四七年的,和一九四七年J. T. Muckle的。
──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