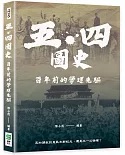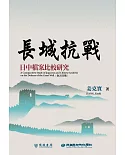自序
這本書是一個貨郎擔,前面的擔子裝的是文革,後面的擔子裝的是評論。前者的寫作在近十年間,最早寫的是毛澤東的新人;最近寫的是江青的筆名。後者的寫作時間跨度更長,讀哈維爾的感想寫於上世紀末,《評梁啟超傳》則是前兩個月剛完成的。評論之中,還夾雜了幾篇述往憶舊的小文。活了一大把年紀,總有些值得說說的人和事。王年一的齎志而歿,劉向宏的抱恨長逝,北京四中的經歷,北京大學的見聞,老鄉給我的回扣,學界的「豬窩化」……林林總總,形形色色。對於大陸的把關人來說,統統是劣品私貨。
私貨見不得天日,在此岸無法問世。劣品不合規格,把關人要刪削斧正。刀斧手來自各類官媒,而號稱最敢言的《南方週末》則君子動嘴不動手。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南周找人為《梁啟超傳》寫書評,知我在寫,大悅,來電索後告余:「大文確實是一篇佳作,神完氣足。只是,大文的尺度太寬了,我們這裡發表起來有困難,特別是十七加一大前後。我建議,您把與現實聯繫的一些話,都拿掉,然後我們再試試。如果此稿直接拿給領導去審,肯定被直接槍斃,那就無可挽回了。」
如此用心,可謂良苦。而「十七加一大」的自撰新詞更讓人感到形勢之肅殺。莞爾感慨之餘,揮淚自刪,從五千字刪到二千七,原標題《改良與革命》改為《多變善變梁啟超》。自以為如此痛下殺手,總可以通過。沒想到,主編先生在一番小小的躊躇之後,還是把它斃了。理由是「影射現實」。證據是文中引用了龍應台的一段話:「一百年之後我仍受梁啟超的文章感動,難道不是因為,儘管時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啟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啟超的呼喊?我自以為最鋒利的筆刀,自以為最真誠的反抗,哪一樣不是前人的重複?」
為什麼主編先生從中看到了「影射」,是因為,他從梁啟超時代的皇權想到了當今的「黨天下」,想到了結束專制,落實憲政,實施民主的艱難。他知道這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存逆亡,但是,為了安全地渡過十八大前後這一晦暗不明的敏感期,還是把此文槍斃了為好。他的選擇有相當的合理性,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內,在他的位置上都可能這樣做。後極權時代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犬儒的普遍化。阿倫特說,即使是超級極權也無法奪去人們的思想,因此,思想是反抗專制的最後的武器。(大意)阿倫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識別犬儒的方法——判斷一個人是否犬儒,以及犬儒的程度如何,只消看看他對專制的態度。我們不妨以莫言為例。
前不久,莫言有一個著名的「答記者問」——
南周記者:你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哥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面來了國王和大批貴族,貝多芬昂道挺胸,從貴族中挺身而過。哥德退到路邊,畢恭畢敬地脫帽行禮。你說年輕的時候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意識到,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哥德那樣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莫言:……隨著年齡的增長,對這個問題就有新的理解:當面對國王的儀仗揚長而去沒有任何風險且會贏得公眾鼓掌時,這樣做其實並不需要多少勇氣,而鞠躬致敬,會被萬人詬病,而且被拿來和貝多芬比較,這倒需要點勇氣。但他的教養,讓他跟大多數百姓一樣,站在路邊脫帽致敬。因為國王的儀仗隊不僅代表權勢,也代表很多複雜的東西,比如禮儀,比如國家的尊嚴。和許多象徵性的東西。英國王子結婚,戴安娜葬禮,萬人空巷,那麼多人看,你能說,路邊的觀眾全都是卑劣,沒有骨氣嗎?你往女皇的馬車上扔兩個臭雞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氣嗎?所以當挑戰、蔑視、辱侮權貴沒有風險而且會贏得喝彩的時候,這樣做其實是說明不了什麼的。而跟大多數老百姓一樣,尊重世俗禮儀,是正常的。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當作普通老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貝多芬的行為,就感到可笑。(2012-10-18)
莫言這番言論的核心思想是「服從專制」,其論證方法是混淆是非,偷換概念。眾所周知,貝多芬是反封建反專制的音樂家,他在權貴面前昂首挺胸,不僅僅是由於個性高傲,還源於其骨子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莫言只看到了貝多芬這樣做「沒有任何風險」,而沒有看到這種思想性格讓貝多芬付出的沉重代價——貝多芬五十七歲時在貧病之中死去。生無體制給予的富貴,死無來自國家的哀榮。
被莫言視為有著真正勇氣的哥德終生寄身於體制,從走出校門到八十二歲辭世,他大部分時間都是魏瑪公國的官員,從樞密公使的參贊到樞密顧問,從公國持政到文藝大臣。儘管哥德有人本思想,有文學成就,但是,這並不妨礙他為權貴服務。事實上,他本人也是權貴之一。看到國王貴族,這位帝國議員的兒子自然會畢恭畢敬。其恭敬的,除了莫言所說的禮儀,恐怕更多的是權勢,是體制,是社會等級。
權勢喜歡才子,更喜歡順民,哥德兼顧這兩種身分,自然更受恩寵。大公兩次送他帶花園的房子,後一幢房產在他死後成了國家博物館。哥德的低眉順眼換取了豐厚的回報:生有體制賜予的名利富貴,死有隆重的葬禮和官史的芳名。
莫言把貝多芬對權貴的蔑視,等同於向女王的馬車上扔雞蛋,不但污蔑了貝多芬,而且汙損了所有反抗專制的前輩後生。誰都知道,反抗專制與暴民行為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莫言把它們混為一談,無非是想告訴人們一個莫氏的理念:「反抗專制未必高尚,臣服專制未必可恥。」以此來為他手抄《講話》尋找臺階。
莫言說:「因為國王的儀仗隊不僅代表權勢,也代表很多複雜的東西,比如禮儀,比如國家的尊嚴和許多象徵性的東西。」這種說法忘記了一個基本前提,國王代表的是什麼國家?儀仗隊代表的是什麼政體?英國人在爭看英國王子結婚,戴安娜葬禮的同時,可以對他們品頭論足。而曾幾何時,中國人只要議論一下江青、林彪、毛澤東就犯了「惡攻」罪而生命不保。這兩個政體哪個值得尊重?
不用說,代表了民主的東西會贏得人民的尊重;而專制極權的象徵物則無法令人起敬,所以,李白痛恨「摧眉折腰事權貴」,傅山拒絕清廷的三邀四請,乾隆南巡到了金陵,吳敬梓「企腳高臥向栩床」;而章太炎則把袁世凱發的勳章,當成了扇墮兒。
身為作協副主席,享受著局級待遇的莫言,努力要把自己混同於「普遍老百姓」,無非是想用這個招牌掩飾自己對專制的態度——你看,老百姓都尊重世俗禮儀——向專制鞠躬,我為專制服務,為文網歌唱,不是很正常嗎?他忘了,自古以來,反抗專制的造反者都是「普遍老百姓」。
如果說,莫言是裝糊塗,那麼,龍應台則是真糊塗。記者問她:「在西方媒體看來,政治標準應是授獎的一個重要指標,在你看來是否應該如此?」
她回答:「我覺得挺煩的,我們到底有沒有單純的能力——就用文學來看文學?」
或許,龍應台看到南周主編的「影射說」會多少明白一點,能否「用文學來看文學」不在能力,而在條件——當今的大陸,跟當年的臺灣一樣,凡是與意識形態沾邊的,無論是文藝還是社科,都離不開政治。當年深受臺灣一黨專制之苦的龍應台,一旦當上文化局長,就去力挺為一黨專制說話的莫言。你說她是不是糊塗?
專制時代,說話著文離不開政治,這個道理古人早就懂。所以,嵇康跑到樹下,光著膀子打鐵。阮籍「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劉伶攜酒登車,一邊喝酒,一邊吩咐家人:「死便埋我!」
我小的時候,奶奶就說我眼大心肥。人生短暫,能把一件事做好,就大不易。而我卻像八爪魚似地什么都抓,又是電影研究,又是文革史、又是社會語言學、又是思想評論,又要述舊懷人,稍微有點空,還要寫劇本、小說。這個貨郎擔雖說是只有文革和評論這兩捆草,但也足以累垮貪吃的小毛驢。眼大心肥跟眼高手低是親兄弟,選文入集又敝帚自珍,免不了心慈手軟。你說,挑著這個貨郎擔,能不惴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