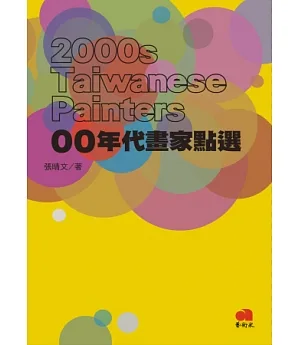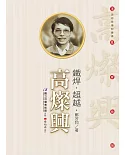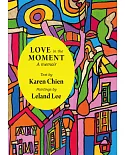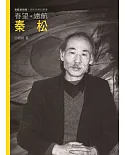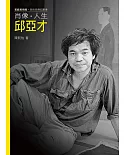自序 ∕ 張晴文
這兩年多以來,因為《藝術家》雜誌的專欄,讓我有更多機會造訪藝術家的工作室,以採訪之名與這些崛起於2000年代左右的新畫家們談創作、聊他們關心的事。儘管許多藝術家都是熟識的,或為同學、朋友,也或許緣於藝評生產的需求而曾經深談;我們經常在畫廊或任何展覽的場合裡偶遇,然而大部分的時間裡,彼此並不見得有多少機會單刀直入地談自己的作品。
許多人曾在受訪結束後客氣地表示歉意,對於談自己創作這類事情真的滿不在行。然而,我想他們之中會有更多人同意,我不是一個稱職的訪談者。帶著目的前來的談話容易讓人緊張,不幸的是那個緊張的人偏偏是我,訪談之中偶爾因為陌生而陷入尷尬的沉默,或者莫名地語無倫次。誠實地說,短短幾個小時的相談,我也從來沒指望能聽到藝術家條理分明地分析自我和創作,甚至,過於熟練的表達也會讓我存疑。我只是想要聊天而已。不善言語如我,其實更希望自己能夠隱形,只需靜靜看著他們如何生活,又如何創作。談話之餘,藝術家們工作的環境、安排工作空間的方式、感興趣的事物、書架上的書、豢養的寵物、聽的音樂,甚至是日常用品,也成為各種微小的線索,讓我對於創造出眼前畫作的那個靈魂,有更多的認識。
我所接觸的這群畫家們皆出身學院,大多在2000年左右以藝壇新秀之姿崛起。在受訪的藝術家群裡,年紀最長、出道最早的賴九岑,其實在1990年代已經有許多發表,直至2002年從北藝大的美創所碩士班畢業,隔年獲得台北獎,大約是一個經歷上的轉捩(儘管畫家的經歷和創作的狀態不見得有太大關係)。做為一位自持的畫家,他的工作空間是我採訪過的畫家裡最擠迫的;而我也經常從更年輕一些的畫家口中,聽見對其作品的欣賞之情。隨著時間過去,這群「年輕藝術家」漸漸不適用於這個籠統且無甚意義的稱謂,他們大多經歷了2007年前後台灣藝術市場那一波躁動的高峰,當然也經歷了熱潮退散後的莫名虛無。他們是台灣美術史上少見的,在校園裡和畫商打交道的一代,更活在一個媒體和行銷高度發展的時空裡。甚至,在他們養成專業的過程中,繪畫可能被與老派、不合時宜畫上等號。就像王璽安曾經在訪談裡提到的,繪畫大概是這個年代裡最無法表現聰明的一種創作方式。而我好奇的是,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畫家前仆後繼地投入繪畫者的行列,站在深厚的歷史面前試圖做些什麼?多年以來,在爭奇鬥豔的畢業展或者大型展覽之中,依然有不少繪畫作品抓住了觀眾的目光,甚至成為展場裡少數經得起一看再看而看不膩的作品。
這些出生於1970年代以後的畫家,藉著畫畫探索各種既古老又當代的問題。最根本的,關於畫家的身分、畫家及其媒體之間的關係,在他們的筆下產生各種不同的討論和實踐。論成就風格,對於尚未步入中年,甚至未滿三十的藝術家來說是否言之過早?看來未必,並且,就藝術環境而言這是確確實實存在的焦慮。當今的學院體制,也已經能夠訓練出高度自覺且台風穩健的畫家。有些風格來自深刻的文化認同,對於自我歷史或文化傳統的認識、信念,在作品裡展現出一種屬於這一代人的詮釋方式。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畫家將興趣放在各種造形的問題上。當代繪畫和影像之間的關係,在數位發達的時代顯得複雜而有趣,也有不少畫家在創作裡展現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探索。
更多時候,畫家在作品裡映射的是關於自我的反省或感受。在某些疑似自傳性的創作裡,畫家以隱晦的語言剖析自身,或許甜美,或許哀傷,這類作品可以是屬於個人的微小敘事,也可以做為當代社會或生活的情調反映。
莎拉.桑頓(Sarah Thornton)在《藝術世界的七天》(中譯《藝術市場探密》)裡寫道,當代藝術已成為無神論者的某種另類宗教。她引用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話說:「繪畫,或者是所有的藝術形式,現在已完全成為一種世人賴以分散自我注意的遊戲,而藝術家要搞出名堂,必須真正深化這項遊戲。」或許繪畫至今還需要向觀眾索求多些駐足時間,而00年代的台灣畫家們也持續追索著繪畫的可能性和出路。在此同時,我樂於做一個和藝術家們成長於同一時代的寫作者,在對談和寫作之間留下關於台灣當代繪畫的片刻紀錄。
然而,在造訪了這麼多畫家之後,我仍未能清楚說出他們為何而畫。但我知道,對他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解決的疑惑值得用這種孤獨的方式慢慢領悟。我對於這一代畫家的探訪和好奇,也將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