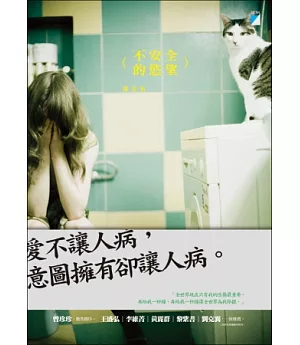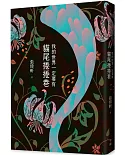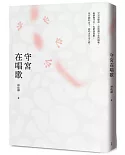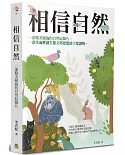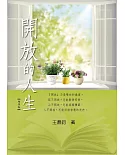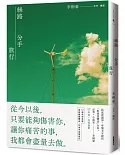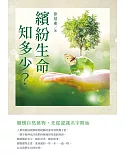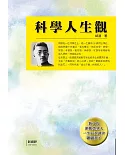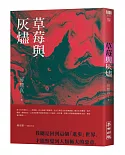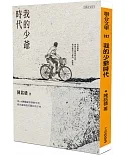【推薦序】
溫柔而勇敢的出走
曾珍珍(國立東華大學英文系教授)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一生未嘗將旅遊書寫結集出版,因為她極少動筆寫遊記;出國旅遊似乎並非她的嗜好。終其一生,她未曾涉足美洲大陸。歐洲之外的地方,僅於一九○六年與畫家姊姊結伴到過位於歐亞交界的伊斯坦堡。後來,這座鄂圖曼帝國的古都,為她的傳奇經典《歐蘭朵》主角由男變女的關鍵情節,提供了奇幻的場景。一九九七年,英國知名的旅遊作家珍.莫蕾絲(Jan Morris,
1926-)從吳爾芙的日記和書信中擷取她在英國境內和異域他方的旅行見聞,輯成《與吳爾芙同遊》(Travels with Virginia Woolf)一書。在導言裡,莫蕾絲不忘提點讀者,吳爾芙在《達洛威夫人》(Mrs. Dalloway)這本小說中描寫倫敦街頭所呈現的敏銳、獨到「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一樣飽滿、淋漓地流貫在她抒寫異地他鄉的散筆紀實中。拋開不可避免的族群偏見和階級意識不論,她別具一格的「旅人凝視」(the tourist
gaze),與男性旅遊書寫不同調性,並不著眼於再現觀光景點的地貌與歷史,一種客觀知識的鋪陳與導覽,也不作興涉入政治評論。反之,日記與書信的私密書寫形式,容許她肆意捕捉個人感官知覺觸景興發的瞬間,筆端流露的是旅次途中靈光乍現的驚喜與歡愉。「幾乎不具形體;近乎透明;像住在一隻水母裡,憑綠光照明。」--五十六歲的吳爾芙這樣描寫雨中的蘇格蘭司凱伊島(The Island of
Skye),其實也寫出了自己官能開放、在水中漂浮的靈體。感應於空間中,吳爾芙引物連類,意到筆隨,全人與景色交融,泯除物我界分的詠物書寫,活脫體現了海德格所推崇的空間詩學--無論在地或他方,以知性體認與尊重物性繽紛、差異之同時,也無礙於感性水漾般的詩意居住。
葉佳怡從台大外文系畢業後,移居花蓮,就讀於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不安全的慾望》這本或許會被歸類為旅遊書寫的散文集,具體展現了她在創英所以愛蜜莉.狄瑾蓀(Emily Dickinson,
1830-1886)和吳爾芙為師,所習得的空間詩學。吳爾芙點撥她隨地水漾般「詩意居住」的訣竅,而狄瑾蓀以山海地景、花鳥蜂蝶等象徵隱喻女性身體,寫活慾望穿越內外空間無邊無界的流動,開啟了女性身體前衛書寫之先河。她的靈視出入於超世達觀與微觀入神之間,無論觀物、內省或知人論世,敏於呈現正反觀點的辯詰與並立,對葉佳怡遊走在此地、他方多向度的視角移動有所啟迪。倘若如她在〈後記〉裡的自述,是因迷戀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的在地書寫《伊斯坦堡》吸引她前往旅遊,希望藉此讓她「身邊的此地立體起來」,那麼,置身在他方「瘋狂吞吃」的葉佳怡,她的官能感應、美學與倫理取捨、想像的衍生,以及思緒與文字律動的洗練應節,其實受惠於狄瑾蓀和吳爾芙的先導居多。〈底下有一隻野貓〉這篇因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陡峭坡地地貌引發的奇文,從如何描述野貓正確的位置(涉及視角的隨境靈動)談及在性別倫理脫序、斜仄的世界裡,人們如何藉由酒趣調理人情的疏離與聚合,可說已把兩位先驅的女性空間詩學變奏、引渡入後現代都會書寫中了。思想視角向著全球化世界多元開放,更讓她除了內省之外,也觀照到了不同處境的旅人身影:穿著連帽衫的黎巴嫩男子、隨地做筆記的北美背包客、逃亡的新疆維吾爾青年。就這個面向看,葉佳怡選擇出走他方(她的他方包括了花蓮和伊斯坦堡),學習解構成見,秉持「不安全的慾望」,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對各類空間的強蠻同化,提出捍衛差異的文化反思,她已儼然用自己的女性書寫形塑出了克里絲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所謂的新知識份子∕異議者的形象。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流亡的時代。如何能避免陷入成見的泥沼中,除非成為自己的國家、語言、性別和身份的異鄉人?若無某種形式的放逐,寫作是不可能的。」一九七七年保加利亞流亡作家和學者克里絲蒂娃以法文在Tel Quel
雜誌發表了革命性的社論〈一種新型態的知識份子:異議者〉。她認為放逐的本身已經是一種異議的形式。放逐讓人切斷任何連結,包括對特定宗教的依附(宗教不同於信仰,依祈克果的看法,如果信仰是烘焙過的茶葉,宗教只不過是用擱在抽屜內包有已沖泡過三次茶葉的紙旁的那張紙沖泡出來的茶),不再相信所謂的人生有一種「先人」可擔保的意義。如果意義存在於放逐中,它就需要不斷地隨著地域與論述的轉化生發與毀滅。放逐是當著「先人」的面勇敢求生,與死亡打賭,這才是活著的意義,頑強地拒絕向死的律法投降。此外,她認為所有勇於用身體思考,挑戰父權象徵次序的女性,是當代異議者的典範。應該就是類似的體悟讓葉佳怡將自己出走他方的書寫取名為《不安全的慾望》吧,且用溯溪時喜歡爭先冒險往溪心一躍,與死亡打賭,作為詮解:「亟於證明自己勇敢、不計後果,而且還能冒險犯難並進而發現新世界。新世界是個模糊的詞彙,慾望卻熱切。然而當時的我還不明白:後果冷冽,卻最接近真實,如果不懂得應對這些因為冒險而帶來的損傷,人無法接近任何溫暖。」
葉佳怡是個有慧根的寫作者,既擅長觀察,又敏於思辨。將花蓮壽豐台十一線丙謔稱為「出賣路」,她用貼近群眾的白話、年輕人率真的口吻,舉重若輕,寫出近乎異議哲學家的靈魂。而寫伊斯坦堡清真寺外頸子掛著念珠的貓,寫當包頭巾的女子從身旁走過,從她的髮絲弧度與香氣意識到神祕的慾力,她的筆致,像吳爾芙般,帶給我們與她同遊的感官歡愉。文字自然、清新,情緒與思想的轉折隱然有著音樂性的律動,許多片段因此像散文詩一般耐讀而發人深省。這本散文集可說見證了台灣文壇一位年輕知識份子∕異議者溫柔而勇敢的誕生!轉益多師是吾師,葉佳怡生活於後現代的台灣,用高度原創的吸收與涵納,為自己在狄瑾蓀、吳爾芙、克里絲蒂娃所開拓出的世界女性書寫系譜中,暫時找到了身分座標,期許她繼續出走,在下一本書中帶我們闖蕩更遠、更真實的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