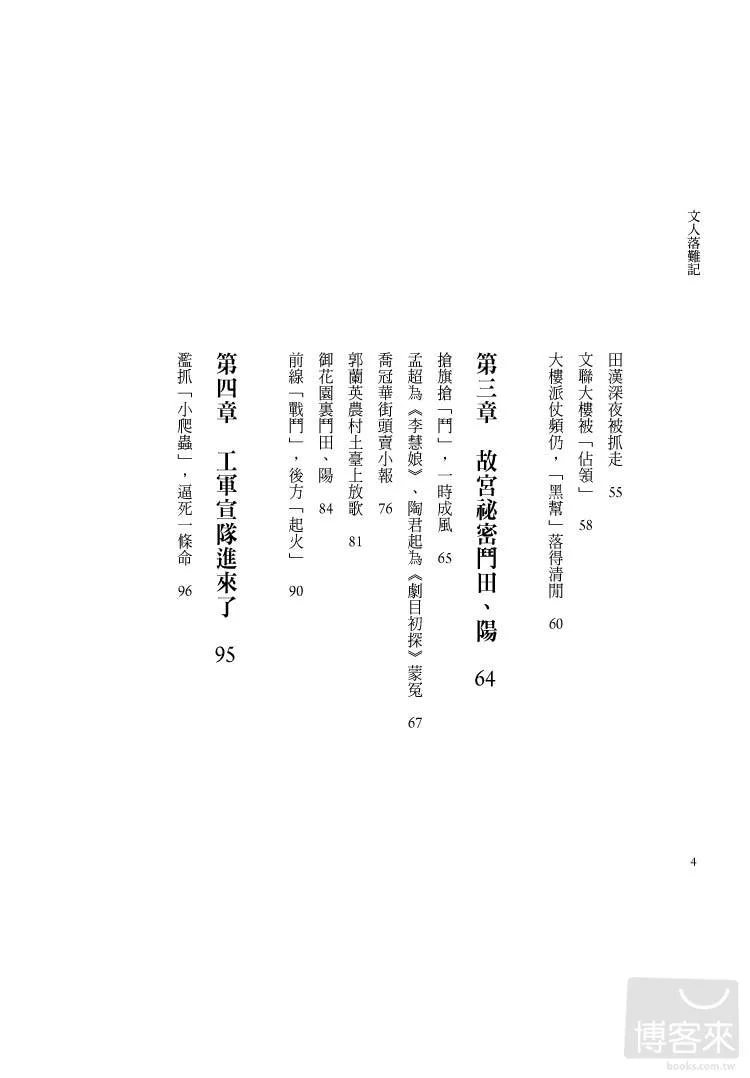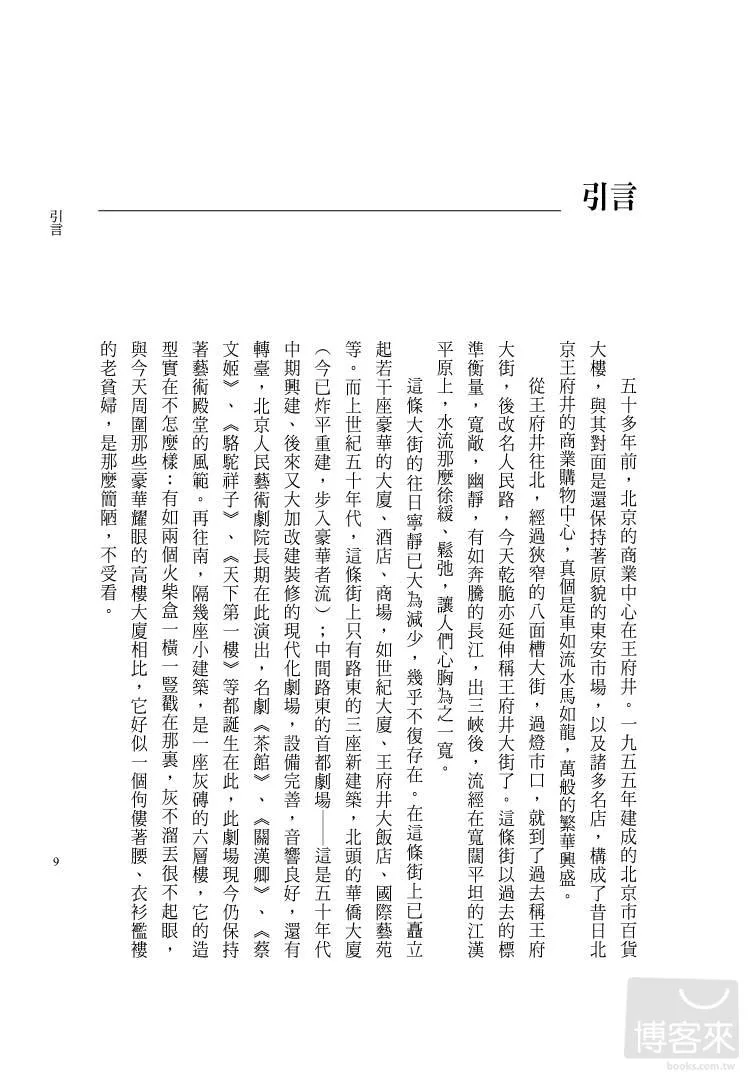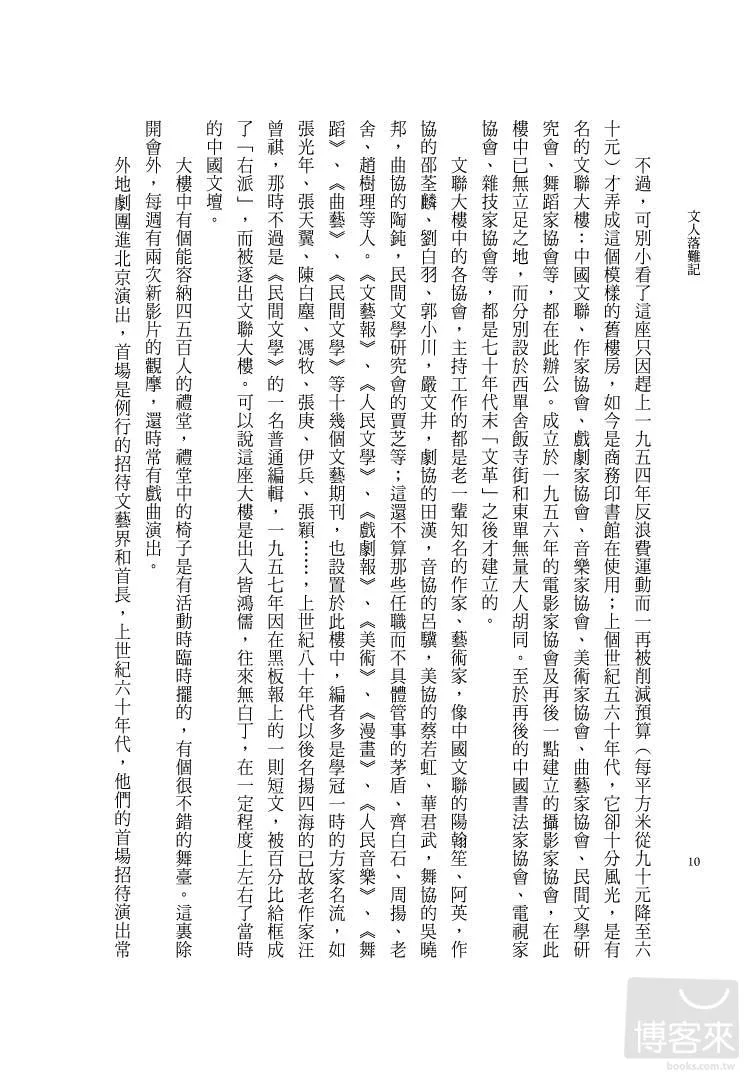引言
五十多年前,北京的商業中心在王府井。一九五五年建成的北京市百貨大樓,與其對面是還保持著原貌的東安市場,以及諸多名店,構成了昔日北京王府井的商業購物中心,真個是車如流水馬如龍,萬般的繁華興盛。
從王府井往北,經過狹窄的八面槽大街,過燈市口,就到了過去稱王府大街,後改名人民路,今天乾脆亦延伸稱王府井大街了。這條街以過去的標準衡量,寬敞,幽靜,有如奔騰的長江,出三峽後,流經在寬闊平坦的江漢平原上,水流那麼徐緩、鬆弛,讓人們心胸為之一寬。
這條大街的往日寧靜已大為減少,幾乎不復存在。在這條街上已矗立起若干座豪華的大廈、酒店、商場,如世紀大廈、王府井大飯店、國際藝苑等。而上世紀五十年代,這條街上只有路東的三座新建築,北頭的華僑大廈(今已炸平重建,步入豪華者流);中間路東的首都劇場--這是五十年代中期興建、後來又大加改建裝修的現代化劇場,設備完善,音響良好,還有轉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長期在此演出,名劇《茶館》、《關漢卿》、《蔡文姬》、《駱駝祥子》、《天下第一樓》等都誕生在此,此劇場現今仍保持著藝術殿堂的風範。再往南,隔幾座小建築,是一座灰磚的六層樓,它的造型實在不怎麼樣:有如兩個火柴盒一橫一豎戳在那裡,灰不溜丟很不起眼,與今天周圍那些豪華耀眼的高樓大廈相比,它好似一個佝僂著腰、衣衫襤褸的老貧婦,是那麼簡陋,不受看。
不過,可別小看了這座只因趕上一九五四年反浪費運動而一再被削減預算(每平方米從九十元降至六十元)才弄成這個模樣的舊樓房,如今是商務印書館在使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卻十分風光,是有名的文聯大樓:中國文聯、作家協會、戲劇家協會、音樂家協會、美術家協會、曲藝家協會、民間文學研究會、舞蹈家協會等,都在此辦公。成立於一九五六年的電影家協會及再後一點建立的攝影家協會,在此樓中已無立足之地,而分別設於西單舍飯寺街和東單無量大人胡同。至於再後的中國書法家協會、電視家協會、雜技家協會等,都是七十年代末「文革」之後才建立的。
文聯大樓中的各協會,主持工作的都是老一輩知名的作家、藝術家,像中國文聯的陽翰笙、阿英,作協的邵荃麟、劉白羽、郭小川,嚴文井,劇協的田漢,音協的呂驥,美協的蔡若虹、華君武,舞協的吳曉邦,曲協的陶鈍,民間文學研究會的賈芝等;這還不算那些任職而不具體管事的茅盾、齊白石、周揚、老舍、趙樹理等人。《文藝報》、《人民文學》、《戲劇報》、《美術》、《漫畫》、《人民音樂》、《舞蹈》、《曲藝》、《民間文學》等十幾個文藝期刊,也設置於此樓中,編者多是學冠一時的方家名流,如張光年、張天翼、陳白塵、馮牧、張庚、伊兵、張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名揚四海的已故老作家汪曾祺,那時不過是《民間文學》的一名普通編輯,一九五七年因在黑板報上的一則短文,被百分比給框成了「右派」,而被逐出文聯大樓。可以說這座大樓是出入皆鴻儒,往來無白丁,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當時的中國文壇。
大樓中有個能容納四五百人的禮堂,禮堂中的椅子是有活動時臨時擺的,有個很不錯的舞臺。這裡除開會外,每週有兩次新影片的觀摩,還時常有戲曲演出。
外地劇團進北京演出,首場是例行的招待文藝界和首長,上世紀六十年代,他們的首場招待演出常在此舉行,而不在他們正式演出時的劇場。一九六十年秋,關肅霜率雲南京劇院首次進京,頭一場《白蛇傳》就是在文聯禮堂演出的。梅蘭芳、田漢、夏衍、歐陽予倩等文藝界知名人士來看戲,演出結束後梅蘭芳等上臺接見演員道乏,夏衍指著關肅霜說:「多好的人材,梅先生,何不收她為徒?」梅蘭芳含笑未語,機靈的關肅霜立時跪倒在臺毯上,向梅先生行了認師大禮,之後才舉行正式拜師儀式。
文聯禮堂中的川劇演出最多。由於語言隔閡,北京普通觀眾對川劇不大熱衷;而其優美、深雋的劇目和表演,在文藝界卻備受推崇。時任中國文聯副主席兼祕書長的陽翰笙是四川人,對家鄉戲十分迷戀,當然大力支持;他與文藝界的川人名流:美學理論家王朝聞,時為部隊文藝工作領導人的陳其通和當時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院長、後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吳雪,號稱「川劇四大金剛」,每演必到,還寫文章介紹鼓吹。一九五七年《人民畫報》編發川劇專頁,在文聯禮堂拍劇照,王朝聞則是「總導演」,哪個戲拍哪個鏡頭,演員的神情怎麼樣才合適,他都親自坐鎮指揮。一個上午拍下來,大家又累又餓,王朝聞便讓設在文聯禮堂樓下的文藝俱樂部茶座送來精緻的叉燒包、餛飩,招待大家午餐,自己掏錢請客。好在那時吃的東西很便宜,一人一份不過幾角錢,上百人也不過幾十元,用不了王朝聞一篇文章的稿費;不像後來稿費低、物價高,恐怕誰也請不起了。
這個設在地下室的文藝茶座是專為文藝界的朋友清談相聚而設的,全是咖啡館式的包廂座,東安市場的森隆飯莊也曾一度在此設點經營,供應簡單的飯菜、麵點。朋友們在此聚談以至開座談會,安靜無紛擾。老舍、陳荒煤等人常來此小坐,或喝茶或便餐。
文聯禮堂中還常有一些當時在外面「不宜公演」而在此「內部觀摩」的電影和戲曲。如放映美國老片《魂斷藍橋》、《翠堤春曉》時,禮堂幾乎被脹破,門都關不上。當年看過這些經典名片的人,十幾年後再睹,有如「他鄉遇故知」;沒看過的青年人,更希望補上一眼一窮究竟。這種情況還屢屢出現在外面被「禁」而在文聯禮堂卻能演出的戲劇中。一九六一年初,隨周信芳北來的江南名丑劉斌昆在此演出過當時的「禁戲」《活捉三郎》;紹興大班在此演出過老本的《男吊》、《女吊》和《斬經堂》,還配合放映周信芳、袁美雲主演的京劇老影片《斬經堂》;川劇名角「面娃娃」彭海清和「紫蓮」(男旦,影視明星鄧婕之父)在此演過老本《活捉王魁》,其燭火滅而復明及王魁的「屍身飄蕩」等特技,令人叫絕。這些戲十分難得一見,且又不花錢白看,「上座率」高得驚人,禮堂中擠得滿坑滿谷,後面和兩側的牆邊也站滿了人。一代京劇名旦芙蓉草(趙桐珊)就是站在禮堂後面看的《活捉三郎》,見當年的老夥伴劉斌昆在臺上仍然生龍活虎,不禁感慨繫之:昔日老哥兒倆這齣戲沒少演,如今自己卻端了痰盒,本該應當則份的「活兒」卻演不動了。
中國大陸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不時蒞臨文聯禮堂看戲。除毛澤東、劉少奇兩位主席沒有來過外,周恩來、朱德、賀龍、陳毅等,都不止一次在這裡同文藝界朋友坐在一起看戲。那時對國家領導人的警衛戒備遠不像今天這樣森嚴,不過在文聯大樓門口設幾個交警崗哨,指揮一下車輛而已。周恩來總理等也很隨便,同文藝界朋友談笑風生。我那時年輕,曾幾次坐在周總理身後看戲,從未受到干預。有一次在人民劇場看周信芳的《海瑞上疏》,我竟然坐在陳毅元帥夫婦身邊,無人過問;陳老總到場後,含笑同熟人握手寒暄後,還問我:「小鬼,你是哪裡的?」令人如沐春風。
這個文聯禮堂中還開過不少有名的會議。那時開會,不過是清茶一杯,也不備飯,既沒有今日的「誤餐紅包」,也不發紀念品。禮堂中也開過一些在文藝史上留下污點的會議,如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批判吳祖光、秦兆陽的「右派言行」……總的說,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聯大樓,雖難於擺脫已經興起的「左」的影響,但還是有著較為祥和、奮進的氣氛。一九六六年「文革」驟起,文聯大樓首當其衝,內外夾攻,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心碎或啼笑皆非的活劇。
筆者從一九五六年起供職於中國戲劇家協會《戲劇報》,在此樓中工作、生活了十四年,一九六九年秋,同大家一起被驅趕到「五七幹校」。本書所錄,皆筆者親歷目睹,事情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許多當事人近年來陸續羽化仙去,我這個當時的年輕人,也已年近八旬而住進了老年公寓。但往事種種,仍歷歷在目,並深感這是一段歷史,有價值的歷史,如果不記敘下來,再過幾年,一段段詭異的史料,也許真無人得知了。
所以,我以忠於事實的原則,把它寫出來。堅持以親歷目睹為準則,耳食之言概不入文。至於寫這種文字會對自己有何影響,也在所不計,因為我遵循的原則是:尊重並忠於歷史,不讓其湮沒;述而不論,不妨礙時政和他人,且不渲染苦難,以輕鬆筆法為文,不時插敘一些有那個時代特徵的別有風趣的小故事。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厄運堪稱是一場劫難,對各行各業的人說也可說是一次落難。但身在文聯各協會的知名文藝家和年輕的工作者們,卻奮鬥不屈,苦中求樂,對未來充滿信心,堅信嚴冬必然過去,春天定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