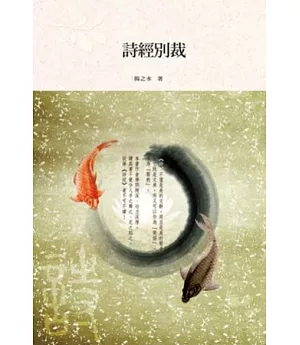前 言
說起「詩三百」,我們今天總把它看成是「純文學」,不過當時卻不然。後世所說的文學,以及官僚、文人、民間,這些概念那時候都還沒有。《論語.先進》中說到的孔門四學,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此所謂「文學」,包括《詩》,也包括《書》和《易》,大致是指流傳於當時的文獻典籍而言。而《詩》不僅是美的文辭,而且是美的聲樂,故它既是文典,而又可以作為「樂語」,作為「聲教」,為時人所誦習。
如此意義之文學,《詩》自然不是出自「里巷歌謠」,《雅》、《頌》不是,《風》也不是。《詩》的時代,是封建宗法社會的時代─這裡說到的「封建」,正是它的本來意義。在此意義的封建制下,以社會等級論,可以劃分為貴族與非貴族,前者包括大夫與士,後者為庶民與奴隸。以居住地域論,可別作國人與野人,前者包括貴族、工商,後者為庶人。若依社會職能,則又可分別為二,即勞心者(貴族)與勞力者(非貴族),前者的社會職能為政治、軍事、文學,後者為農、工、商與各種賤役。若更細論,則貴族中尚有層層等級,非貴族中又有層層等級。比如士,乃武士也,是低級之貴族,居於國中,他有統馭平民的權力,也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務,其地位則低於大夫,高於庶人,而仍屬君子。至子奴隸與庶人,便都屬於小人。這是從《左傳》、《國語》等東周文獻中可以得到的認識。若上推至西周,等級的差別當更為嚴格,那麼我們據以考察《詩》所包括的時代,即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五百年,也很適合。君子與小人的差別,《詩》中提到也有不少。如《小雅》之〈采薇〉:「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此君子與小人對舉,前者為貴族,後者則庶人之屬。〈采薇〉中的小人君子,朱熹《詩集傳》所以曰即「戍役」與「將帥」;〈大東〉中的君子與小人,朱子所以曰「在位」與「下民」;〈角弓〉,范處義《詩補傳》因解作「若王果有是善道以動化於上,則小人相與連屬於下」。又君子與庶民對舉,則前者為勞心者,後者為勞力者。如《小雅.節南山》:「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如《大雅.卷阿》:「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朱熹解作「順愛於民也」。至於與「祀」同等重要的「戎」,它的主力原是貴族。在當時盛行的車戰中,「小戎」之上的「君子」,幾乎沒有例外的是貴族。而庶人,於戰事中只能做徒兵,充廝役。因此,《詩》中寫到的從戎之君子,不會是士以下的庶人。而庶人與奴隸,那時候王可以把他隨土田等物一起錫與受命者,他也可以被用來買賣交換─「五夫」之價與「匹馬束絲」等,見於西周金文。至於庶人的生活狀況,其水平之低下,條件之惡劣,由現代考古發掘中所見,可以知道得很真切。《風》曰堂曰室,曰著曰闥,庶人無與焉。而代表了當時物質生活最高水平的錦帛、玉器、青銅器,更不屬勞力者所有。所謂「禮不下庶人」,或者原因之一即在庶人本不具備履行禮儀的最起碼的財力。物質生活極端貧困,又怎麼可能有創造精神生活的餘裕呢。《風》曰錦衣曰狐裘,曰兕觥曰佩玉,曰車曰馬,《召南.采蘩》說到「公侯之宮」、「公侯之事」,〈采蘋〉說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邶風.泉水》有「出宿」「飲餞」之禮,《衛風.木瓜》有瓊琚、瓊瑤之類的酬答,固然都不是庶人的生活,而《衛風.考槃》,《陳風.門》,《曹風.蜉蝣》,《鄘風.君子偕老》,《鄭風.叔于田》,《大叔于田》,《齊風.猗嗟》、〈盧令〉,《秦風.駟驖》,等等,《風》詩中的大部分,情感意志與精神境界,月旦人物與觀察生活的眼光,又何嘗屬於庶人與奴隸?即便《小雅.黍苗》,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乃庶人所事之賤役也,然而通觀全詩情調,卻實非賤役者言。何況「勞動」與「勞動者」與「勞動者的歌」原本不是一事。《召南.葛覃》寫「勞動」,卻不是「勞動者」的生活,《豳風.七月》寫「勞動者」的故事,但它並不是「勞動者的歌」。比如陶詩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這是真正的「勞動」了,然而沒有人會以為它反映了「勞動者」的生活。說詩者常常喜歡用後世的山歌、民謠與《詩》類比,其實無論創作意圖、修辭手段抑或思想境界,二者都遠不在一個層次。《詩》原是生長在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為宗法貴族體制所籠罩的社會,《雅》、《頌》不論,《風》詩中的大部分作品,從內容到語言,原非可以「里巷歌謠」概之,因此很難用後世的概念,說它是「民間文學」。
然而《詩》的價值,卻不在於它是民間作品與否而定其高下,而在於作為當時意義上的文學,它實在是最好的。孔子愛《詩》,意或在此。春秋引《詩》斷章取義,大約也是由此而發生,這裡不僅有「古訓是式」的意思,作為美的文辭,它也為時人所喜。如此過程中,《詩》和許多詩句的意義也有了擴展。比如有的好句放在整首詩裡,則須服從整首詩的意思,而句意不免受到限制。一旦斷章取義,便因為它本身所具有的張力而可以有新的解釋,亦即新的意義。折衝樽俎之間,賓主以《詩》代言─或用《詩》中之事,或用《詩》中之意,或只取切於此際場景的《詩》中之辭,而雙方心領神會。如此風雅,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它未必是《詩》之幸,也未必是《詩》之不幸。但總不妨說,《詩》作為原始意義上的文學,是輝煌在斷章取義的春秋時代。
從現存的先秦載籍來看,詩與文是並行發展的。詩的淵源或者應該更早,但卻沒有確實可信的材料流傳下來。前人雖然從先秦文獻中網羅鉤稽古謠諺、古佚詩,做了不少輯佚的工作,但這些歌、謠的創作年代其實很難確定,因此未免其偽雜糅。何況這裡還有一個區別,即詩必有韻,而有韻卻未必即詩。或者說,有韻是詩的重要特徵,然而卻不是它的唯一特徵。《書.堯典》曰「詩言志」,《詩大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則有此志與情,方有詩的精神與旨趣。可以說,韻律是詩的形貌,情志方為詩的內質,在謠諺與詩之間,原當有這樣一個分界。而先奏時代流傳至今的比較可靠的詩歌作品便只有《詩經》和《楚辭》。
「詩三百」,都可以入樂,並且可以伴隨著舞,《左傳》中便有很多這樣的記載;後來代表了南音的《楚辭》,也是如此。以後樂與舞都失傳,自然很是可惜,不過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如果詩非依賴樂舞則不能完成它的美善,那麼應該說這樣的詩尚不是純全之詩。詩、樂、舞,可以結合,而且結合之後達於諧美;詩、樂、舞,又可以分離,而且分離之後依然不失其獨立之美善,這時候我們才可以說,三者都已臻於成熟。因此,《詩》的旋律雖已隨風散入史的蒼穹,但無論如何它已經有了獨立的詩的品質,即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力和美,並由這樣的文字而承載的意志與情感,則作為文學史中的詩,它並沒有損失掉很多,只要我們時時記得,它有一個音樂的背景,它曾經是屬於「樂語」的詩。
《詩》有《風》、《雅》、《頌》之分。《詩大序》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此說未必能夠與詩完全相合,所謂「政有小大」,也未免令人疑惑,但作為一個大略的分別,或者尚有可取之處。當然樂調很可能是劃分類別的重要因素,只是我們已經無法知道。以內容論,大致可以說,《風》多寫個人,《雅》、《頌》多關國事;《風》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頌》則重在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即前者是抒寫情憨,後者是講道理。抒寫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動,而道理講得好,清朗透徹的智思,同樣感發志意,令人移情,何況二者之間並沒有一個截然的分別。如果說早期記事之文的簡潔很大程度是由於書寫材料的限制,而並非出於文學的自覺,那麼到了《詩》時代,追求凝練便已出自詩心,尤其二《雅》中的政論詩,常常是把詩的意旨鍛鍊為精粹的格言,這些詩句也果然有著格言式的警世的力量。
詩的創作時代,已經無法一一考訂,但仍可有一個粗略的劃分,即《周頌》在先,《大雅》次之,《小雅》又次之,《風》則最後。當然各部之間也還有交叉有重疊。
至兩漢,才有詩經學的建立。《詩》有了「經」的名稱,大致是在戰國晚期。《禮記》有〈經解〉一篇,所稱述的是《詩》、《書》、《樂》、《易》、《禮》、《春秋》六種,《莊子.天運》也把這六種稱作六經。但那時候還沒有把「經」字直接加在「詩」下,「詩」與「經」連稱作為書名,大概要到南宋。
兩漢《詩經》學是包括在兩漢經學裡的。西漢魯、齊、韓三家立於學官,東漢毛、鄭一派取而代之,《詩》的傳播講授從此便不離政治教化。三家詩既立於學官,它與政治的關係自然是密不可分。或曰三家偏重於作詩之意,毛則多主採詩、編詩之意,而從三家詩所存的部分來看,它以講故事的方式說詩,似乎更接近春秋戰國時代賦詩、引詩的風習,比毛詩近古。因為早已失卻全貌─魯詩亡於西晉,齊詩亡於北魏,韓詩在唐代也已亡佚,所以不能夠知道它的體系,但恐怕未若毛詩全備。毛詩終於存,三家終於廢,這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毛詩每一首詩的前面都有一個序,〈關雎〉一篇的序尤其長,既作〈關雎〉的題解又概論全詩,宋人把後者稱作大序,前者稱作小序,以後便一直沿用下來。詩序的作者,曰孔子,曰子夏,曰毛亨,曰衛宏,戲曰子夏、毛亨、衛宏合作,至今也沒有足以定讞的論據,但其源或者很古,儘管不必一定追溯到孔子或其弟子子夏。序說有信有疑,乃至疑多於信,尤其《風》詩之部。不過後世廢序的一派提出的種種新說,很多意見似乎沒有比詩序更覺可信,而詩序畢竟保存了關於《詩》的若干古老的認識,無論如何仍是讀《詩》的一個很有意思的參照,即便我們在很多問題上全不同意其說法。
平常說「毛傳」,即指《毛詩故訓傳》。《漢書.藝文志》稱「《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正是它的本名,以後「故訓」作「詁訓」,乃是訛誤,而積久相沿,成為通行的名稱。毛傳的作者,最早見載於《漢書.儒林傳》,只稱毛公,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才有毛亨、毛萇大小毛公之說,所謂「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若以早的記載為可信,那麼把《毛詩故訓傳》的作者認作毛公似乎更覺可靠。
關於《毛詩故訓傳》名義,孔穎達《毛詩正義》、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都有闡發,不過仍是以「詁訓傳」為說,近人齊佩瑢《訓詁學概論》中對此做了分辯。漢人訓詁之作以稱「訓故」為多,稱「故訓」者止毛公一人,而用意原有不同。《詩.大雅.烝民》「古訓是式」,毛傳:「古,故。訓,道。」鄭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故訓傳」之「故訓」,即由此取義。而所謂「傳」,《毛詩正義》以為「傳者,傳通其義也」,馬瑞辰以為是「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不過《毛詩故訓傳》以一個「傳」字標明作意,其實乃兼備訓詁與傳二體。然而由書名透露出來的消息,卻表明毛公之初心本在於「傳」,即欲藉此建立起一個說詩的體系,最終的成就在訓詁,也許他並沒有想到。《毛詩故訓傳》對字義的解釋多很準確,也可以說它是最早的一部《詩經》辭典。如果沒有這結實可靠的基礎的工作,後人恐怕很難把《詩》讀懂。至於配合序說的屬於「傳」之一體的引申發揮,則可信者少;關於「興」義的解釋,可從者似也不多。
毛傳說詩的體系完成於鄭玄所作的《毛詩傳箋》。三家詩屬於所謂「今文經」一派,毛詩屬「古文經」一派,鄭玄作箋,則在古文經的基礎上,兼採今文說,對毛傳訓詁的部分做了許多補充,對傳的部分更多有發揮。有了鄭箋的推闡,毛詩才真正定為一尊。至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而對毛詩一系做了全面的整理、補充和研究,成為毛詩的定本。現在我們說到的《詩經》,便是毛詩。
宋人的思想最活躍,雖然唐人成伯璵作《毛詩指說》已對詩序有異議,但更多的疑古之說是由宋人提出來。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其友人以《詩》三百五篇篇名連綴成文,作〈陳子衿傳〉,其思頗雋,卻是很正經地把《詩經》拿來開玩笑,這當然與《詩經》研究無關,卻由此可見一時風氣。
朱熹晚年定本《詩集傳》,提出了廢序的主張,可以算作《詩經》學史上的革命,不過序中所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實在又開了一條討論《詩經》的歧途,影響至今。《詩集傳》最大的好處是簡明扼要,通俗易懂,雖然字義的解釋多本毛、鄭,而以己意取捨於先儒者,有不少較毛、鄭為優。這些特點最適宜教授,於是它由南宋末年起便成為官定的教科書,一直沿用到清。
宋人也還有遵古的一派,卻也不很迂腐,范處義的《詩補傳》、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的《詩緝》,都以疏解平實見長,嚴氏且很有一些新見,可取者不少。
毛、鄭重新受到特別的重視,要到清代。這是訓詁考據的顛峰時代,一時大家、名家迭出,粗計亦無慮數十,其中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最為著名,而解決字義中的疑難,又以馬氏為長。
毛、鄭建立的訓詁考據即屬於經學的一派,大致解決了後人讀《詩》的文字障礙,但《詩》之文心文事,它卻很少顧及。於是又有用藝術的眼光對《詩》做賞鑑批評的一派。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如鍾嶸的《詩品》。朱熹的《詩集傳》也很顧到這一面,而至明代蔚為大宗。清人視六經皆史,明人視六經皆文,《詩經》當然是六經中的上品。孫□的《批評詩經》、戴君恩的《讀風臆評》、鍾惺的《詩經》評點,是全把「經」看作美的文辭,而只在抉發文心上用力。清代牛運震《詩志》、王闓運《湘綺樓詩經評點》,則可以說是這一派的後勁。除評點外,以串解而寓賞鑑批評於其中者尚有不少,明為盛,清則多有繼承。
兩面都能兼顧者,似以清人錢澄之的《田間詩學》為上,雖然認真說起來仍是稍稍偏重於前者。徐元文為錢著作序,有一段話說得很透徹:「夫讀書者惟虛公而無所偏倚,乃有以得其至是至當。朱子之作《詩集傳》,其意亦以為斂輯諸儒之說而非一人之獨見也,惟其先有詆訶小序之見橫於胸臆,故其所援引指摘,時有不能無疑者。後人說《詩》,若先有詆訶《集傳》之見橫於胸臆,則其所援引指摘不足以服人之心有甚於朱子者矣。我獨善夫飲光先生(按錢字飲光)之詩學,非有意於攻《集傳》也,凡以求其至是至當而已,於漢、唐、宋以來之說亦不主一人也。無所主,故無所攻矣。無所攻無所主,而後可以有所攻有所主也。其斯為飲光先生之詩學也。」錢著中自己的意見,不屬賞鑑批評的一派,而常常能夠曲盡物理,體貼人情,頗覺親切有味,卻是最難得的。
學《詩》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是孔子的名言。以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始,而有了《詩經》的博物學研究,可以算作訓詁考據一派的分支吧,這一分支的力量卻是不小,著作也多。令人愛讀的有陸氏《疏》、宋人羅願的《爾雅翼》、清人多隆阿的《毛詩多識》。陸《疏》最早,不僅所說多可據,而且極有情趣,文字又可愛。比如「薄言采芑」條:「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土人戀之不出塞。」又如「榛楛濟濟」條:「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斗筥箱器,又揉以為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赭否?曰灶下自有黃士;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
羅願《爾雅翼》專意詮解《爾雅》中的動植物,而涉於《詩》者頗多。它的引證,說詳也可,說雜也可,總之每一則都可以做故事讀,自然於解《詩》之名物也很有助益。
比多隆阿《毛詩多識》更有名的其實是姚柄的《詩識名解》。不過姚氏過於信從聖人之訓,只因孔子言及「鳥獸草木」而「蟲魚」從略,他便不談蟲魚。《毛詩多識》則遠較姚著為詳,而最好是多言所見所歷。比如「熠燿宵行」條,曰:「關左多草少竹,多山少澤,故惟有飛螢。形如叩頭蟲,大亦如之,黃白色雙翼,長與身等,腹近尾下有光,飛如星流,有人兩手拍擊作聲,便止於地。」螢火蟲屬鞘翅目,這一類昆蟲多有「偽死性」,即每逢驚擾,不是走為上計,卻是跌落在地佯作死狀,多氏則正好把這一細節寫得分明,儘管已算是題外話,卻總是「多識」之有得。
近人所作,以陸文郁《詩草木今釋》為好。陸著把古稱今名一一貫通,很是明白曉暢,間或著一閒筆,雖然與《詩》無關,卻自婉妙可喜,亦足解頤也。
五百年間「詩三百」,實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刪選之後的精華,卻也不算太少。五百年雲和月,塵與土,雖然世有盛衰治亂,但由《詩》中表現出來的精神則是一貫。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愛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過可以說,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貫串事始終的脈搏和靈魂。孔子取《詩》中之句以評《詩》之精神曰「思無邪」,真是最簡練也最準確。《詩》中的男女之情,後來朱子多以「淫奔之辭」視之,其實婚姻乃人倫端始,蕃育人口,上古尤其重視,求「男女及時」,本來不違古禮。孔子「思無邪」之評早把它盡括在內,又何勞後人曲為之解?
只是「詩三百」已經是選本,司馬遷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雖然由「三千」刪至「三百」的說法不很可信,乃至「詩三百」究竟是否成於孔子也有異議,但孔子總是做了細緻的整理工作,選定的可以說都是永久的詩。而所謂「別裁」,卻兼有選與評的兩層意思,實在口氣大大。其實這本來是出版社老朋友的「命題作文」,但覺一個「別」字之下頗存寬容,既可以盡量表達一己之願,又不必顧到各方面的平衡,因此雖然膽怯,依然用它做了書名。然而終究心存忐忑,因此不能不在這裡更做說明。
請先為「別裁」正名。「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語出杜甫《戲為六絕句》之末首。其言「別」,區別之謂;「裁」,裁而去之也。清人沈德潛作唐詩、明詩、清詩之「別裁系列」,即取義於此。但這裡取得一個「別」字來,則只是用「另外」之意,猶區別於「本傳」之「別傳」,或曰於公共標準之外,「別」存一個自己的標準,說得更明確一點兒,便是「我所喜歡的」。至於「裁」,則連對象也換掉─於《詩》,如何言「裁」?所「裁」者,古人之《詩》評而已,又以串聯其說,而夾進一己之見,此所謂「別裁」,只是借字說話,其實與老杜無干,與「沈前輩」之「別裁」體例不合也。
當然喜歡之下仍然頗有分別。如喜其意,喜其情,喜其敘事,喜歡事與情中的思,又或者事與情中史的分子,也有的只是特別喜歡一首詩中的一句兩句。而沒有錄在這裡的,卻又不能以「不喜歡」概之,一則因為剛剛完成一本《詩經名物新證》,故凡彼處談及者,除〈七月〉一篇之外,此中一律未錄。當然不是藉此機會為推銷做安排,唯一的考慮是避免重複和浪費。二則有不少非常喜歡的詩,在它面前卻是格外躊躇。這躊躇的意思,不大好表達,舉例說,比如《鄭風.蘀兮》:「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今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大雅.桑柔》:「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桑柔〉在說著「既作爾歌」的時候,詩好像是有著裁定是非善惡的判決的力量;而在秋風剪斷生意的一片悲涼中,.〈蘀兮〉說著「倡予和女」的時候,詩又是聯繫自然與人生的最為親切的依憑。對著這樣的詩,不免令人懷疑我們是否真正了解和理解了詩在當時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否還能夠真正領悟詩所要告訴人們的東西。此際又不僅僅是心知其美而口不能言,便是連「知」也是朦朧的。因此我覺得需要為自己留下更多的思索的餘地,又因此許多列在最初的一份選目中的詩,最後並沒有錄在這裡。則它雖然題作「詩經別裁」,而「別裁」所含之「選」的意義,它其實是沒有的。
說到注釋,更是一件大費躊躇的事,總想不出應該注釋到怎樣的程度為宜,而這「宜」,究竟以誰為標準。後來這標準取了最為近便者,便是本人。以自己的讀《詩》經歷而言,最初讀白文,多半於字義不得其解,於詩意不識其妙,於是想知道古人有什麼樣的意見,而最早的意見又是什麼。如此稍稍涉獵之後,於各異其說的紛紜中才略略有一點兒會心。前面一節說到的幾種著述,可以算作自己的一個基本書目罷,雖然實在不足為訓,但以己度人,或者彼此的感覺不至於相差太遠。因此在注釋中便盡量多援古訓,如毛傳,如鄭箋。雖然鄭玄解詩常常遜於毛公,但有時也很有可喜。比如《邶風.終風》「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箋:「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此「古之遺語」,乃至遺語中的一番意思,我們至今也還在用著。而在如此細微處竟也遠遠地可與詩人相通,豈不賴鄭箋之力麼!又朱熹的《詩集傳》取用也多,正如前述,它有簡明通俗之長。而朱子解詩也時有用情處。比如《小雅.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朱熹曰:「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雖然於詩不必是達詁,卻是於人情見得深透,而我們正要以此情此心讀《詩》才好。三家之外,各家的意見則「裁」不勝裁,而這本書不是「集解」、「集評」的體例,只好大半割愛。當然不見得順我者取,逆我者棄,不過個人的好惡在其中的確占了分量,乃至於注釋的繁與簡,也多以己意斷之,而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別裁」之「別」字下求得坦然。總之,古賢已遠,衷懷幽渺,本不堪強作解人,更不必說一「親風雅」,但總可略存一點心嚮往之的意思吧。
為省便計,書中最常用到的如《毛詩故訓傳》、《毛詩傳箋》、《經典釋文》、《毛詩正義》,均省作「毛傳」、「鄭箋」、「釋文」、「孔疏」。又引用前人之說,僅舉名姓,不錄書名,而在書後附一引用書目,以備檢索。談《詩》的著作,所引之說,均見於原書中的各詩題下,故也不必很煩瑣地一一注明卷數了。
遇安先生曾為這本書的寫作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見,只是那時候先生太忙,因此常常一起「細論文」的是文友止庵君,最後又承惠以長跋。同室硯友么書儀君也每有中肯的意見。若同春秋引《詩》斷章之例,那麼正該賦〈鹿鳴〉之首章,意取「人之好我,示我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