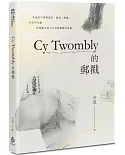推薦序1
諧謔龜裂,赤子情現∕曾珍珍
“The Forge”這首十四行詩是愛爾蘭詩人謝默斯.悉尼(Seamus Heaney)年近三十完成的作品。2003年,獲頒諾貝爾桂冠八載之後,64歲的詩人受蓮蘭基金會(Lannan Foundation)之邀公開演講,特別挑選這首早期詩作當場朗誦,以饗聽眾。此外,若往前回溯,1969年出版第二本詩集時,他曾截取這首詩第一行的行尾雋語作為該集集名《Door into the
Dark: Poems》,由此可見這首詩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某種程度,說它是悉尼詩歌創作生命開端的詩藝宣言(ars poetica),及至白首回顧,初衷依舊,應是對這首詩還算允當的一種讀法。
2012年歲末,甫畢業於前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研究所的柯蘿緹,經過嚴謹的評審過程,在眾多角逐者中脫穎而出,獲得國家文藝基金會的補助,得能將其MFA畢業作品《無心之人》付梓出版,身為他的指導教授,自然與有榮焉。謹試譯悉尼的名作“The Forge”並略加詮解,作為引子,祈能藉此映現青年詩人柯蘿緹創作的潛能與真誠,並期許他持續冶煉技藝,他日修成華語詩壇大器:
The Forge
All I know is a door into the dark.
Outside, old axles and iron hoops rusting;
Inside, the hammered anvil’s short-pitched ring,
The unpredictable fantail of sparks
Or hiss when a new shoe toughens in water.
The anvil must be somewhere in the centre,
Horned as a unicorn, at one end and square,
Set there immoveable: an altar
Where he expends himself in shape and music.
Sometimes, leather-aproned, hairs in his nose,
He leans out on the jamb, recalls a clatter
Of hoofs where traffic is flashing in rows;
Then grunts and goes in, with a slam and flick
To beat real iron out, to work the bellows.
打鐵仔店
凡我所知惟一扇門進入幽明,
外面,輪軸老舊而鐵圈正生鏽;
裡面,榔頭搥擊著砧板發出急促的銳響,
火星四射鳳尾開屏無法預料
或者新打成的一隻鞋在水裡吱吱冷卻。
料想這砧板必然擺放在中心某處,
形狀方正,惟一端頭角卓犖似獨角獸,
受命不遷:一座祭壇
在此他殫精竭智打造形狀和音樂。
有時,圍著皮護兜,鼻毛外露,
他倚著門沿往外探看,懷想達達的
馬蹄在瞬間飆逝的車流中緩緩行進;
然後幹譙幾聲進門去,把門(口彭)然一甩
搥出精粹的鐵,鼓風箱搖啊搖。
打鐵的工藝作為文學創作的隱喻,可說是一種具有普世性的原型象徵。然而,熟悉二十世紀愛爾蘭文藝復興始末的讀者,很容易從這一普世性的原型象徵聯想到喬埃斯(James Joyce)在《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書末的告白:他決定離開故鄉都柏林移居歐陸,潛心從事文學創作,像鐵匠般忠於寫作工藝,為愛爾蘭打造靈魂。從這一層典故推究,悉尼取材原鄉鐵匠做為詩人的隱喻,除了揭示致力於本土書寫之外,另有一層接續喬埃斯,以涵納歐陸傳統壯大愛爾蘭文學格局的寓意。正是這一層考量促使他選擇了文藝復興時期發源於義大利的十四行詩作為這首詩的外形。此一襲自於歐陸傳統的格律,外觀容或像輪軸和鐵圈一樣老舊、生鏽,原創的巧思加上精藝的講究,猶能賦予它靈動、善感的內在生命。的確,在體悟詩藝宛如祭壇的古老信仰之同時,審時度勢,用傳統的形式刻劃出現代工師不敵自動化製程導致手工技藝沒落,甚至慘遭淘汰的窘迫,以及身處窘迫中的憤怒與堅持,藉此喻指詩人自己不昧於現實熱愛創作的忠忱,這正是這首十四行詩的原創性和現代感之所由生。翻陳出新標示著延續詩歌生命於當代的創作要訣。求索於幽明之中,詩人既能以內在的靈光感應有關獨角獸的超現實啟示,自然主義的敏銳官覺同時也讓他能夠細膩自如地將凡軀外露的鼻毛、跨越性別界分的護兜納入觀照中。傳統與創新並行,幻奇與現實同參、神聖與凡俗若無界分,年近三十的悉尼以“The
Forge”昂揚地宣稱自己藉由詩歌創作打造出了進入幽明玄秘的門。
同樣三十在即,柯蘿緹經過數年的上下求索、精心錘鍊,終於也打造出了自己平生的第一本詩集。在指導《無心之人》的過程中,我彷彿見證了悉尼〈打鐵仔店〉詩中所勾勒的那位工師/詩人一路摸索終至成長的身影。面對台灣當代詩壇表面眾聲喧嘩,其實詩的影響力正在式微的現實,柯蘿緹秉持他對寫詩這一創作活動的癡迷,以雜食者不挑食的胃納,從現代詩各家經典作多方攝取養料,無論是古典新裁(〈松下〉),或仿西方戲劇獨白(〈凌晨三點三分的色情電話〉)嘲諷本土現實,或出入於感官認知與抽象玄想之間搜尋超現實象徵,用出其不意的想像和脈脈含情將其跳接或推衍(多首耐讀的情詩,如有著濃濃里爾克風的〈給艾蓮娜〉),題材多樣,風格各異,他寫來大抵都能意到筆隨;多語的雜拼使用更讓他的詩讀來富於生活性、戲劇性。而游移於多情與無心之間觀照紅塵眾生的悲喜癲慾、書寫自己的流離情愁,有時他看似戴著痞子酷酷的假面演戲,擅長以反諷掩飾哀傷,只是他的反諷常因技窮而露出破綻,當下諧謔龜裂,赤子情現,我認為這正是柯蘿緹的詩最迷人的地方。規避專情看似無心,實則以赤子之心涉入鄉土現實,體會多端,諷世不盲從片面觀點,風格轉益多師。這些與早期的悉尼也略有幾分神似。
最後,值得一提的,相對於境外的菲律賓書寫實驗,柯蘿緹的第一本詩集最討喜的嘗試,當屬以棒球練習與比賽為象徵入詩,悼念同鄉先行者詩人羅葉的〈關於一個角落的記憶〉,可比美悉尼的打鐵店十四行詩。替當代的台灣詩人貼切擇取一個原型象徵,同時具有球員與球迷身分的柯蘿緹將他的票投給棒球場上的右外野手,而這也曾經是少年楊牧的自我塑像(《葉珊散文集》序)。
(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推薦序2
後現實主義的出發∕向陽
今年年初,應東華大學創英所教授曾珍珍之邀,擔任該所研究生何立翔的碩論口考委員,創英所規定須以嚴謹的文學創作取得藝術碩士學位,因此何立翔提出的是他的詩集《無心之人》,我因而可以提早閱讀到這位年輕詩人所寫的詩作。對我來說,這是個新鮮的經驗,過去我認識一個年輕詩人,多是先從他在副刊、詩刊中單篇發表的作品開始,累積閱讀印象,慢慢建立起對這個詩人的了解,時間往往是一年,甚至多年之久;但這次不是,整本詩集以學位論文的方式呈現,等於是一口氣就閱讀了一個年輕詩人的第一本詩集,換句話說,一棵樹就站到前面來,展現他的枝葉以及整體的樣貌,這樣的閱讀,是先看到了整體,再看到個別的細節;並且還得提出品評,打口考成績,這經驗的確特殊。
從年初到此刻,我已經忘掉了口考時講了些甚麼,也忘了我如何對何立翔提供我的建議。詩,是極端個人的創作,帶著詩人創作時獨特的風格,本來就沒有一定的標準,也容不得拿尺碼量度、用磅秤論斤,每一個詩人都是一棵獨立的樹,自有風姿,因此我當時大概只提出了我閱讀《無心之人》的感想,提供何立翔參考。我認為,一個年輕詩人的詩作,可以容許青澀,也可以容許揮灑,但不可不清楚地表現與前行代、與同年代詩人不一樣的獨特風格,這個風格標誌了他出現在詩場域中的位置,也決定了他未來是否能夠持續創作的動力。沒有風格,在詩的場域中就沒有位置。
十多個月後,何立翔獲得了國藝會的補助,就要出版這本詩集。寄到我信箱的檔案,一打開來,《無心之人》還是《無心之人》,作者則由本名換成了筆名「柯蘿緹」。我記得了,這是歪仔歪詩社的青年詩人,得過文學獎,但我對他的認識也僅止於此。我在電腦前「打開」這本詩集,逐一重讀,從卷一〈涉街〉,到卷二〈南方〉、卷三〈陌生人〉,最後讀完卷四〈無心之人〉,我看到了在後現代浪潮席捲下一個以嶄新的現實主義美學出發的年輕詩人,以及他採擷生活、社會、現實世界以及非現實想像,加以重組、出以反諷,而又協調以弔詭的書寫能力。這就是了,這就是一個年輕詩人帥氣的出發。
這個出發,來自他的行踏,從童年的〈學小民國賽馬開始〉,他寫宜蘭、寫花蓮(多見於卷一);到菲律賓的馬尼拉,他寫異國的街道、社會風情(多收於卷二)。這些具有地誌和行旅雙重意涵的詩作,通過他敏銳的感覺、多變的語言,展現了與舊有現實主義(至少是1980年代之前)不同的現實主義書寫。他筆下的現實來自生活,都是生身或行踏所見;但他又能聰明地將這些現實加以扭曲、捶打、變形,而更加彰顯了現實的真實性。這是現實主義在後現代資訊社會中的轉化,透過他的詩,讓我看到一個新的現實主義書寫的開始。
這個出發,也來自他對生活周遭的人的觀察和同情(這也是現實主義的主要對象之一),在卷三、卷四之中,他寫色情電話中的「女聲」、寫一個高中女生的自殺、寫東區辣妹,也寫馬尼拉的公關小姐、奎松市說閩南語的華裔少女、華校裡講塔加祿語的圖書館員與學生……,對於生活中的「陌生人」刻劃入微,寄予關懷。但他又能透過語言的巧設,運用反諷、諧擬和部分的雙關,凸顯這背後更大的結構問題,而不止於單純的同情或憐憫。其中映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腐爛、迷失以及朽敗,嘲諷中可見悲憫、荒誕中也可見情深,在我來看,假使有一個「後現實主義」,這位將本名「何立翔」換成筆名「柯蘿緹」的年輕詩人可能已經觸及了。
這是一個美麗的出發,當後現代主義在後資訊年代逐漸趨疲的時刻,一個可以名為後現實主義的書寫年代似乎也暗地展開了,在這本名為《無心之人》的詩集之中,我看到了新一代詩人柯蘿緹的自信,以及他來自生活而又顛覆生活,反映現實而又超越現實的獨特風格。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教授∕詩人)
推薦序3
不知名與所悉∕印卡
這幾年台灣出現一些以菲律賓為主的南洋寫作,或許是因為一些新生創作者的海外替代役男經驗,促就這些題材的出現,比如連明偉獲得台積電中篇小說文學獎的〈番茄街游擊戰〉就是近年最顯著的一例,在這些逐漸增加的文本中,柯蘿緹這部名為《無心之人》的詩集亦屬其中之一。相較於過去台灣文壇鼓吹的旅遊文學,這些有別於典型馬華文學的海外經驗,或許是研究者有興趣的觀照點。
大學時就認識柯蘿緹,在閱讀他這第一本詩集時,不由得讓人出格地想起哈伯瑪斯《事實與格式》──多年前在等待其清大中文系的成年禮時,正好發現這本書陳列在圖書館的新書架區──如果這種記憶事件中的偶然性有任何意義,也許是屬於哈伯瑪斯對美學現代性心態(mentality)所言及的一絲那種對歷史的抽象反對,歷史因此失去了一種劃分好的、保證連續流傳發生(uberlieferungsgeschehen)的結構。這本《無心之人》也許不是最好的嘗試,但透過這本抒情之作,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台灣政經改變對於主題與語言風格影響的諸多可能。
這本詩集依其主題大致可以分為成長回憶、南洋時期,以及一些看似明朗實則幽微的心情書寫。如同柯蘿緹的詩句:「已然見底,記憶的乾糧∕即將消磨殆盡」,這是這本抒情節奏明顯的詩集在記憶細節、人物刻畫之餘所遺漏的。但正如〈關於一個角落的記憶〉:「濕冷的雨在家鄉下著,……」或是在〈秋末懷李潼〉憶起同學父親,這本詩集中的宜蘭形象彷彿投手丘向外拓展開來,藉由柯蘿緹對棒球的喜好以及鄉野的描述互滲成為特殊的抒情地景。
對於此中的抒情描寫語調,我想也許加塔利(F.Guattari)對於童年的描述可以幫助我們更理解這本詩集「抒情」所隱藏的未知:
……總有消失,或者所幸被忽略了的危險,在這兩種情況下,青年學生和精神病患者,常被置於正常小孩或是正常成年人廣泛的社經、政治等各個領域被關注著。在移情關係中幾乎沒有任何實際的雙元關係……在這裡,我們期待這「母親和兒童的關係」在實際情況中,我們認識到,這是最起碼的,三角關係。換句話說,總有一個真正的中介對象的情況,作為歧義或支持介質。
這本詩集的抒情口吻始終中介著柯蘿緹本身的文學訓練與主題。身為創作者,我也時常思考長久以來的抒情傳統在這近十年的典範強化下,究竟是造成一種技藝的危害,還是情感的再發現?雖然這本詩集還未及強烈有其表達及其想解除的片段、階層與領域的脈落,但抒情使言說自身難以被辨認。這本《無心之人》詩集的出現有我不得不說的,或是換成用柯蘿緹的詩句:「像你這樣的人,你的心若有裂縫∕流出的會是什麼。」
誠如早先所提及,這幾年由於一些寫作者因替代役前往東南亞所逐漸突現而出的主題,與馬華文學形成某種程度的張力。在語言形式上這跟中國詩人當代的邊塞詩與真正的維吾爾文學、圖博文學,有相似的言說權力關係。比如董炳月最近針對野村榮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記》的相關漢詩研究,以及當代中國詩人對於邊境的現代詩寫作,比如冬至〈烏魯木齊的雪〉、〈北疆四季歌〉,我們也可以在這本詩集裡發現其中抒情語言曖昧的位置。此黃錦樹在針對抒情傳統的「正言」或是王弼「得意忘言」中對詞彙一言一義的政治性,我們也可以在這本詩集看到抒情語言由於抒情性建立在物、景的慣性,難以有「成為他者」(becoming
others),將不同的因子混入主體性的可能。
然而在《無心之人》中多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語言不穩定的激盪、試圖調合他者的姿態,比如這本詩集中〈凌晨三點三分的色情電話〉所呈現的B級幽默除了呈現出雅俗語言彼此間的衝突,一方面呈現了抒情套語的感知結構的穩固,另一方面也暗示著某種新詩藝的可能性。比如整個卷一涉街〉提供了另一種版本的《臺灣鄉鎮小孩》,或是〈在春天撞倒後母〉中「漲奶了一整個冬季的後母」這類生動的語言,以及使用同音異義的詞語所試圖創造的詩歌空間,都足見這本詩集的實驗性格。但我仍期待柯蘿緹可以從楊青矗、陳黎等前輩已建立的語言詩學中尋求更多可能,讓他更早能跨越那些未盡的挑戰。
某種程度我與柯蘿緹可能更天真的相信文學無關意識形態,但我們這一代足見世界的暴力正逼向創作想像力的根基。就如同〈烏杙,這地方〉:「這地方經常被誤讀成:鳥代∕這地方,並未發現鳥居遺址∕也無人從事代書工作∕但鳥們,依然隨著四時啾囀∕僻居此地的人們仍舊聆聽,居住∕這個地方,人與一切各安其分∕沒有誰能代為書寫誰的生活。」但當某些主題在時代之下突顯而出,創作者代筆寫下的那些不知名與所悉的,語言中表現的真誠,不過只是不要成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也許這也是我們在企盼新詩學沒說的心聲。
(作者為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