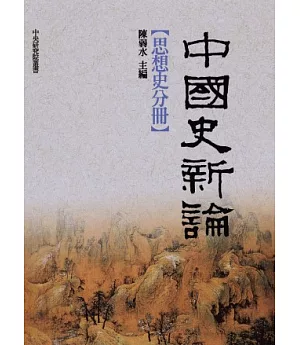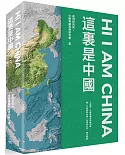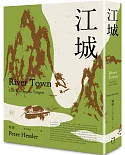《中國史新論》總序
幾年前,史語所同仁注意到2008年10月22日是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希望做一點事情來慶祝這個有意義的日子,幾經商議,我們決定編纂幾種書作為慶賀,其中之一便是《中國史新論》。
過去一、二十年來,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
我們以每一種專史為一本分冊的方式展開,然後在各個歷史時期中選擇比較重要的問題撰寫論文。當然對問題的選擇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而且總是牽就執筆人的興趣,這是不能不先作說明的。
「集眾式」的工作並不容易做。隨著整個計畫的進行,我們面臨了許多困難:內容未必符合原初的構想、集稿屢有拖延,不過這多少是原先料想得到的。朱子曾說「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我們正抱著這樣的心情,期待這套叢書的完成。
最後,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主編、參與撰稿的海內外學者,以及中研院出版委員會、聯經出版公司的鼎力支持。
王汎森 謹誌
導言
一般來說,專書的導言很重要,導言說明一本書的題旨,解釋主題的意義,介紹相關背景,甚至闡述研究方法,以備讀者進入書的主體。至於論文集,就很難說了。論文集中的文章,往往課題分散,風格互異,導言常是功能性的,為一些不甚相同的東西,提供共聚一堂的理由。就本書而言,精華在論文,導言也不十分重要。在這篇文章,我想以編者的身分,談談本書的緣起,以及編輯過程中所生的感想,約略等於書中諸文的前菜,或許有助於讀者對本書特色以及中國思想史領域的認識。
這本書編集的過程非常漫長,長到已經是一段歷史了。本書的籌備工作起於2004年春天。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王汎森先生(現為中研院副院長)邀集所內同仁,商議出版一套「中國史新論」,涵蓋傳統中國的各個主要面向,作為2008年慶祝創所八十週年的獻禮。當時籌畫這套叢書,有一個想法,就是希望編寫出來的成果,既能反映學術的最新進展,也能提出寬廣的敘述和討論,供專家以外的學者乃至一般知識人閱讀吟味。
我承命主編「中國史新論」的思想史冊,就依照這個方向規劃。我把書名訂為「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轉折」,依此意旨,擬了十多個大概的課題,都跟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轉變有關,然後邀請學者撰稿,希望各篇文章配合,能夠構成一本內容實在而有啟發的著作。至於個別文稿,則是期盼,既有綜論的性質又有個人的深度,寫作方式不必過於技術性,可以大量融入作者以及他人的既有成果。
我按照上述方向籌編本書,進展並不如預期,文稿出現多樣化的情況。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包括何謂綜論性的學術著作,各人的體會並不一致。又如,學者從事研究,很希望自己的文章有新意,有突破,但原創與宏觀往往無法並存。另外我個人工作過多,經常荒廢編務,與作者的聯絡和溝通不夠積極,也進一步促成本書自然演化的態勢。無論如何,經過多年邀稿、寫稿、集稿而成的本書,大概有兩個主要特點。首先,書中的論文既有綜合性較強的,也有專題性明顯的。其次,綜論文章的主題固然都針對思想史上的重大轉折,即便專題論文,也都與此相關。本書雖然沒有實現原初的構想,成為一本具整體性的著作,但仍有相當明晰的結構。讀畢本書,應該可以對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思想史上大部分的重要變局有所認識。此外,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本書沒有完全走綜論的路線,卻因此獲得了若干深具創新性的研究,這是讀者閱讀本書就能自知的。簡單說,就論文的形態而言,本書具有複合的性質,雖然全部文章都和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變化有關,但由於系統性不足,可能已不足以擔當「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轉折」之名,在出版前,我決定將本書改題為《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希望平實地反映其內涵。
以下,要對本書做進一步的介紹。前面說過,本書的論文可分為綜論和專題研究兩類。依照這個區分,綜論類有陳來(作者敬稱略,以下同)〈西周春秋時代的宗教觀念與倫理意識〉、金春峰〈漢代經學與經學哲學的確立及其歷史意義〉、陳弱水〈漢晉之際的名士思潮與玄學突破〉、呂妙芬〈歷史轉型中的明代心學〉、艾爾曼(Benjamin
Elman)〈18世紀中國經學的危機〉;專題類則有余英時〈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試探〉、葛兆光〈「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對儒家思想世界的擴充與挑戰〉、黃進興〈理學家的道德觀——以《大學》、《近思錄》與《傳習錄》為例證〉,以及王汎森的兩篇論文:〈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本書論文共十篇,一類五篇,也算巧合。上舉諸文中,專題類都屬於原創性的研究,這是無須特別說明的。至於綜論類,也涵藏了許多作者個人的研究所得,有的還是在這些文章中首次發表。綜論類與專題類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處理的現象範圍較大,文中融匯比較多作者或他人的既有成果,在表達方式上,有些文章敘述多,引文比較少。上述的差別只是約略而言,實際情況並不那麼明顯。
本書諸文的主題也有可論之處。就涉及的時代而言,先秦部分有兩篇(余英時、陳來),漢代有一篇(金春峰),中古有兩篇(陳弱水、葛兆光),宋元明兩篇(黃進興、呂妙芬),清代三篇(艾爾曼、王汎森),分布尚稱平均。如果從中國思想史上重大轉折的視角來看,先秦的兩篇都是處理古代中國思想的起源及其主要內涵,也就是,可以稱作「思想」這樣的東西——或可界定為自覺程度較高的觀念系統——如何從古代的文化與心態中浮現成形。在余英時的論文,他運用了雅斯培(Karl
Jaspers)的概念,稱此為「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金春峰的論文討論經學在漢代的成立以及與之相關的思想,這是中國思想史上關鍵性的發展。陳弱水探討漢晉之際的思潮以及玄學的興起,則是中國自儒教取得正統地位後的第一次思想巨變。葛兆光從引進或創造新知的角度,處理佛教和道教對中國原有世界觀的衝擊。來自印度的佛教在兩晉以後壯大以及道教的形成,是中古時期的另一變局,為中國的思想世界帶來結構性的改易,重要性不言可喻。葛先生之文,是本書中唯一探討非本土主流學術思想的論文,彌足珍貴,本書在這方面的比重可能過低,是一項缺憾。黃進興透過宋明理學尊崇的《大學》、《近思錄》和《傳習錄》,解析理學家道德觀的特質,呂妙芬則多面檢視明代心學。理學在宋代的崛起是中國思想史上之一大事因緣,以王陽明為首要代表人物的心學在15、16世紀出現乃至於領時代風騷,則是理學傳統的一大波動。王汎森論清初禮治思想之文,處理明清之際思想變化中的一個重要面向;艾爾曼則討論盛清考證學的思想史涵義以及經學考證與科舉、自然科學的關聯;王汎森另一文藉著探討清代道光、咸豐年間(1821-1861)以下的禁書重出,指出晚清思想新局的一個本土來源。上述最後的三篇論文,分別涉及清代初、中、晚期,前兩篇針對傳統中國最後一個重大的思想變動——理學的沒落與考據學的興起,最後一篇則觸及了近現代的大變局。整體而觀,本書雖然沒有系統地辨識與論述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轉折,在這個問題上,唯一主要的缺漏也只有唐宋之際的變化,涵蓋面算是相當廣。
本書另一個值得介紹之處,和本叢書的宗旨有關。本叢書名為「中國史新論」,可以說,一個重要目標是在顯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歷史學科同仁以及其他學界同仁在開拓新領域、運用新方法、探索新問題上的成果。本書是《中國史新論》中的一冊,是不是足以當「新」之名呢?
我覺得是可以的,但要比較清楚解釋這項評估,需要先作幾點一般性的說明。在歷史學中,思想史是個特殊的領域,相對小但長期保持活力,在知識界的重要性則起伏不定。思想史最明顯的特點,可能是它的多學科或跨學科性質。人類過去的思想是很多學科——特別是人文學科——都關注的,包括哲學、文學、宗教學、政治學乃至新起的文化研究,並不是歷史學者所獨專,歷史學中的思想史學者和其他學科的同行常有密切接觸,有時彼此的研究方式也差不多。舉例而言,在20世紀的美國,對思想史領域成形貢獻最突出的,可能是提倡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的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Lovejoy就是哲學訓練出身,長期任教於約翰霍浦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哲學系
。思想史的跨學科性,在國際各主要學術圈都是如此。在中文世界,無法用現代西方學科來界定的中文系也以思想史為重要研究領域,更是突出的現象。思想史的跨學科性,使得研究者很容易受到各種人文思潮的影響,特別是理論性思潮,至少在英語系國家,這造成思想史學界中方法論與研究方法意識特別發達,思想史的研究取向也隨之飄忽多變。中文思想史學界雖然不能說特別重視方法論的反省,但臺灣自1960年代以後就深受英美學風感染,西方新近史學觀念後來也進入中國大陸,中文思想史研究因此迭有新貌,是自然不過的事。
思想史領域還有一個值得提出的現象,就是在不同的學術社群,往往有著殊異的樣貌。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中文、英文、日本學術界都有活躍的思想史研究,但差別不小,德國的情況也可能相當不同。這個現象是如何產生的,還有待仔細查考。一個明顯可見的因素是,思想史的歷史相當悠久,而且來源多端,不完全是現代專業史學的產物。在歐洲,思想史最主要起自哲學史,根據學者的研究,19世紀以法國Victor
Cousin(1792-1867)為代表的折衷主義哲學(eclecticism),是造就近代哲學史意識的最大力量,事實上,Cousin本人已經使用「觀念史」(l’histoire des
idees)一詞了。折衷主義以為,歷史是最重要的哲學方法,人們唯有透過對哲學史的全面檢視,找尋出哲學思辯中最普遍的元素和觀念原則,解決其間的難題,才能夠獲得哲學真理。其他文化活動的歷史,如文學史、科學史也都與思想史的形成有關。以文學史為例,19世紀德國的浪漫主義思想認為,文學——特別是詩和神話——是人類精神世界的表現,文學的歷史不啻等於心靈的歷程。19世紀法國的文學史研究,已有接近後來思想史的做法,如以作者內心或歷史脈絡的因素來解釋文學現象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想像,在19世紀的歐洲,特別是德國與法國,當「科學性」的現代史學興起之時,在強調變化即是本質的整體思想氛圍中,許多學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自己所關心的心靈現象的歷史,這些研究後來逐漸滲入歷史學,或與歷史學結合,形成了思想史學。思想史的來源既然如此複雜,而且經常是外於專業史學,某個社會的思想史研究,很自然受到當地一般人文學術傳統或風氣的影響,從而造成重大的社群差異。在中國,思想史並不純是從外輸入的,本土的思想史書寫可以追溯到很早,《高僧傳》系列中的「義解篇」,記述理學傳統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以及清代、民國初年其他的學案體著作,都是某種形式的思想史。直到現在,在中文學術界,思想史研究還存在新舊雜糅的情況,新與變不是這個領域發展的全貌。
如果說,在中文的學術環境,思想史研究既不斷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又仍有舊傳統的力量,那麼本書之「新」,「新」在何處?要以什麼時間為衡量的起點?我想,可以1970年代初期為起點,這是西方思想史學開始大舉影響臺灣的時刻。當時臺灣所接受到的最主要觀念,顯然是「內在理路」研究法,影響可能長達20年之久。這個觀念強調,思想史最重要的研究對象,是思想本身,而且思想的演化與變動,往往最能從思想內部的因素——譬如過往的思想或思想傳統的深層結構——得到理解。這種取向的研究,大大提升了臺灣研治思想史學者解析觀念、探查思想之間關係的能力,也使因果解釋成為思想史研究中的核心問題。「內在理路」的風潮挑戰了原來習於描述個案或探討某人「生平與思想」的做法,對於思想史領域在臺灣的明確建立,起了關鍵作用
。
我們如果拿本書的內容和上段所說對照,會發現,沒有論文屬於「內在理路」的取向,本書與這個取向的重要相異之點至少有二。首先,本書普遍重視思想與其他文化要素的關聯。舉例而言,余英時和陳來探討古代中國思想的形成,都很注意這個「哲學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與宗教的關係,余英時推論先秦諸子(含孔子)思想和巫文化的牽連,更是思入微茫,深富創意。此外,陳弱水論漢晉之際的名士思潮與玄學興起,留意從文學作品探尋思想的蹤跡;葛兆光之文,則由導入新知識或新世界想像的角度,來揭示佛教和道教的衝擊。在本書最後一文,王汎森以物質性的變化——被禁的舊文本以各種形式問世,作為觀察19世紀中期以後思想動態的透視點,頗有晚近西方人文研究中「物質的轉向」(material
turn)的意味。上述的做法,個別而言,大多已見於過往的研究,但整體觀之,無疑反映的是思想史和文化史結合的新傾向。
其次,本書不少論文也關注思想和歷史環境的關係,譬如思想變化中的政治社會因素或思想的社會文化影響,陳弱水論漢晉之際思潮、呂妙芬論明代心學、王汎森論清初禮治思想等文,都是明顯的例子。思想應該從外在環境來取得了解,是人文研究中很早就有的想法,馬克思主義的下層結構、上層結構之說就是其中一個極端的表現,在思想史的傳統裡,也一直是重要的觀點,但相對於臺灣1970、1980年代流行的取向,本書的這個方面也算有新意。人的意識受環境影響,乃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環境的反應,在常識上是很明顯的。但在研究中如何具體指陳兩者間的關係,有時難度很高,可以說,這是思想史領域中的永恆問題。
上面所談的兩點新意,遠不足以概括本書的內容。如前所述,思想史領域具有多學科性,方法論意識發達,變化多端而又新舊學術因子夾雜。這種不完全推陳卻出新的狀況,導致研究多元化,本書於此也有所反映。舉例而言,黃進興的論文透過檢視若干經典文本以及有關詮釋,試圖揭露宋明理學家共通的道德觀,具有哲學意味,和本書其他論文的風格都不相同。此外,本書的大部分文章並非採取單一取向,作者往往利用思想史領域所存在的各種思路,多角度地探討自己的課題。以上是我對本書論文的一些粗略觀察,提出觀察的同時,也對思想史研究的一般狀況稍有評說,希望所論尚無大誤。
最後要問,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情況已經很好了嗎?有沒有重大的缺漏或挑戰?答案是:有的。無論在經驗事實的重建、已知事物的理解、問題的辨識、心靈和文化現象的發掘、研究取徑的反思等方面,都還有非常多工作可做。至於怎麼做,優先做哪些,原則性的談論恐怕用處不大,重要的是,要在實際的研究進程中不斷考慮,不斷測試,不斷實踐。這裡只想提出一點,和其他主要學術社群——如英美、歐陸、日本——的思想史研究相比,中文學界有一個明顯的大空檔,就是政治思想史。在西方和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都相當發達,是思想史領域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甚至有重要的方法論概念是從政治思想的研究中產生出來的
。在很多社會的思想歷程中,集體秩序如何建立、怎樣才是正當的集體秩序、集體生活與人生價值的關係為何、政治權力當如何運用,一直屬於核心的問題,政治思想在思想史研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事屬當然。但可怪的是,在中文學術界,政治思想史特別不發達,在近現代史的範圍之外,無論是通論性著作或專題研究,都相當寥落。中國思想以現世關懷著稱,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治」的問題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隱晦不彰,是相當諷刺的。
中文學界對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忽略,原因顯然很多,有些可能和學者的研究方式有關,有的可能和他們的思想狀態有關。讓我猜測其中一個原因:不少人認為,中國自秦漢以後,政治思想就失去創造性,陳陳相因,缺少研究的意義。這種想法觸及了一個根本問題:什麼是思想?如何分辨值得研究和不值得研究的思想?應該指出,在現實世界,大部分思想創造性都不高,但思想的作用未必與創造性相關。以當前的臺灣而言,人們最注意的思想現象是意識形態(ideology),這顯然就不屬於有創造性的思想。問題是,我們的社會和學術界對所謂「意識形態」認識不足,這個概念的義涵為何,作為經驗現象的意識形態有哪些樣貌,都少有人考慮,在這種情況下,有關的談論往往變得無意義。我的意思是,我們需要面對現實,如果一個環境真的是被信仰、教條和意識形態所主宰,學者就有責任研究這些形態的思想,不如此做,而只上下求索找尋有深度、有新意的觀念,是對歷史的曲扭。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深究這些看來僵硬的思想版圖,說不定會有具啟發性的發現。過去二、三十年,中國思想史研究有很大的進展,視野擴展,新議題一再出現,但劃地自限的情況還是有的。私意以為,我們應該有更強烈的探索心,努力了解思想運作的實態,以深化自我認識。這樣的認識,也可能貢獻於世界的改善。
陳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