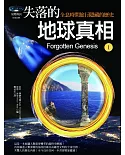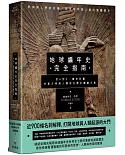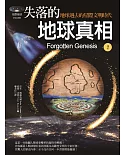推薦序
可愛的妖怪世界
看完本書底稿,我第一個反應是:這位作者好厲害!不但收藏了這麼多食玩,而且對每一類食玩的歷史背景具有正確知識。例如這本聚集日本妖怪食玩的書,自平安時代妖怪史寫到現代,還穿插中國妖怪典故,以及本土台南林投姊故事,令人讀得津津有味,配上圖片和照片,更是賞心悅目。
第二個反應是:若有機會,我想拜託作者給我看看她收藏的這些食玩。對於食玩,我也很熟悉,因我家兩個孩子小時候曾經收藏過,每次買糖果或巧克力,目的都不是想吃那包糖果或巧克力,而是附贈的食玩。當然那時代的食玩沒目前這麼精緻,卻也讓孩子們收藏得不亦樂乎。
轉蛋上市當時,我也曾玩過一陣子,因事前無法預知掉下來的轉蛋裡面是啥玩意兒,有點刺激也有點新奇。現在日本的便利商店,幾乎每家都把這種食玩擺在最顯目的櫃檯,我都只是看看而已,不買。家裡光放書就嫌地方不夠了,哪有餘地擺這些精緻玩具呢。不過這套妖怪食玩,真的令我也想收藏。
作者在書中提到她很喜歡鬼故事,我也很喜歡鬼故事或描述超自然現象之類的書,以及怪談。但我似乎不是特殊體質,除了高中時代有過鬼壓床經驗(當然不是真的被鬼魂壓住),至今為止從未與另類世界接觸過。但這並非表示我不怕鬼,也並非表示我不相信妖怪的存在。我認為,那只是我們看不見而已,絕非不存在。
高中時代,我有個朋友是陰陽眼,每次他來我家玩,都會說「今晚特別多」,或「今晚不怎麼多」,有時還說「妳家公寓樓下樓梯口站著個抱著孩子的女幽靈」。我每次都聽得毛骨悚然,有時還跟一大堆朋友特地跑到樓下去「探險」,只是看不見的人就是看不見。當年,因我是從台灣回國的「歸國子女」,又是混血兒,在學校很有人氣,家中經常聚集一大堆不同年級、班級的朋友。只是,有陰陽眼的,就他一人而已。雖眾人都看不見,卻沒人懷疑他的陰陽眼能力,畢竟他個性不是那種會說謊的人。
又,高中時代,女生們之間流傳一種說法:在半夜十二點整,把所有燈都關掉,再點蠟燭照鏡子,鏡子中會出現未來的丈夫臉孔。這說法在我們學校流行得很厲害,卻沒人真正試過(至少在我朋友之間)。我當然也不敢試。不知是不是當年這學校怪談給我印象很深,直至目前,我還是對鏡子懷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說起來,日本的妖怪並不可怕,甚至可跟「寵物」同列。因日本是神道思想,認為萬物都有「靈」,一株古樹可以是「神」,也可以是「妖」;一塊岩石可以是「精」,也可以是「怪」。甚至連語言都有「言靈」,表示一旦說出口或寫成文字,那「事項」便具有自己的生命,會自己往「目的地」前進。也因此,日本是「八百萬神」國,更是「八百萬妖」國。而妖怪,簡單說來,正是「沒當上神」的落伍神。一般說來,日本的神,不會插手管人間俗事,眾神專司大自然現象,而且沒有形狀,但這些「沒當上神」的妖怪,不但具有各式各樣外型,也很喜歡跟人類黏在一起,喜怒哀樂都跟人類相同。
山中有天狗、送狼(跟在人背後直至下山),河邊有河童、小豆洗,海中有海和尚、幽靈船,村落有姑獲鳥(懷孕中或生產時過世的女性,下半身沾滿血跡,抱著嬰兒要過路人抱一下嬰兒)、雪女,家中有座敷童子、付喪神,街上有百鬼夜行,神社寺院有式神、護法童子……等等等,族繁不及備載。
雖說往昔便有記載妖怪的古籍,但直至江戶時代妖怪學才真正興盛起來,起因在浮世繪家鳥山石燕(1712~1788)畫的《畫圖百鬼夜行》,他把至今為止只有文字描述的眾妖怪,全賦予外型並分類,也就是說,給妖怪注入生命。文學作品方面則有《雨月物語》作者上田秋成(1734~1809)、《南總里見八犬傳》作者瀧澤馬琴(1767~1848)、國學者平田篤胤(1776~1843)等人。
戰前的妖怪作家是小泉八雲、泉鏡花、芥川龍之介,民俗學者方面有南方熊楠、柳田國男,畫家是河鍋曉齋(號稱「日本最後一位妖怪畫家」),其他還有妖怪博士井上圓了、歷史學者喜田貞吉。戰後的妖怪漫畫家就非水木茂莫屬了,作家則是京極夏彥、宮部美幸、荒□宏等人。只是,我做夢也沒想到,台灣竟會出現個妖怪御宅族──葉怡君,而且是女生!太佩服了。
總之,我非常推薦這本書,無論內容或編輯,都很讚!
茂呂美耶 二○○六年八月 於日本埼玉縣
自序
點燈:櫥子裡的妖怪
文◎葉怡君
小的時候,我相信櫥子裡有妖怪。
每開衣櫥之前,必先「嚇!」一聲的叫,然後才撐開空隙,翻出想拿取的衣物。
沒有誰教導、沒有長輩發現,也不是看了什麼《獅子.女巫.魔法櫥》之類(當時這書在台灣還沒個影子),這是一種小孩子面對蠢蠢欲動世界的儀式,也是打招呼的方式。
相信它們有法力,孩子都害怕未知、有力量的東西。不過大部分時間,它們就像無聲無息的好鄰居,朝夕相處、平安無害。
跟學校同學不同的,是偶爾沒關好的櫥門,鬼鬼祟祟露出一條黑色隙縫,像異界睜開的眼眸,窺視著來往的家人,唯有我時而停步,與黑暗長久對望著。
會認為衣櫥裡有妖怪,或許是因為小叮噹,也是從抽屜裡蹦出來的。另一個可能,是當時著迷於《聊齋誌異》,無論上餐桌或進浴室,都帶著這本半白半文的六○○頁小說,小生被狐精迷了,我也被書妖魘住了。哪一頁有折痕缺角、滷肉汁香、或是不慎滴了水漬,莫不瞭若指掌,比校園裡遊樂設施的位置還清楚。
那時候,家住在衛生署立台南醫院附近,現在新光三越百貨的對面,雖說是市中心精華商業區,小城的黑夜比白日更多孤寂,只有間行的車輛,呼嘯在奔回家的路途上。
雖然平常老誇口敢「向天公借膽」,但我的罩門,就是不願意半夜上頂樓去。若須撿拾白天遺落的東西,或須照顧飼養的狗兒,一但避無可避,總是磨磨蹭蹭、東拉西扯,要不拖著家人、要不牽延時間,就是拒絕獨自上樓梯。如果真的不得已,就只好電快的閃上去,又飛跑著衝下樓,跟泥鰍一樣迅捷。
因為,夜半的頂樓,看得見台南醫院附設靈堂的燭火,聽得到亡者家屬哀怨悲切的哭聲。那時簡易靈堂搭在隱密的小樹林中,一般人不會留意,但我家住在鄰近,當然知悉。每次到了樓上,天邊冷月寒星,暗夜蕭索清寂,一陣分不清方向的風冰冰地吹來,「噫噫噫……噫噫噫……」的嗚咽聲,哽哽塞塞、斷斷續續、似遠似近的飄散過來,就好像鬼魂往脖子裡吹涼氣,讓人寒毛直豎。
如果大膽向醫院的樹叢瞧,會看見靈堂點燃的燭火,在風中幽幽然明滅著,就像亡者已逝的生命之火,掙扎過後,終歸就要熄滅了。暑熱蒸散後的夏天,棺材常放在外側樹蔭下,目光不想瞧,都不能不見。
對一個未曾經歷生死之痛的小孩來說,這些就是最魂飛魄散的經驗了。無怪乎每次我都像馬蜂追趕似的快去快回,末了還要到廚房去喝水壓壓驚。
雖然是這麼怕鬼,但我又愛看鬼故事。就像中研院學者林富士說的:
「我們大多平凡庸俗,生活單調乏味,日子幾乎一成不變,因此,永遠會對『非凡』之人有所憧憬,對於『異常』之物有所覬覦,對於『妖怪』的世界有所幻想。」
當《聊齋》無法滿足對鬼怪的想像,我轉向最知名的神話小說《西遊記》。第一本西遊是從老書櫃邊角挖出來,文言文配上木刻版畫,年代久遠、字小如蟻、紙薄且軟,不但沒有封面,還缺了最後兩頁,但是千變萬化的情節,讓眾生顛倒,我跟著遊歷天界龍宮西域……浸泡發酵得更加深入。
這時國語課本還在上「國父的童年」,許多冷字僻字怪字,我這小學生似懂非懂,典故更是一知半解,每當作者吳承恩(1500~1582)大掉書袋、連篇古詩駢體,我就自動跳行--譬如描寫黃風大王:
「冷冷颼颼天地變,無影無蹤黃沙旋。穿林折嶺倒松梅,播土揚塵崩嶺坫……(中略四十二句七言古詩)……呼喇喇,乾坤險不炸崩開,萬里江山都是顫!」
許多人小的時候都看過《西遊記》,就我個人來說,印象比較深刻的有:黑風怪、白骨精、黃袍怪、金角銀角大王、九尾狐狸、聖嬰大王、虎力鹿力羊力大仙、金魚怪、兜怪、琵琶精、六耳獼猴、鐵扇公主、牛魔王、黃眉老佛、賽太歲、七蜘蛛精、百眼魔君、大鵬金翅鵰、金鼻白毛老鼠精、辟塵大王、玉兔精……等等,別責怪我耽溺的細數,只因美好的最是竹馬青梅。
真佩服吳承恩歸納式的想像力,這些鬼怪各有個性、專長、特色和來歷,加上不計其數的跑龍套小妖,活脫脫是一幅以怪喻世的人界圖。網路中網友把西遊群妖裡的大鵬金翅雕,評為「戰鬥實力最強的妖怪」;而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和孫悟空一個模子倒出來的六耳獼猴,那是一個明顯的比喻,暗示人生「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小時候就這樣開心的,囫圇吞下唐僧之八十一難,興沖沖的把書帶到學校,卻沒有人感興趣。同學高談昨晚的「小甜甜」,厚厚的古書被翻了幾頁,就孤零零晾在一邊,像長年不得志的作者。
我把書緊緊捏在手裡,非常確信這一○八回大鬧天宮,絕對比卡通精彩生動,但是人笨口拙,沒辦法讓齊天大聖井底翻身。
後來就不再帶去了,因為書太重;而且那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對小學生一樣也太重了。
每次重讀《西遊記》,都像看京劇的熱鬧武打戲--高蹺拐子、翻滾打鬧、鑼鼓喧天,不是戲不深刻,端視看官能不能看進骨子裡。想起吳承恩因為寫書,耽誤了八股文章,屢試不第,他曾表示:「因自竊笑,非餘求怪,蓋怪求餘也!」--不是我去找妖怪,是妖怪來找我的!所以奔放遏抑、不可不寫。即使貧老以終,相信他再一次,還是會選擇在書中復活吧。
後來我又愛上神話《山海經》,它是迷信與理性思緒的集大成,也是亙久歷史的傳說變體。如果說,《聊齋》是淌人熱淚的才子佳狐、《西遊記》是鈸磬齊響的喜感武打,那麼東周時代的《山海經》就是展卷舒讀、大山大海的地理圖誌了。
來者不孤,我最愛的古代詩人陶淵明,也很喜歡《山海經》,並曾賦詩十三首以詠之: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陶淵明《讀山海經》之一
或許是受了《山海經》、《楚辭》、六朝志怪、唐代傳奇、宋元話本、明清小說等等的古典文學影響,我將「妖怪」看成先於人類的存在本體,是廣大博物的一員,是未知、未明、未現的化物,可以研究分析、探討共處,也是宇宙不可或缺的群體。
說起來,小時候怕鬼怕得緊,只覺得人可怕、死人變的鬼也可怕,而對妖怪卻毫不在意,這種想法到現在還難以蛻除。
因為「鬼」是「幽靈」。是人死後有著怨恨或執念,三魂七魄無法歸位,銜恨徘徊、立意復仇的飄盪魂魄。如同《韓詩外傳》所寫:
「人死為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則歸於風,眠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
最恐怖的不是本體(如果還有本體的話),而是意念。而意念,恰恰正是人最難拔除的。
當時曾經天馬行空的希望,衣櫥裡的妖怪會蹦出來(奇怪我期待的不是白馬王子),一起去探尋美麗的新世界、豐美的迦南地……這種潛意識的逃避與反抗,完全是十足的犬儒,而且只有心動沒有行動,注定要變成一場空夢。到了慘綠的年紀,無論如何不情願,我也不能神隱消失,只好回過頭來順應現實,掌心握住生存的沙,卻漏失了更多寶物。
從那時起,每天打招呼的妖怪老友,漸漸從我的生命中消失了。
日本的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1875~1962),曾經定義「妖怪是淪落的神明」。而它們又何嘗不是淪落的人類?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
它們明瞭我的改變,並不苛責,而我也自顧不暇,就像是後來的許多老友,即使彼此仍然牽念,卻疏於溝通聯繫,便漸漸變成了浮生水印。這些躲藏在衣櫥裡、蜷縮在光亮下、不被瞭解的異端,就這樣無聲遁去,回到容納一切的黑夜,回到被摒棄的自由自在去。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們兩兩相忘,一去多年。
前幾年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必須常常出差,有時投宿在豪華的五星級,有時只是在煙塵的小旅社,但讓我意外的是,常常會有人主動叮嚀:「記得開鎖前要先敲門、推門後要打招呼,這樣才能通知『它』,我們只是借住一下喔!」
剛開始我沒聽懂,之後卻有如雷電擊遍,潑身大悟──是它們啊!
生存的代價,是背棄過去。背棄那個以前用沉默來叛逆,就算自言自語,也始終堅持獨立視野的我自己。重逢異界老友,有如撿拾漂流的瓶中信,即使人生時而狂風暴雨、時而雨霽天青、時而花開遍地、時而荊棘繚繞……但是花了這麼多年,總算醒悟到--不需要曲從多數的成見,不需要裝飾無謂的粉面,不必要扭轉確認的夢想,不用去捆綁天生的意念……找回了失散多年的自己。
《妖怪玩物誌》這本書,算是我多年收藏的野人獻曝、兼讀書筆記。感謝異界妖物給予的啟示,更感謝始終支持我的至親好友(尤其是常被煩的弟弟)、文編曾淑正(本書催生者)、美編Zero、攝影陳輝明、大老闆王榮文,還有素未謀面、卻慷慨賜序的茂呂美耶小姐,在她的書中神遊多年,這次能透過文字結緣,心中有著深深的感謝。謝謝各位容納我的胡思狂想,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喜歡這些可愛的鬼怪。
據說萬古久遠以前,人類與妖怪的對峙,是光與闇的鬥爭,光明取得了勝利,也埋葬了黑暗。但是,當人類擎著文明的長槍,睥睨遠古的萬物,以為「黎明的曙光」擊敗了魑魅魍魎時,卻沒發現,自己的心也成了鬼物。
人類最終仍須承認,其實最需要黑夜的,是僅有白晝的靈魂。
獻給這世界及異世界,所有不甘於單一光色強盛主宰的妖物們。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