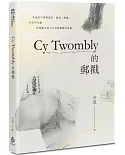我不在家
蕭蕭
一位三十多歲的朋友興致勃勃跟學生一起上篆刻課,有時在系辦看見她的半成品,堅硬的石頭被四片小木條夾緊,石面上已有灰黑的線條,約略可以辨識字跡,哇,真神奇,還不到一學期就已經有模有樣了,我轉著半成品跟她這樣說。
「周邊應該留下的框線,常常被我刻壞了!」
「那框線是必要的嗎?」
「對初學者來說,是必要的。」
「喔,那是一種規矩吧!」
雖然我不懂金石、篆刻,但每次看到印章四周的框線,很多人都可以掌握住線條的筆直與勻稱,總是佩服篆刻高手這種功力。就一個初學者而言,如果能在這四圍線條表現刻功,將線拉得直而瘦細,將轉折處顯現得方方正正,有稜有角,手勁就已值得稱述了。不過,也就因為每顆印章都這樣循規蹈矩,這樣恪守師徒世世代代沿襲下來的成規,我們反而忽略了這種基本功,彷彿印章生成就應該這樣。當然,我們的注意力都會集中在框線內的字,通常那是自己的姓名,「我」的具體代表,一種「承諾」、「信守」的力量。
真正篆刻的藝術工作者,絕不等同於刻印章的師父,刻印章師父重視的是技藝,獲得的讚譽是「巧匠」;篆刻家卻重視生命的體驗、人格器度的修持,往往濃縮而為幾個字,鐫刻在石彷彿銘記在心,譬如「上善若水」大家都熟知的老子的教示,或者大家不一定熟悉的「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諧趣時如「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長一點的「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或者「縱心物外」、「與誰共坐明月清風我」的瀟灑,甚至於佛教經典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改寫的對聯:「風調水順體泰心安」,往往令人會心一笑的同時,恍然若有所悟。所謂「匠心獨運」指的應該就是這樣的篆刻家,既有精湛的刻工合乎「匠」字,又有虔誠面對世界的開悟的「心」,可以是自成一家的「獨」門絕技,又能具備「運」斤用斧的格局與氣魄。
在我擔任香港大學駐校作家回國後,初學篆刻的這位朋友送我一顆原石,上篆「我不在家」。當時心中一凜,這麼白的一句話,不能貼在門口,免得小偷覬覦;不能存放在答錄機上,否則下一句鐵定是毫無創意的「請留話」。這樣直率的話應該向誰說,說了他會如何震撼,或者無動於衷?
「我不在家」,那我應該在哪裡?家,除了是親人共同生活的地方,還可能有別的含意嗎?譬如說,一個流派,或者一個修行的所在,一個可以放心的地方,「我不在家」,所以我在嘗試、我在接受考驗,沒錯,「我在路上」,可能是回家的路,卻也可能是在奔赴理想的旅程中。《世說新語.任誕篇》說到王徽之(子猷)住在山陰(浙江紹興)時,雪夜中醒來,喝酒,四望皎然(好一個四望皎然),因而在室內徘徊,吟誦左思的〈招隱詩〉,忽然想起隱居在剡溪(浙江嵊縣南方)、被稱為通隱(曠達的隱士)的戴逵(安道),雖然「巖穴無結構」,但「丘中有鳴琴」,雖然「荒塗橫古今」,但值得「杖策招隱士」,所以即刻夜乘小船前往,經過整整一晚才到,但子猷到了戴家門口卻又不向前叩門就回頭了,他說「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王子猷確實是「我不在家」,「我就在乘興而行的快樂中」最好的例子。同時,他也把戴安道當做「我不在家」的人,是的,戴不一定要在家,而我已來過,人生際遇,不就是這樣?這,也就夠了!
「我不在家」,這位三十出頭、送我石頭的朋友,到底要我領會什麼?
有趣的是,就在那幾天我卻接到詩人曾美玲的新詩集《終於找到回家的心》,換句話說,長期生活在家鄉虎尾的詩人,也有著「不在家」的感覺?那一顆「回家的心」又會是什麼樣的心,她如何找到,她會如何告訴我回家的途徑?
我急急打開曾美玲的詩集,設想這部詩集應該有一首主題詩〈終於找到回家的心〉,遍尋卻無著,詩集分六輯,六輯的輯名中沒有她,全部七十多首詩中搜尋不到這個題目的詩作。一般詩集的書名總以詩人最得意的一首詩為顏為額,至少也以某一專輯的輯名為書名,《終於找到回家的心》似乎不是這樣。這時,我靜下心來打開詩集閱讀,第一首詩〈雨中靜思〉,分成兩節,第一節寫「一場大雨驟然落下 / 各色大小傘花 /
擎起或輕薄或沉重的夢 / 在午後的街道上 / 流浪」。詩人在下雨時靜靜看著雨中行人,撐著傘,感受到那是不同的夢在流浪,眾多的人、眾多的心不在家。這是一種悲憫,悲憫流浪的夢何時回到自己的港灣——可以依賴的、溫暖的肩膀。
接著往下讀第二節,卻讓我心眼一亮,遍尋不著的「終於找到回家的心」終於找到了:
終於找到回家的
心,大雨過後
街道流成一條
清明的河流
帶走千萬噸虛無的慾望
家,一個可以安頓身心的所在,曾美玲所要找的「回家的心」:袪除了慾望,清明的心就是一顆可以回家的心。那樣的心,需要一陣大雨,沖刷虛無、沖刷慾望、沖刷汙穢,留下清明,有著清風之清、明月之明的清明,可以安頓身心。
《終於找到回家的心》是在一開始的第一首詩就揭示了這樣的清明上好之河,順著清明無慾望的河,那麼容易就找到回家的途徑。如果繼續讀這本詩集,沿著詩人的悲憫之心,即使「我不在家」,不也就是永遠「在家」嗎?即使他不在家,我心清而明,仍然與靜幽的明月清風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