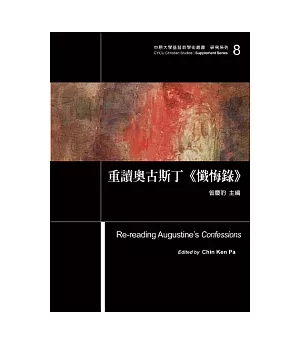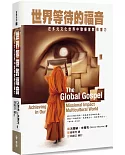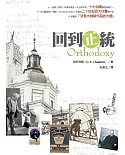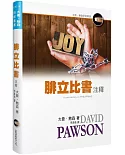序
奧古斯丁的祈禱與眼淚—重讀《懺悔錄》∕曾慶豹
我愛你已經太晚了,你是萬古常新的美善,我愛你已經太晚了!你在我身內,我馳騁於身外。我在身外找尋你;醜陋不堪的我,奔向著你所創造的炫目的事物。你和我在一起,我卻不和你相偕。這些事物如不在你裡面便不能存在,但它們抓住我使我遠離你。你呼我喚我,你的聲音振醒我的聾聵,你發光驅除我的幽暗,你散發著芬芳,我聞到了,我吸取你的氣息,我嘗到你的滋味,我感到饑渴,你撫摸我,我在你熾熱中想望著你的平安。(Confessions,
X:27)
要永遠記得,要讚美上帝。他要我來幫助你們,並不是我自己要來的。……當你們認為親眼看見我吃東西的時候,實際上我什麼也沒有吃,你們所看到不過是擬像。(次經《多比傳》十二17–19)
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1953年的作品《懺情恨》(I Confess, [讓我們模仿紀傑克(Slavoj zizek),從電影開始吧!紀傑克編輯出版了一本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儼然成了希區考克電影的專家。]),在法庭上為了挽救神父,證明兇殺案發生時他不在場,有夫之婦不得不公開自己與神父過去一段難以啟齒的交往過程,承認自己與神父的曖昧關係。以為不坦白就無法獲得寬恕,但又卻使自己和神父身陷囹圄,使原來的複雜案情更添複雜。到底該不該坦白?坦白之後的心靈是否因此平靜或更起伏不定?什麼是懺悔的經濟?
一、
《懺悔錄》(Confessionum)為我們開啟了近代的「笛卡兒主義」,又啟迪了廿世紀「諸現象學運動」,包括胡賽爾、海德格、阿倫特、呂格爾、德希達、馬西翁、卡布托等人都分享到了此書的睿見。在西方思想史上,希波主教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不僅僅被理解為基督教神學家,他的思想地位與柏拉圖、康德並列,奧古斯丁以後,沒有一位思想家敢忽略他的影響。提到奧古斯丁的著作,學界無例外地會認為《三位一體》(De Trinitate)、《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和《懺悔錄》並列為他所有的著作中最為重要的三部,堪稱作「神學三部曲」。而且,又以《懺悔錄》被說成是最為廣泛被人閱讀和討論得最多的一本,這說明了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是理解為奧古斯丁的「自傳」[關於奧古斯丁的「生平」,我們可以從《懺悔錄》來認識他的「前傳」(46歲),我們也可以通過繪畫來認識奧古斯丁,最完整且經典的代表作,無疑的,即是畫在意大利托斯卡尼區的聖吉米納諾(San
Gimignano)的The Church of Sant’Agostino內的東邊聖堂的十七幅(分成三個部份)奧古斯丁一生重大的事蹟,作者是Benozzo Gozzoli,此作品完成於1464–65之間]。也不是一般意義的所謂「思想著作」,更不僅僅是作為貫穿著對於他其他著作的導引性理解。
《懺悔錄》寫於397至401年間,全書共分作十三卷[(卷一)罪∕告白∕童年;(卷二)成長∕偷梨;(卷三)旅行的開始;(卷四)論友誼;(卷五)從迦太基到羅馬;(卷六)重新理解基督教;(卷七)新柏拉圖主義∕真理∕信仰與理性;(卷八)皈依∕拿起來讀;(卷九)新生∕母親莫妮卡之死;(卷十)論感官∕論記憶;(卷十一)論時間;(卷十二)論聖經詮釋;(卷十三)論創世。],後面三卷明顯偏離了原來「懺悔」的意識,變成是對創世記第一章的解釋,因為在撰寫《懺悔錄》之同時,奧古斯丁正在寫《創世記疏解》,對於他的「神學思想」感興趣的人會重視後三卷的內容。可能,卷九即是《懺悔錄》的最後一卷,我們應該停在這裡,但是卷十卻又是全本《懺悔錄》最有意思的一卷,要想綜合性地把握並作為入手理解《懺悔錄》的思想準備工作,應該從卷十開始,卷十就像是《懺悔錄》的「前言」。
《懺悔錄》不屬於「歷史哲學的書寫」(《上帝之城》),也不是「解經書」(《詩篇釋義》),也不是「教義學」或神學之辯(《論三位一體》、《駁伯拉糾派》)。《懺悔錄》(397–401)是一部「祈禱文」[卷十至十三除外],也是一部「讚美詩」[全書對聖經詩篇的引述極為頻繁,奧古斯丁著有《詩篇釋義》,其篇幅是《上帝之城》之一倍厚]。
一個人的「懺悔」是向上帝「懺悔」,我為何要去讀他人的「懺悔」?一位主教為何要「公開」他的過去?純粹為了寫一部「回憶錄」或「自傳」(autobiography),或是想留下什麼,希望人們對他的過去有更多的認識?一部「個人的懺悔錄」何需認真對待,難道只因為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奧古斯丁主教,一位被視為「正統」的教父嗎?[盧梭的《懺悔錄》是「啟蒙主義者的瀆神」、托爾斯泰的《懺悔錄》是「文學式的矯情」]
按拉丁文Confessor的意思,意指「見證」(witness),而且是自希臘文那裡翻譯過來帶有殉道(martyr)的那種公開意義的「見證」,所以有人把《懺悔錄》翻譯成《證言》(The
Testimony)。懺悔在祈禱的語式中是一種「坦白」,或者是「公開」自己的罪行。首先即是「坦白地說出」這個動作,而種種「說出」的都是過去的;其次,說出自己的罪行就已經是某種責罰,也是抵罪(expiation)的開始,這種坦白地說出正是對自己進行拷問的方式,即要求記憶起自己的罪行;最後,對於自己的過去必須有所了解與接受,不管是痛苦的或快樂的,形成一種經濟學:「不願坦白的痛苦」和「坦白形成對靈魂的寬慰」,悔罪即意味著尋求寬恕。[Confession(懺悔)和penitence(贖罪)在法文中是近義詞,兩者意思又有交叉,都有因為犯下了罪過而表示悔恨,請求上帝寬恕的意思。但是Confession更強調認罪和坦白,通過坦白來獲得寬恕;而penitence則可能包括一些行動,如苦行、自我責罰等。見傅柯《不正常的人》中譯者註,185]
《懺悔錄》第二卷一開始說:「我願回憶我的過去的污衊和靈魂的縱情肉欲,並非因為我流連以往,而是為了愛你,我的上帝。」(II:1,以下引文採用徐玉芹譯本,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一個人的回憶何以是「為了愛」,「愛上帝」與「公開過去的污衊和靈魂的縱情肉欲」有何關係、一種怎樣的懺悔意識使我們以公開自己過去的「不是」來表達對上帝的愛?懺悔與愛、公開的關係是什麼?如果上帝早已知道這一切(X:2),人又何須向祂坦白呢?坦白可能與知道(知識)無關,或許它更多的是喚起一種責任(responsibility):坦誠面對並回應(response)自己之所做所為。
祈禱不是以「什麼是……?」作為開始的,奧古斯丁雖然也問到:「我的上帝究竟是什麼?」(X:6),但不同於哲學的「什麼是……?」,他以「愛」作為開始,一種「不得不」的愛。不同於哲學本源地提問,問:「……是什麼?」,當開始了哲學,卻在「問」中脫離了經驗;換言之,祈禱之前,先預設了一種「關係」的存在,這樣的「關係」使得祈禱得以可能,因而祈禱一開始就不是主體性的,愛從來就不是一個沒有對象或不預設了存在著一位他者的愛。奧古斯丁把懺悔理解為「為了愛你(上帝)」(II:1)即為了「回應」,回應於一個早已洞悉人心底蘊的上帝,如果「愛」是作為回應的方式,就與責任聯繫起來。
懺悔是對欲望的揚棄嗎?那麼,沒有欲望的愛又會是什麼?[阿倫特在Love and St.
Augustine中討論了奧古斯丁將愛置於斯多亞—伯拉圖式的欲望(craving)和基督教的回憶中做兩難性的處理]奧古斯丁表達了他對上帝的愛基於一種「匱乏」,這正是欲望的誘餌,「除非安息在你懷中,不然我的內心無法獲得安寧」(I:1)。懺悔表面上看來是一種限制欲望的表現,但是它所限制的是主體自己的欲望,而非源於他者的欲望,這種匱乏是從一個能指到另一能指的轉移,通過「他者」賦予了匱乏以意義,這種欲望不是尋獲滿足,而是對於「不滿足」的「滿足」。奧古斯丁把這種欲望理解為一種來自於上帝的暗示,暗示著人的有限,因此是神聖的足跡。愛即是欲望的不可能的化身,愛即是愛那不可能者(The
Impossible)。
我們和奧古斯丁一樣困惑:「當我說愛上帝的時候,我愛的是什麼呢?」(X:6, quid ergo amo, cum deum meum amo)
「愛上帝」究竟是「愛的是什麼」,只能意味著我所愛的上帝不是一種以「某種」的方式到來的上帝,作為他者,上帝永不是為我們所愛,相反的,我們是為祂所愛[源於上帝的聖愛(caritas)],是上帝愛我們,上帝以愛的方式臨在[阿倫特把這種愛解釋為「鄰人之愛」,所以奧古斯丁在上帝、自我與鄰人之間構成「愛的秩序」,即一種友愛。奧古斯丁在《懺悔錄》處處流露出「友愛」(friendship),我們要記著的是「別人的好」]。
二、
也許,我們必須改變傳統那種「神學」或「教義學」式的解讀。過去神學家由於職業的需要,或故弄玄虛地搬弄神學或哲學語彙來閱讀《懺悔錄》,某個程度可以說違反了《懺悔錄》的題旨[將聖經或教父著作當作「系統神學」的素材或是教義學資源,實為現代性之後的事]。
我們要談論《懺悔錄》的祈禱語式、回憶、愛、友誼、寬恕、哭泣、死亡、母親、視覺、欲望、哀傷、離別、痛苦等作為我們思考的對象,還有一個顯著的現象,《懺悔錄》中大量地引述聖經,其中詩篇佔了極大的篇幅,為何祈禱與讚美有如此緊密的關係?
事實上,我們不應該期望、也無法得到問題的最終解答,理由是《懺悔錄》這部書本身即是不斷提問的過程,它探詢的正是奧古斯丁理解自己不斷生成、變化的事件,其中許多的遭遇和思考竟是些不確定性的東西,在祈禱之中向上帝開放他對事物的看法,同時也揭示他自身的無知。這是一種「祈禱的經濟學」。
首先,《懺悔錄》是一種通過回憶的方式去觀看自我的過程。人如何觀看自己?自我觀看與一種懺悔的祈禱語式有何關係?事實上,觀看作為一種生活,它開啟了生活以外的各種可能,不管回憶作為一種觀看的方式是否準確,但是對過去的回憶總是一種觀看,一種「此時此刻」的、非語法或邏輯般的觀看,甚至它與時間的關係變得模糊、變得難以理解。「時間」(X:17,
20)不正是經常被人拿來討論《懺悔錄》的主題之一嗎(Paul Ricouer: Time and Narrative,
chapter.1)?奧古斯丁對時間的困惑不是哲學性的,而是祈禱性的,不是通過論證,而是通過回憶。回憶是人的一種存在向度,正是這個從人的存在來理解時間、從懺悔的語式建構出來的時間意識,給廿世紀的現象學一個關鍵性的切入點[胡賽爾在《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中坦言其對時間意識的分析受到奧古斯丁的激發,甚至對《懺悔錄》卷十一做過眉批和注釋;海德格在1920–21年間開過一門討論《懺悔錄》卷十的研討班,成了《存有與時間》的起源]。沒有時間,就無需懺悔。
通過「記憶」,奧古斯丁的時間是一種「凝神」(intentio)的狀態,是指人在自身又躍出自身的視域中看過去、現在與未來,因此過去、現在與未來不是靜止的[這裡的時間並不是胡賽爾的知覺意識經驗的retention, intention,
protention],而是「溢出」(ek-statische)的,但是這一切都在懺悔的意識中進行,所以是收攝心神、專注於上帝或永恆的一種「記憶現象學」。
《懺悔錄》的書寫之所以可能,正是依靠「記憶」這個活動,奧古斯丁把記憶看作是一種「影像」,而且這些「影像」是通過感官得到的(X:8)。相對於「記憶」,那就是「遺忘」,奧古斯丁自己問到:「遺忘究竟是什麼?」(X:17)若遺忘,就沒有記憶,但遺忘又是如何記起來的呢?我們真的忘記還是記起了某些東西?記憶究竟有多真實?值得注意,忘卻並不是不存在,它僅僅是以沈默而非公開、非坦白的方式存在,記憶和忘卻形成了懺悔的辯證,是關於「坦白與沈默」的辯證。人類似乎總是在記憶和忘卻之間建構、摧毀,「解構」的思想正是對此「遺忘」產生興趣開始(尼采、海德格、德希達),當然我們還想到「精神分析學」[弗洛依德晚年也寫了一本懺悔錄:《摩西與一神教》,這是一種經過現代性以後的書寫方式,把自己隱身於巨大的迫害之下,企圖抹除與自己任何相關的記憶,通過記憶的抹除,抹除身份,即抹除認同,即為現代精神分析學的另一種書寫:為了忘卻,而非記起]。
《懺悔錄》最深刻之處即是存在著一個「我」:「但現在我在你面前,用這些文字向人們懺悔現在的我,而不是懺悔過去的我。」(X:3)
《懺悔錄》努力呈現這樣一個「我」:一個通過「懺悔」的方式來呈現一個「我II」,正是這個「我I」使這種活動得以進行,正如德希達說到:「一個畫家考慮他自己,被吸引於、關注於那形象,然而那形象又在自己的眼前消失於深淵之中時,他絕望地試圖再次捕捉自己的動作便已經是一種記憶的活動。」(Derrida, Memoirs of the Blind,
68)換言之,想要呈現的「我II」,正是那個「我I」,所以就必須不斷地回憶,不是逼近於「我II」,當然也不是「還原」,關鍵在於它所展開的「視域」,是不是如李歐塔(Lyotard)所言的:「奧古斯丁是為了避免遺忘而書寫,恰恰他所遺忘的正是自己。」(Lyotard, The Confession of Augustine, 83)。
記憶是一種源於上帝給我的,所以它是恩典而非人的能力,因為懺悔的記憶主要引自於「在你面前」(X:2, 17)。在上帝面前的我,通過了對現在的我的遺忘,記憶起過去的我;過去的我如此清晰不是源於過去,而是源於記憶起過去的我的「現在的我」,這個「現在的我」正豎立在「你面前」,一個我傾聽祈禱和讚美的「你」的面前。
是我,又不是我,或者是另一個我。懺悔源於看到別人看不到,只有自己看到的罪惡,或不通過回憶就無法看清的我;坦白是為了獲得寬恕,為了得到寬恕必須記憶起自己的過犯,無法記起的,就無法獲得寬恕。要說出自己的罪(寬恕),必須承認自己的罪(懺悔)。
所以奧古斯丁說:「在你眼中,我對我自己是一個不解之謎,這正是我的病根」(X:33),我們通過奧古斯丁的書寫發現,「懺悔」這種獨特的語式正是一種「因為我(I)所做的,我(II)不知道」。基督教的懺悔意識恰好不在於「知道」自己的什麼,相反的,犯錯是因為「無知」,即是「不知道」。正是「懺悔」符合了其根本的含意:無知的犯錯,所有的犯錯即是出於這樣一種無知,無知或不去知道都是一項罪,懺悔即是避免無知,儘管不知道,但必須坦白承認自己「無心之過」[「無心之過」仍是一種過錯,而非現代「求真意志」的犯罪學之脫罪理由]。一切之過,莫過於「無心之過」,正因為此一「無心」而非「有意」,更說明了懺悔之必要,向著上帝懺悔而非向著自己「改過」。
三、
我們可以發現,《懺悔錄》通篇都在呼求「主啊」、「我的上帝」這個專名,究竟這個名字代表了什麼?為什麼懺悔必須是通過我們呼求祂作「主啊」、「我的上帝」才是可能的呢?懺悔可以不呼求「主」的聖名嗎?人向一個「名字」祈禱是如何可能的,尤其是這個「聖名」,懺悔之徒是如何認識到這樣的「不可能性」,也許,向一個「名字」祈禱是可笑的,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懺悔如果是為了激起我們對祂的愛、對祂的稱頌(XI:1),我們對一個「名字」的愛和稱頌意味著什麼?什麼樣的「名字」可以成為我們去愛、去稱頌的呢?為什麼是「主」這個聖名而非別的?任何一種名字被呼喚,都代表著一種欲望,祈禱是一種「拯救聖名」(saving
the Name),將「名字」給了懸置,它將我們的欲望擱置於懸而未決之中,這樣的「主」是一切,也可以是空無,如德希達所言:「它總是離你而去,卻又從不遠離。」(Derrida, ‘Post-Scriptum,’ in On the Nam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上帝的名字,是一個「公開」的名字,不屬於任何人「專有」的名字;上帝的名字,當我呼喚祂,通過祈禱的語言,祂成了我召喚「作為秘密的我」的上帝,一個屬於我的「專名」(否定神學),所有的秘密繫於此一「專名」中。因為在祈禱的語式中,「呼求」不是呼求某物「在場」[形上學],而是「給予」[神學],即作為禮物般的「給予」,一種滿溢的到來[Jean-Luc
Marion的禮物現象,with/out]。
上帝是一個拯救的名字(Sauf le nom),這是帶上了否定神學印記的名字;上帝的名字並不是可以理解的東西,而是一個需要回應的名字。這即是祈禱中的「呼求」所帶有的現象學意義。奧古斯丁對上帝的名字的呼求,不是呼求某物的「在場」,而是呼求相伴,在祈禱中,一種來自於「他者」的相伴,是對呼求的回應,也是對於「在場」的超越。
《懺悔錄》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就是關於真理的問題。奧古斯丁在第十卷開頭說到:「我願意在你面前,用我的懺悔,在我心中履行真理;同時在許多證人之前,用文字來履行真理(facere veritatem, to bring forth the
truth)」(X:1)這裡注意到「書寫」這個動作作為對「履行真理」的理解,而非被降低為認知理性秩序內的啟示、解釋、和告知,奧古斯丁想在書寫中懺悔(in litteris, per has litteras)(IX:12, 33; X:3,
4),書寫即是銘刻於將來的書寫,書寫不僅僅是對過去的書寫,由於與記憶的問題有關,在已經發生的事上,通過記憶銘刻於將來,為此向教友們做見證。於是,書寫、記憶、懺悔成了一種三位一體的關係,奧古斯丁的「真理」問題在此形成一種獨特的書寫形式[履行真理的獨特語式。阿倫特在奧古斯丁那裡發展了她的「行動哲學」]。
德希達說:「自畫像者並不告訴人們什麼,他只是承認自己的過錯,並要求寬恕」(Memoirs of the Blind,
117)。上帝原已知道一切,因此懺悔並不是在告訴上帝任何事情,好像上帝不知情一般;任何的懺悔都意味著尋求「寬恕」過錯,但是尋求「寬恕」的過程也是在此「過錯」中,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即是表達了這樣一種寬恕,但是,它並不是為了什麼事情而求得的寬恕,而是一種不為任何事情而求得的寬恕。事實上,所有已然發生的事情都是無法挽回的,一切都已經過去,重提陳年往事似乎也於事無補,所以懺悔還是否必要?為了回憶的懺悔,或為了懺悔而回憶,表面上,奧古斯丁說了他許多犯罪的「事證」,正是他把記憶理解為此時此刻,所以,這些懺悔的情節要是成立,其唯一的可能性即在於「無法被寬恕」,一切的懺悔都是指向這樣一種「寬恕的不可能性」,以及真正的「寬恕」即是「寬恕那不可寬恕」的[德希達]。可見,奧古斯丁所有的懺悔和「犯罪事證」,並非直指事物本身,一切都在「延異」中產生了其他可能的含義,這是奧古斯丁最為推崇的「寓意解經法」(林前3:1–6),這種方法應用於祈禱之中最為明顯和直接。
全本《懺悔錄》運用著聖經的「寓意」手法,都是一種在給定的意義中尋找其他可能性,這裡也引伸出《懺悔錄》暗示著處處充滿著「不可靠性」,懺悔很難不成為某種「欺騙」,「公開的欺騙」,因為連奧古斯丁本人都覺得「我無法證明我所言的真假」(X:3)。這裡的意思至少表明三方面:說出的不一定是真的、說出真相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在履行真理。
正是如此,懺悔意味著是一次又一次地暴露自己無可救藥的犯錯,必須說出而非不說,不是無法說出,而是不知說些什麼是適切的或恰當的,說出之後並非供人歌頌和贊許,因為懺悔更多是一種自我解構,自我只能通過「他者」來呈現,自我永不是「同一性」的,因為任何的欺騙最難克服的即是自我欺騙[也是笛卡兒最難對付的「懷疑」:惡魔論論證],否定自我欺騙的存在就必然是一種「悖論」,所以這是一種無法克服的「欺騙」,正是這種再一次的犯錯為我們打開另一種可能性的條件,如果我們並不是克服「欺騙」而通往真理,奧古斯丁等於是「公開說謊」的人,其本身即是「帶面具說話」的人,往往一個追求真理的人正是「隔著某物」說話(參見尼采〈真理與謊言之非道德論〉),祈禱的狀態即是一種「隔著某物」在說話的方式。
事實上,《懺悔錄》卷十是作為一至九卷的「前言」或「導言」,奠定了我們對於全本《懺悔錄》的思考與理解。《懺悔錄》卷十分兩個部份,8節至29節論及「記憶」,30節至42節談到「感官」,說明了身體的活動可分作兩部份:記憶與感官,懺悔不是通過感官而是記憶,這裡雖然有柏拉圖思想的影子,但不是認識論的而是祈禱的。由於祈禱本源地來自於回憶,沒有回憶,祈禱就不可能。記憶,作為事實本身,包含了「忘卻」,「忘卻」在此恰好是指某種已然存在的東西,回答懺悔之可能性即在此;懺悔即是回憶,回憶之具體內容恰恰好所指的正是身體的活動。
《懺悔錄》中有關「身體告白」也是一個有趣的題目,這個問題當然是因為傅柯「主體詮釋學」和「性史」所引起的。奧古斯丁通過了「身體的活動」(誘惑、好奇心、貪心、虛榮、同情……(X:30–42))來進行懺悔,「身體」在懺悔的過程中不僅僅是被當作否定的對象,同時卻又是一種「發現真相」的途徑,而且奧古斯丁對於上帝的讚美又避免不了使用身體可以感覺的方式來「體驗」上帝(XI:1)
(X:27),到底身體與懺悔的體驗有何關聯?「愛上帝」如果不是一種欲望使然,那又是什麼?身體為何如此的神秘,以至於成了與「愛上帝」對立的東西?可見,在懺悔的身體告白中,身體有多神秘,上帝就有多神秘。
傅柯把懺悔理解為一種古老的思想,它貫穿著整個西方思想史,以「關心自己」為實踐方式,一方面使自己成為對象,一方面則是將自我技術化,前者將注意力朝向自己與非利己主義形成悖論,後者即是以自我規訓的方式達到自我控制和改變自己(Foucault,《主體解釋學》,12)。「懺悔是一種說話行為,主體通過懺悔在證實自己是什麼時候與這種真相聯繫,置身於一種依附他人的關係中,同時又改變他與自身的關係」(《主體解釋學》,386),所以懺悔與身體、愛欲、真理、自己(auto)、說真話等有關。
傅柯分析parrhesia這個拉丁字「坦白」的意思時發現,這個字還有libertas(自由)的意思,是開放讓人說話、說出他需要說出的話、說出他想說出的話,它意味著說話主體的一種道德品質的要求(《主體解釋學》,381,
389)。我們不能忘記奧古斯丁這位「修辭學教授」的身份,「修辭」在此並非指一種文學或說話的技巧,它更多的是一種與自我認識和自由有關,因此,如何通過這種語言的訓練來達到對主體的技術化正是《懺悔錄》最隱蔽的問題,這與祈禱和修身這種宗教生活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係。
懺悔意味著在上帝的注視底下,內心世界的時間被現在激活,對過去的自己進行述說,以作為皈依上帝的見證。《懺悔錄》不斷地討論眼睛,不管是「流淚的眼睛」、「目欲」(犯罪的看)或「無形的眼睛」(信仰的真光),隱身在這一切背後最巨大的眼睛即是「上帝的眼睛」,這才是形成懺悔意識,以及使懺悔得以可能的根本條件。因此「我非但不能把我隱藏起來,使你看不見」,「不論我怎麼樣,我完全坦露在你面前」(X:2),正是一切在祂的鑒臨之下變得無所遁形,懺悔也就變得「不得不」。
尼古拉庫薩(Nicholas of
Cusa)說「上帝就是眼睛」,關於我的存在與上帝的凝視,他做了極為經典的表達:「所以我存在,因為你在觀看著我;倘若你把自己的視線從我身上移開,則我將不能存在。」[《論隱秘的上帝》,89,76]懺悔即是源於上帝的觀看,「眼睛所至,便是愛之所致」,上帝凝視著我,上帝的目光是愛的目光,因此祂的觀看就是愛[《論隱秘的上帝》,76,87]。凝視即關愛,而非「他人即地獄」。
奧古斯丁說:「我愛上帝,是愛另一種……。」(X:6)以上種種的說明,可以總結為一句話:奧古斯丁在《懺悔錄》所講述的是一個人的故事,但是,那是一個關於他自己成為了一個問題的人(I am become a question to myself)的故事。奧古斯丁正講述著「另一個我」(X:30)嗎?是他本人,抑或上帝?
四、
嚴格說來,《懺悔錄》到卷九就結束了,即結束於母親去世的事件上,可能《懺悔錄》的寫作真正的起源來自於莫妮卡之死。《懺悔錄》也是通過母親的死亡來哀悼自己的過去,所以莫妮卡的死是一個關鍵,由她引起了奧古斯丁對所有過去的追憶,《懺悔錄》即是向上帝的懺悔也是向死去的母親的懺悔。母親與奧古斯丁的親密關係遍滿於《懺悔錄》每個細節中,母親的存在宛如上帝在世的代表,一切使奧古斯丁轉向上帝的關鍵都來自於母親的祈禱、母親的哀傷和焦慮,母親的逝世使他頓時失去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源於母親。卷九第十節即一個神秘的「奧斯蒂亞經驗」(IX:10),這是奧古斯丁與母親離別前最為深切的交談經驗,一種真正的「永別」,儘管無數次都是奧古斯丁別離了母親,這次卻是母親與他道別,而且是「永別」。因此是母親引發他的懺悔,引發對過去的追憶,通過追憶作為與過去一切的「永別」,值得注意的是,那是他接受洗禮後不久就發生的事,那年他三十三歲,莫妮卡最後是了無遺憾般地與奧古斯丁永別了。
《懺悔錄》是一本哀悼母親死亡之作,真正的關鍵是母親的死。[59歲的德希達在尼斯面對著垂死的母親Georgette Safar
Derrida,仿傚了奧古斯丁寫下了五十九章自傳體的獨白:Circumfession《割禮告白》。德希達在奧古斯丁大街長大,這是以他的同鄉名字而取的。德希達公開了他的身份和信仰:他是最後一位猶太人,道出了自己真正的名字Jackie,以及一直以來旁人都不曾知道的名字Elie,這屬於母親給予他的生命,一個禮物的記號。這位「渺小黑皮膚的阿拉伯猶太人」流著眼淚對我們說:我在祈禱和眼淚中公開了秘密,要他人在閱讀他的書時望到他的眼淚,讓他們知道我的一生是在一連串漫長的祈禱中度過。Circumfession,
38–39, 83–84]《懺悔錄》寫於母親逝世十年之後,也是他正式當上希波大主教的第二年,人生走到如今,《懺悔錄》作為告慰天上母親的靈魂,也許是奧古斯丁最大的動力所在,還有什麼比母親對他的影響更加巨大呢?還有什麼比母親對他事奉上帝一事更為操心呢?《懺悔錄》全書處處「流著淚」祈禱,宛如母親為他所流的淚一般。
毫無疑問的,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是一部告訴我們關於「眼睛」的史前史的著作,懺悔意味著「看見光」,但他指出的例子中,竟是一群「失明」的人,包括多比[一個失明的多比是如何教誨他的兒子多比雅]、以撒[以撒在盲目的情況之下將祝福給了對於祝福做出選擇的雅各]、雅各[這些人都在奧古斯丁的書中出現過,但他似乎忘了保羅也是失明的],上帝打開了他們那雙「無形的眼睛」(invisible
eyes)看到了「真光」。(Memoirs of the Blind, 117–119)這是一種盲者獨有的視域,只有他們才「用對」了眼睛,看到應該看的東西,即上帝。
奧古斯丁祈禱說:「我的心如何向你哀號,我的眼睛如何熱淚盈眶」(X:37)。德希達認為《懺悔錄》是一部「眼淚的書」,我們可以在書中處處找到流淚、哭泣、哀哭的經驗。(Memoirs of the Blind, 126. [德希達還要我們「看,這個人」(Ecce Homo):尼采,特別是他在杜林抱著馬哭泣的那軼事])
眼睛無法看到自己,眼睛在流淚的時候證實了這件事;眼睛失去了凝視作用,開啟了它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說到底,懺悔絕非自己看見自己,柏拉圖說明了眼睛必須看著一個客體,通過看著它,眼睛才看到自身。這是一雙「他者」的眼睛,它不是我自己的眼睛,一旦眼睛看向他,就將看見自己在看[如拉岡的「鏡像」]。由於眼睛無法看到自己,這種自我觀看,正是看到我是盲目的或瞎眼的。
德希達說他流淚時,他不知道究竟是自己還是母親在哭泣,不同於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的「死亡」是自己的死,德希達面對著母親,是他者的死,他者的死正是我的死,是一種給予,正如泰勒(Mark
Taylor)所言的‘(m)other’。所以,說奧古斯丁流淚,不如說是莫妮卡的眼淚,是莫妮卡的流淚與祈禱換得了今日「喜悅的淚水」。哭泣是一種「失明的狀態」[據說聖法蘭西斯因流淚過多而失明],眼淚是盲目經驗表現的最高形式。眼淚是只有女性[Monica/Georgette]能以保持盲目所提供的「視域」,如德希達所說:「眼光的實質不是視力而是眼淚,……揭示性或啟示性的盲目,那顯露了眼睛的真真實實的盲目,是為眼淚遮蔽的凝視。」「當淚水遮蔽了視力的那一刻,它們揭示了眼睛真正的功能。……眼睛的終極目的是使視力探尋而非觀看,關注祈求、愛、歡樂或悲傷而非打量或凝視。」(Memoirs
of the Blind, 126–127。參見耿幼壯《聖痕》第五章)
如果《懺悔錄》的祈禱和眼淚即是對於母親的哀悼,同時也在哀悼自己,那麼,母親的死與自己的死是否為同一件事,由於過去充滿著母親的回憶,伴隨著母親的死去,也帶走他的過去,是要忘記母親還是忘記自己的過去,奧古斯丁是向母親和過去的自己道別,抑或是重新記起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