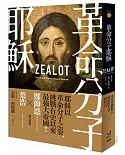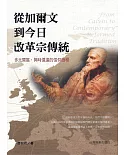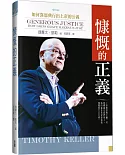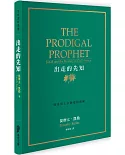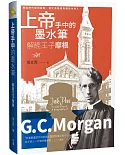總序
自從「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在明朝天啟五年(1625 年)於西安出土以後,知道基督教在唐朝貞觀九年(635 年)即已到了中國。那時,「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金像,來獻上京。」而且一度還相當興盛,「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後在武宗會昌五年(845 年)終因一道嚴厲的諭旨而被取諦。其間雖有二百一十年的歷史,並未生根。
後在元朝時再捲土重來,稱為「也里可溫教」,然則因元朝為異族人統治的天下,而傳道又不得法,如強佔鎮江金山寺為十字寺等,僅曇花一現。等元朝結束,也里可溫也隨之而亡。到了明朝,西方傳教士帶著宣教的熱忱,再度叩關,終因中國的門戶封閉而不能如願,以致有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求救和渴望的呼聲:
「磐石呀!磐石呀!甚麼時候可以裂開呢?」
磐石終有裂開之時,主豈有難成之事?到了適當的時候,主自己打開門戶,雖然是千辛萬苦,有時甚至要犧牲性命,但在主裡的犧牲不是沒有報酬的。最後主聽了他們的禱告,終於如願以償踏上中國土地,范禮安、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居然開拓了中國工場,從明末到清初。天主教的這些飽學之士留給中華文化不容小覷的著作,堪稱得上要好幾代人才可能消化得了。
新教則於一八○七年由「倫敦傳道會」差派馬禮遜(RobertMorrison)來華宣教,後因中國政府不准傳道,而轉赴澳門。他經過千辛萬苦,終能如願以償;之後的傳教士,都接繼著馬禮遜的腳步,特重著述、譯著之工作。其間,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就是新教創辦了《萬國公報》,英文的全名為The Globe Magazine and A Review of
theTimes。實際上,在《萬國公報》出版之前,早有傳教士發行之《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遐邇貫珍》、《中外新報》、《六合叢談》等的發行。根據華文書局編輯部所撰〈景印《教會新報》、《萬國公報》緣起〉:
「中國教會新報」(The News of Churches, or The Church News)於同治七年七月(1868 年9 月)創刊於上海。發行人為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英國教士慕維廉(William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佐其撰述。每週一刊,每刊四張(八面)……。主要內容,刊載中國基督教事務,特別是闡揚教義,譯述聖經故事,報導教會動態,以及辯難宗教問題。間或記載中外史地,科學常識,及中國教育消息。前後發行六年,共三百期,至同治十三年改為《萬國公報》,《教會新報》之名不復存在,然其組織更加擴大,其內容也更加充實。」
《萬國公報》自《教會新報》最後一期接續發行,仍由林樂知主編,形式內容,稍作改進。連續發行九年,共九卷,略作停頓。至光緒十五年正月(1889 年2 月)以歸併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Society)發行,改訂新章,增大篇幅,每月一刊,林樂知仍主時其事。至其內容宗旨,雖然仍不脫傳布基督教義,溝通教會消息,然亦負擔起推廣西學之責;於西洋科學知識,史事人物,國家現勢,均有涉及。其最足以歆動中國朝野士大夫之報導,則為中日甲午戰爭之際所刊載之中東戰紀。《萬國公報》遂引起朝野官紳之廣泛注意,一時視為新知識之重大來源。凡關於民族自立、主權完整、政治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啟發。嗣後變法維新運動,很顯著頗受其鼓吹之影響。而並時學會林立,各地紛紛創辦報刊,卻又是形式上之重大摹擬。
在民國時期,天主教發行著名的《益世報》,被當時譽為四大報刊之一,與《大公報》、《申報》和《民國日報》並列,除此之外還有《聖教雜誌》等。新教方面必較知名的有《真理與生命》、《青年進步》、《文社月刊》、《天風》等,許多的代表性著述都是從這些報刊雜誌開始的,進而也擴大成了出版各種大小不少的書籍的基礎。
另外必須一談的是上面提及的廣學會。廣學會於一八八七年成立,對基督教文化事業之提倡,不遺餘力,尤其在華人出版界有不可磨滅的功勞,它比華人出版界的樞紐商務印書館還早十年。廣學會與基督教青年協會相繼出版了不少好書,尤其在民國時期,基督教青年人材輩出,都留下了不少值得肯定的著作。天主教方面則是在土山灣印刷出版了不少有價值的著作。
本委員會鑒於時機之難得,遂主編這套叢書,從景教開始直到一九五○年,以廣義之基督教定義蒐集一千三百年來漢語創作凡百餘本,名為《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成》,藉以對歷史負責,也以此來回饋讀者。
本委員會名單如下:
王成勉、李金強、李亮、李雋、吳昶興、邢福增、杜樂仁、房志榮、周聯華、查時傑、翁傳鏗、陳方中、郭明璋、曾陽晴、曾慶豹、黎子鵬、潘鳳娟、蘇德慈(以上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周聯華 敬識
編者序
本選集名為《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選粹》,收編了六部十九世紀漢語基督教敘事文學作品,包括米憐(William Milne)的《張遠兩友相論》(1819)、理雅各(James Legge)的《亞伯拉罕紀 》(1857)、賓為霖(William C. Burns)的《正道啟蒙》(1864)、白漢理(Henry Blodget)的《亨利實錄》(1865)、胡德邁(Thomas H.
Hudson)的《勝旅景程》(1870)及楊格非(Griffith John)的《紅侏儒傳》(1882)。
這批作品分為創作和翻譯兩大類,前兩部屬於創作或編著的作品,後四部則屬於翻譯作品。按照寫作的語言來看,也可分為文言及官話兩大類,除了《正道啟蒙》和《亨利實錄》採用了官話外,其他作品皆以文言文書寫。每部被選收的作品皆具有代表性及獨特的價值,有的開創了基督教敘事文學的先河,有的翻譯特色顯著,有的具有重大的文獻價值,有的發行量高、出版壽命長。以下將逐一介紹。
《張遠兩友相論》乃首部基督新教傳教士創作的小說,以問答體來揭示基督教思想的重點,展開與中國宗教文化的對談。無論在敘事形式、行文風格,還是在內容和傳播途徑等方面,作品都盡量去適應中國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適應策略(cultural
accommodation)使作品帶有種濃厚的本土化色彩,《張遠兩友相論》被看作中國近代小說或通俗小說,已被收入於多本小說目錄之中。[1] 這是十九世紀數以千計的基督教中文書冊當中修訂本最多、發行量最高的作品。[2] 作為第一部基督新教的傳教士小說,《張遠兩友相論》的創作技藝仍未臻成熟,但它卻為日後基督教中文小說的著作開創了先河,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鑑的楷模。
《亞伯拉罕紀略》是一部以章回小說體編著的聖經人物傳記,採用了中國史傳小說的筆法,具有中國傳統小說歷史演義的敘述特點。《亞伯拉罕紀略》在聖經的歷史框架內或在其敘事線索中拓展合理的想像虛構,令故事發展不偏離聖經的敘事原貌,同時又使得小說的人物形象更為生動飽滿。理雅各既用歷史的眼光評點這部歷史人物傳記小說,又強調了它的真實性及教化意義,並透過「回目」、「詩歌」和「回後評」等引導讀者接受基督教的價值觀,體現了中國傳統小說「羽翼信史」及「道德勸懲」的文藝精神及功能。[3]《亞伯拉罕紀略》可謂聖經與中國文學融合的經典範例。
《正道啟蒙》是一部以基督生平為骨幹的聖經故事集。這部作品最獨特之處,乃是譯者對原著大規模的改編加工,把原著的問答體變成敘事體。作品大量融合四福音的敘述,使聖經內容變得更加淺白易懂之餘,還添補了譯者的論述和觀點,使得這部西方基督教作品與中國傳統文化背景產生關聯,令中國讀者更易理解和接受。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890)對《正道啟蒙》作出高度評價,指出無論其「外表、書名、內容和語言風格都大受讀書人的歡迎。」[4]《正道啟蒙》在清末民初的基督教文學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主要歸功於其淺白地道的語言、中國本土化的敘事特徵,以及合參聖經各書卷的嘗試。
《亨利實錄》是一部頗具特色的異域小說。故事以十九世紀的印度為背景,作者以寫實主義的筆觸描繪了異域生活的種種,除了不乏傳道拯救靈魂的思想情節,亦呈現了印度的社會、文化和宗教風貌。小說原著在十九世紀暢銷英美。《亨利實錄》的譯者試圖向讀者解釋其從未見過的生活習慣和社會文化,藉以消除讀者和異域文化的隔閡。可以說,《亨利實錄》讓晚清的中國讀者有機會接觸到在英美暢銷的基督教小說,得以擴展他們的閱讀和想像空間。
《勝旅景程正編》是一部彌足珍貴的《天路歷程》(第一部)漢譯本。雖然其出版量及影響力遜於賓為霖的《天路歷程》(1853年文言本及1865年官話本),但當大部分晚清的《天路歷程》漢譯本皆承襲賓為霖一脈時,這個翻譯版本卻已另闢蹊徑,其翻譯特色可謂獨樹一幟。舉例來說,在翻譯書中的人物、地方的名稱上,胡德邁花了不少心血,別出心裁,音譯意譯兼備,如:Christian譯為「激烈尊」,並附以眉批:「激烈尊,即基督徒,今所稱激尊者,取其有激動烈心之意。」本土化的翻譯特色也十分顯著,如Village
of Morality譯作「修身村」,Lord Hate-good譯作「恨善老爺」。譯者又大量引用中國歷史、文學的典故,如Obstinate譯為「株守」,典出《韓非子.五蠹》之「守株待兔」;Vanity
Fair譯為「浮雲巿」,典出《論語.述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外,相較於賓為霖的譯本,胡德邁的現存版本極為稀有,予以收編便有了無可比擬的文獻價值。基於原著影響力的考量,並同時也礙於篇幅,本書目前只先收錄《正編》。
《紅侏儒傳》是一部帶有西方童話色彩的基督教寓言故事。譯者坦言此乃「半譯半著」之作,歸化的翻譯令英國本土的色彩褪去,同時西方童話的元素亦刪減了不少。中國地道的用語、相類的故事以及篇末議論的加入,充份照顧了讀者的文化背景。這部作品讓人窺見當時的傳教士如何消除文化隔閡之餘,也反映出他們對中國宗教文化的看法。此外,《紅侏儒傳》罕有地標示出華人助手的名字,見證了傳教士與華人信徒合作翻譯基督教作品的成果。
在本系列叢書中,本選集目前僅收錄這六部作品,它們僅佔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的一小部分。至於其他重要的作品,如郭實獵(Karl F. A. Guzlaff)的小說、傅蘭雅(John
Fryer)的時新小說(1895)等,除了計劃將來以專冊出版外,部分亦將收錄於編者與李奭學、吳淳邦教授合編的《晚清基督宗教小說選編》之中,由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另外,是次選編的全屬基督新教作品,而同期的天主教作品未予收錄,完全是因為文本資料的匱乏,正表明了此領域亟待學界開展進一步的研究。
在版本的選擇方面,編者盡可能採用作品的初版,包括《正道啟蒙》、《亨利實錄》、《勝旅景程正編》、《紅侏儒傳》,力求向讀者呈現作品的原貌。若無法覓得初版,編者則尋找現存最早的版本,包括《張遠兩友相論》(1831)及《亞伯拉罕紀 》(1862)。由於《張遠兩友相論》及《亨利實錄》不斷再版,編者以最早的版本為藍本,再分別取一八三六年及一八六七年的修訂本加以對照校勘,讓讀者瞭解兩部作品初期版本流變的情況。
本選集為每部作品重新標點、分段及註釋。至於編寫註釋方面,除了為個別字詞釋義及標示例句、典故出處外,編者特別關注這批作品與中文聖經的互文關係,盡可能地參照晚清時期的聖經漢譯本,把相關的經文在註釋中臚列出來,讓讀者得以窺覽十九世紀中文聖經翻譯的面貌,以及其對基督教敘事文學的影響。另外,就翻譯作品而言,編者將譯著與英文原著仔細對照,為求讓讀者一睹原著的面貌,同時更深了解譯著的翻譯特色,以及跨文化翻譯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及可行的應對策略。
編者撰寫了一篇導論及六篇作品簡介,導論將綜合討論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的思想主題、文學形式及翻譯特色等,而每篇簡介則概述了個別作品的內容提要、影響力,以及作者或譯者的生平等。
這部選集得以完成出版,實在有賴眾多友人的鼎力相助。首先,我衷心感激「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成」總編輯曾慶豹教授的信任和邀請,讓我擔任本冊的主編,受寵若驚之餘,定必全力以赴。此外,我要多謝橄欖華宣出版發行集團出版部編輯王鍾山先生,他在標點、排版及校對方面提供了專業的協助,我倆多次越洋通電話,愉快地交換意見,彼此素未謀面,卻早已惺惺相惜。至於編寫註釋及潤飾文字的工作,我幸得數+AM5位研究助理的鼎力相助,分別有黃信之、陳志謙、孔德維、唐院及黃媛媛。在搜集文獻的過程中,牛津大學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David Helliwell及Gillian Mary Grant、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的Graham Hutt、約翰本仁博物館(John Bunyan Museum, Bedford)的Patricia Hurry樂成其事,我銘感於心。另外,本研究及文獻的搜集承蒙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Research Grants Council)(項目編號CUHK447510)的資助,謹此致謝。最後,我無言感激內子淑卿多年來百般的包容,默默支持我追尋夢想,而子女津津、沙沙、涌涌的天真笑臉、朗朗笑聲則化成力量的湧泉,令我在上下求索的學術路上如沐春風。
黎子鵬
二○一一年十一月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註1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頁753;孫文光編,《中+AM5國近代文學大辭典》(合肥:黃山書社,1995),頁546;劉葉秋等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844;樽本照雄編,《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頁938。
註2 現存的版本,可參黎子鵬,〈默默無聞的牛津大學館藏──十九世紀西教士的中文著作及譯著〉,載《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七期(2006∕2007年),頁40,註30。裴士丹(Daniel H. Bays)推算不同版本的《張遠兩友相論》,在十九世紀的發行量高達100萬冊。參Daniel H. Bays,“Christian Tracts: The Two
Friends,”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edited by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4.
註3 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4;李家樹、陳桐生,《經學與中國古代文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4),頁237 49。
註4 The Seventy-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74), 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