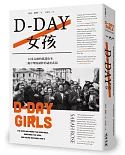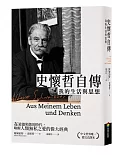智慧沒有童年。有人將古希臘哲學喻為哲學的童年,因為西方哲學正是從希臘哲人那兒發展而來的。
然而,從智慧的角度來看,本沒有什麼童年、青年、中年、老年之分。智慧既在時間之中,又在時間之外,它往往具有跨時空、超時空的意義。
今人在可累積的知識和可計量的硬體方面確實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今人的愚昧並未見減少幾許;相對而言,古希臘人在學問和人生諸方面所透露出來的智慧,每每使我們感到汗顏。
當今世界日新月異,變化速度日趨快速。但學問和人生中的大問題並未改變多少,因為人類飲食男女之生理需要和求真、求善、求美之心理需要並未改變。所以有人認為西方整個一部哲學史就是與柏拉圖對話的歷史。這話雖有點誇大,但也不無道理。
與古人對話,實際上是在重新發現自己、認識自己,那麼將古人知與行中所體現的種種外顯和內隱的智慧抽繹出來,就並非勞而無功了。
古希臘民族是個愛智慧的民族。他們為此而生,他們也可以為此而死。蘇格拉底終年披著破衣爛衫,毫不介意,卻孜孜以求「認識自己」;泰勒斯放著近邊的事不顧,而忙於「遠觀天象」;阿基米德在大軍壓境,死到臨頭之際,還有滋有味地在沙土上演算著幾何題。他們可以為了澄清一個問題而通宵達旦;他們也可以為了一個智者的到來而興奮不已,半夜披衣去敲朋友的家門。
希臘人將世界展現為可用理性來把握的東西,所以,他們「遠觀天象,近取諸身」,一心想把握隱藏在事物背後的「邏各斯」(類似中國老子所說的「道」)。不過,「邏各斯」本身又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工具,因為「邏各斯」的另一層涵義就是「語言」和「理性」。這樣,運用語言和理性的過程也就成了認識「邏各斯」(「道」)的過程。
反觀中國老子的「道」,它不是通過語言和理性得以認識的,而是必須借助於直覺和悟性加以把握的。因此,「邏各斯」和「道」也就成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的不同標誌。所以,有人稱古希腦以來的西方文化奉行是「邏各斯中心主義」。
古希臘智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體現在這種理性精神之中。在這種理性精神的支配下,古希臘的各門知識得到了發展。因而現代西方人的種種學科,如哲學、歷史、物理學、生物學、醫學、倫理學、政治學、修辭學、詩學等等都可以在古希臘找到源頭。
古希臘的智慧不僅體現在對抽象知識的追求中,同時也體現在神話、藝術和日常生活之中。
他們的神話異常豐富,處處透露著機趣。它們將神人化了,神具有人一般的七情六慾。所以神話表面上講的是神,實際上反映的是人的情感,是對天道人理的一種形象化的、想像的描繪,從而使他們得以「詩意地栖居於這片大地。」(荷爾德林語)
在他們的藝術作品,如音樂、雕塑、繪畫、悲劇、喜劇中也蘊含著種種智慧,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們的悲劇。古希臘的悲劇精神與東方文學、戲劇作品中所常常流露的出世和厭世的悲觀和傷感不同,其意義更多地在於對人及命運的思考,以及歌頌悲劇英雄對不可抗拒之命運的抗拒。所以尼采將古希臘悲劇稱為「肯定人生的最高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