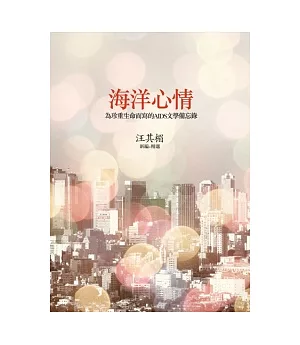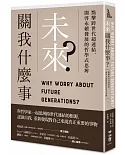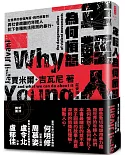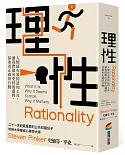我就是這樣開始的 (代序)
一九八六年,有一個美術系的大學生,在成功嶺檢測出HIV陽性反應,而被退訓,然後還被學校要求休學,怎麼有這種事?我去看他,他在排小劇場的戲,他就是田啟元,藝文界最早曝光的愛滋感染者。於是很多師友都受到牽動,想為之做些什麼。
他的畫家導師支持他完成只剩一年的學業,我很安慰。那位導師名叫羅芳,是我從小就認識的對門鄰居家的三姐,還好有她,作為大學追求真理的代表,站出來反對「隔絕」與「排斥」,反對知識殿堂帶頭「反智」!
後來田啟元發病,他的高中學姐房東到醫院照顧他,也順便照顧住在愛滋病房的其他青年人。那是二十幾年前,病人被家庭和醫護人員丟著不管的情形還相當「正常」。那位房東就是楊捷,把病人一個個裹著棉被,帶回家吃年夜飯的勇氣姐姐。她跟我說,「你也一起來好不好?」我掙扎了一下,想到生病的人反被家人棄置不顧,就向父母請假,在年終團聚中提前離席,到她的公寓,和一桌子愛滋感染者用公筷公匙一起慢慢吃飯談天。
和我一樣神情不太自然的另一位陪客,是剛發願的天主教修士漢明。才剛走進聖潔的修道之路的小修士,坐在一群「失落的肉體」和「徬徨的靈魂」中,那個時期感染發病者以同性戀者居多,聚在一起,言笑四射。看到修士青澀而力圖鎮定的臉龐,讓我知道上蒼已經伸出手開始教育我們。其實就是經由眾生,我們的鄰人,得病者與照顧者,一一來到我們身邊,啟發我們的心靈意想和心智圖像。
王紫山那晚發燒,他是精神病院的護士,與楊捷在當腦性麻痺者的志工時相識,自己得了愛滋病,也只得坦然接受楊捷的照顧。他虛弱得必須提前回院,拖著腳步經過我面前時,輕輕伸出手與我道別。瞬間我發現了自己的緊張,我也立刻認知了這份恐懼的不必要,和不重要。這個不會把病毒傳染給我的朋友,已垂垂將逝,我不能拒絕他的手,我不能辜負他對我成熟人格的信任。
紫山出院後來中途之家幫忙,他細柔的醫護能力,搭配啟元的聰明和衝勁,楊捷的開闊和寬厚,讓事情井然有序。紫山和啟元已去世多年了,每當人們問我是怎麼開始的,我會想起他那滾燙、柔軟的手指,與我相握時的觸感,這可說是我「征服恐懼」或是「放下自己」的第一步。
在當時隱密社會中的工作相當困難、相當地下,就非常令我感動;而這一些在日常行動中見到的義工、親友、感染者、發病者,每個人的面貌都如此清晰,他們擁有一種台灣青年自在的生命力,而必須保密、必須隱忍又低調的工作與生活方式,折射出整個台灣社會埋藏著的各種問題。
從中途之家到關愛之家,到綠茵坊花店,也顛沛流離了十幾年,也曾經被管區警員曝光而遭房東驅趕,楊捷用她的破卡車載著不能走動的病人,到處找房子,還得找房租。我看著她的疲困與勞累,聽著她講病人的事情,每一個故事都有深重的無奈和傷痛,每一個人都很卑微,但每一個人她都尊重。
我能做什麼?只能動筆寫,記下我的見證,用文字陪伴躲在陰影裡的病人和他們的親人,我寫了一篇篇溝通信念的文章,寫台灣的愛滋病人,也寫病人所處的家庭、社會、學校等大環境,在報章雜誌上慢慢發表,然後集結為《海洋心情──AIDS文學備忘錄》一書,在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五年間,由東潤、燕京(簡體字版)以及遠流先後出版。到底是人間善意,弱勢者相濡以沫的情懷,讓我能拋下對無知社會的憤怒與羞愧,只輕輕的提醒,小聲的呼喚。寫這本書不只是為了所謂少數的病人,為的是與愛滋共處的大社會,我更希望這個曾經教育我、營養我、堅強我的社會裡的所有的人,能持續擁有知識、擁有感覺,因此能活得再健康一點、過得再文明一點。
而綠茵坊花店讓病人能自立自助的行動,引起正面的迴響,有很多人來幫忙。藝文界與醫界的朋友每個月捐助房租,試著減輕楊捷的重擔,也延續好幾年。到了後期,「三犬基金」等各界人士開始加入,成為楊捷的長期好友和贊助人。
當然這十幾年間醫學界的方法和態度已較為進化。何大一博士的雞尾酒療法在一九九六年問世。早期突然發病,或發病後引起伺機性感染的各種致命症狀的情況減輕。感染者的壽命延長,從早期的僅有七年,到現在的統計,至少可以再活三十七年。但感染率仍然上升不下,異性戀感染者人數早已超過同性戀社群,而用毒者因共用針頭、共用溶液的感染方式,使全國的愛滋防治,與愛滋病人的身心關懷又進入另一階段。
歐美、非洲、亞洲、中國、台灣,各有不同的處境和問題。台灣因用毒者母親垂直感染,而生下的疑似愛滋寶寶(就是初生時雖因母體感染,其後定期追蹤檢測與投藥,直到兩歲左右,也因本身造血功能等因素而轉為陰性反應)。新來的小生命成為楊捷,和我們所有其他的關懷者,心底新的隱憂,也知道必須承接這迎面而來的新工作。
二00五年,楊捷在搬了兩次家的花店後面,開闢一間可以放小床的臥室,「三犬」的明驥、元達和其桐看到盼盼、關關、愛愛,和保母睡覺的地方已很狹窄,卻還必須為早產的台台和灣灣加裝呼吸器等設備,當場他們答應幫楊捷找寬敞一點的住處,大家心裡都明白,從醫院、從監獄、從派出所門口、從公園的板凳上轉送過來的嬰兒將一個個增多,真的需要一間獨幢的大房屋。房子很快找到了,大人小孩歡喜地跟著楊捷搬進我們永久的家,只是沒想到「房東」「三犬基金」出錢出力之外,還被社區抵制,一向低調的他們頻被媒體報導,還成了法院被告,官司纏訟年餘,還好二審勝訴,還給弱勢團體一個公道。立法院也修訂「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者人權保障條例」,至少在理論上強化了「就學、就醫、就養、居住」的權益。
時光飛馳,當年的年輕修士已成為幹練成熟的李漢明神父,他來為老友楊捷主持正式的「台灣關愛之家協會」。大陸農村愛滋孤兒的助學安養,也悄悄進行了七、八年,加上台灣南北好幾個地方的關愛之家,全都是依靠無數善心人的捐款來維持。雖說人們行善並不要求回報,然而善念善行其實仍是有期待的;期待有所幫助,期待有所改變,就是一種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的鄭重呼喚,使人如此解放心牆,付出自己。
所以,我需要比以前更常出去募款,也比以前參與更多關愛之家的工作。就是為了這麼多年來的善款與善情不能辜負。人心的能量聚集在一起是多麼難得,多麼珍貴,再艱難的工作都要繼續下去,否則不就成了徒然浪費。而且健康的人生態度、分享的共存信念,我更不忍心讓這樣的理想在台灣社會中轉為虛空。
遠在非洲的修女陳麗卿是一個遙遠的鼓舞力量,她在艱困環境中,懷著感恩和樂觀的信念,渡過每一天的難關,她說:
「我全力在預防AIDS的教育上出力。
我們已經失去了一代,
抱著希望,和年輕的一代、
幼小的一代,一起走。」
原來AIDS是一種信心的考驗,考驗我們是否還相信教育的力量,還相信訊息的傳遞,還相信觀念的匯通,就能改變行為、產生行動,就能挽救人們走向傷害與毀滅?
同時,也考驗我們的勇氣,敢不敢思考真相?能不能承認無知與錯失?肯不肯挺身而出,為下一代、為別人家的孩子、為不認識的人,付出關心與幫助?
而每去關愛之家,都會遇到不同國籍、不同膚色、不同宗教、信仰、使用不同語言的朋友。眼中看著孩子,手中做著事,好像他們本來就該在這裡出現,而我隨時準備記敘;為心底的悸動,為情緒上的撞擊,為精神上受到的開啟。
但願這一本在讀者手上被安靜翻閱的書,能增加人與人之間互相了解、互相包容、互相敞開心胸的機會,可以嗎?
汪其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