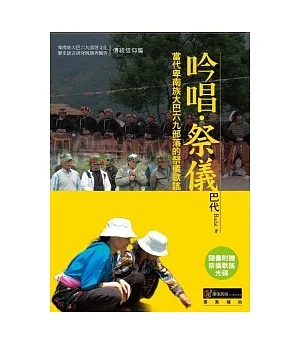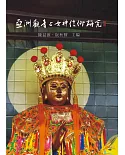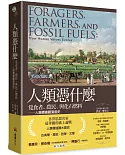自序
孤單,卻不孤獨
我喜歡在漫霧的下午時分驅車進入大巴六九部落後方的利嘉林道,深入早年先人燒墾、狩獵的區域,感受早年部落人艱困維繫農務,並與異族交往而成為歷史記憶的區域氛圍。
越過稜線前,在「甘達達斯」旱田區農作繁茂,山莊、民宿、野舖、茶肆間雜其間,春夏繁花簇放與秋冬楓紅與變葉黃橙的繽紛斑斕,每日,那山林總要陷落於一種傍晚的蕭瑟與入山人難以言喻的情感流動,讓人絲毫不覺得這條遠離都市文明的鄉間山道,是那樣孤單的迤邐蜿蜒在疊疊層層的山脊線上。
越過稜線後,古木參天,逐漸變換原始林的兩側景物,配合著大冠鷲、彌猴、山羌而次第變更佈景似的,令人目不暇接又不忍瞬目;途中曾遇見了彌猴家族,公猴誇張的敲打空樹幹發出警訊,頗令我感到驚奇。我常這樣一個人單騎在林道濃淡不一的霧中,周遭聽似喧嘩,但那些隱於枝葉,藏於山坳、溪澗的聲音,總與自己有一種難以測度的距離感。
這林道是在1937年日治時期,大巴六九部落遷移至杜拉杜勞(泰安社區現址)後,相繼開路成為日本砍伐檜木林、樟木林,與國民政府以後林務局繼續伐木造林的重要林道。其位置於台東市的正西方,中央山脈東麓,以卑南族大巴六九舊部落(哈里蘇來、甘達達斯)為入口,向中央山脈深入蜿蜒延伸32公里,正巧穿越過1917年前後部落與內本鹿布農族郡社群人紛爭的甘達達斯農作區、大巴六九山區、馬里山區、盆盆山區,與同屬雙鬼湖保護區的高雄縣霧台阿里林道遙相呼應;回返離開山區時,經過部落區域與巴拉冠接上聯外道路,不巧又正好貫穿大巴六九部落歲時祭儀歌謠展演、呈現的主要場域。
這樣的巧與不巧,正好照映著大巴六九部落過去一百年間,部落的生活記憶與祭儀歌謠的連結與變遷,正與開闢道路的國家集團有著密切關連。那最初封閉又完整部落世界,那最初反應生活文化的祭儀與歌謠,都因道路的開闢,山林的開採,土地權的莫名旁落、流失,部落遷移與外來文化衝擊,有了根本性的變動。而這劇烈變動的影響是那樣地撲天蓋地,令人無力招架;是那樣兇猛狂烈,令部落舉足失措以致失憶。也使得年年舉行的歲時祭儀舉行,也不免蒙上一點點地虛張聲勢,一點點地模擬演出與逐年加深的文化失傳的憂心。但,即使虛張聲勢或模擬演出,在大巴六九部落,目前環繞在歲時祭儀的各類歌謠依舊頑固地被傳唱與實踐。耆老、長者在祭儀中聲嘶力竭的吟唱,歌謠聲中傳遞著族群傳統的記憶,並表達在歲月老去的等待中,期望能有後者傳承的焦慮。
我無法確定這些有能力起詞吟唱的老者,還能有多少的歲月等待,一如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輩青壯,會紛紛覺醒投入傳承的行列,吟唱並記憶文化。但我早已積累了一股深切的急迫感,希望在這兩個不確定的時間因素交會之前,我輩已經建立好了一個連接的空間與緊密接合的元素,使不致讓祭儀傳承有太明顯的脫軌間隙。於是我企圖從影像、聲音以及文字,所有我可以掌握的工具著手;不避諱自己對音樂的外行,不計較自己對影像與文字的美感不足,硬著頭皮上陣採集與記錄、整理與研究,期望一些美好想像的可能實踐,而終至完成部落自發性的第二本調查報告。
正如午後獨行在大巴六九山區那般,獨行的不確定與迷航的潛在危機濃烈的存在,我絲毫不恐懼猶豫;因我輩族人深切的託付,長老耆宿殷切的叮嚀期望與傾囊指導,令我的孤單彳亍充滿了動力。當然家人無悔的支持與容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的補助,也讓我偶而有「孤單」情緒時,不致於感到「孤獨」,而削弱了我發願投入「大巴六九部落文化歷史語言研究與調查報告」工作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