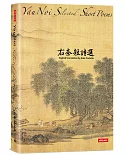推薦序一
詩人年輕,世界靜好 陳巍仁
替詩集開卷,對我來說是個全新的體驗。長青讓我來為這本《給世界的筆記》寫序,應是知道我曾與散文詩這個文類纏鬥良久,故希望我能以這個經驗為基礎,繼續談論一些微知管見。眾所皆知長青在詩創作上一向勇於窮究表現方法,並以此逼淬出懾人的詩質,這幾乎是種嚴苛的自我鍛鍊,如先前《落葉集》的主題規範、《江湖》的語言規範,以及不時跌宕而出的精采圖像詩皆然,這本散文詩集,也是另一段漫長實驗成果。從一九九七年起,長青便持續有散文詩發表,如今積累成卷,已可窺探詩人這十餘年來對此文類的思維。台灣的散文詩發展向有明確脈絡,長青以年齡上相對的「新生代」(雖然作品中曾自諷已成中生代)賡續其後,這本來就有番避不開的定位議論,我這篇小文若對此閃爍其詞,便不能算是盡責。從散文詩史沿革的角度來看,這篇文章理應作得嚴肅典重,以彰顯新生代詩人延續文脈、開拓新局的意義,然而細觀長青的散文詩,卻別有一番舉重若輕,迴旋自在的氣息,若用體系、風格等大帽子硬扣,不唯遮損其情性,更會錯失文類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因此,我想要用比較簡明輕鬆的方式,來回應長青的作品,同時帶入我的一些思考供讀者參酌。
相對於其他地區的華文散文詩,台灣散文詩可說極具辨識度。當大多數散文詩還受困於文類辨識的灰色區域時,台灣散文詩卻迅速在「詩」的隊伍站穩了地位,這當然得歸功於商禽的先導,蘇紹連、渡也以及杜十三等詩人繼之而起的優秀表現。散文詩的「詩」,絕非「詩意」或「詩化」等可模稜含混的印象式概括語,在下筆之前,詩人便對詩美學有清楚的認知及自我要求,在其認知中,散文詩就是詩,殆無疑義,只是採取了散文的形貌。歸納這群主流詩人的作品,散文詩的詩質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現代主義脈絡下的「超現實技巧」,這在商禽作品中已發展得十分成熟;其次則是有極短篇小說精神的「驚心結構」,以蘇紹連為大手筆。台灣散文詩常以營造一奇特荒謬的情境為起頭,並在情節的推移中,在最後突然給予讀者電光火石的一擊,這不但可帶來獨特的閱讀體驗,更能凸顯作品欲討論的主題,並使讀者再三回味咀嚼。這套操作方法十分明確,效果亦佳,幾位質精量足的詩人儼然構築出一套文學史的譜系,並獲得了該文類的詮釋權,是故接下來有很長一段時間,凡言散文詩必稱商、蘇,許多詩人雖也寫,但多是嘗試或調劑性質,足以彙集成冊的能量已不復見,指點文類前景的氣勢更難以相提並論。
簡而言之,台灣散文詩在短期內完成了「典律化」過程,卻一併呈現了高峰期過後的停滯狀態,若持續再無變化,便很可能成為專屬上個世紀詩壇的獨有現象。不過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竟出現不少新生代詩人專力於此,稍早於長青之前,已有王宗仁、然靈等相繼推出散文詩集,長青這本集子一到位,一個完整而具有代表性的陣容便就此形成。以長青在詩壇耕耘的功夫之深,以《給世界的筆記》為例來看新生代詩人對典律的回應與突破當很具代表性。
一開始我最好奇的是「影響焦慮」的問題。既然是讀著前輩詩人的詩作成長,驚心散文詩的效應又是如此強大,我預期長青的詩作還是會受到感染,但展卷之後,卻發現別是一番天地。當然,非要尋找脈絡的連結也是有的,且並不困難,比如在〈不誠實的詩人〉中,浴室中的香皂、蓮蓬頭、燈泡諸物紛紛對詩人傳達不信任的質疑訊息之後,詩人終於忍不住發飆痛吼,但換來的卻是「身體洗乾淨有用嗎?你的心,已經是不誠實的詩」這樣冷峻嚴厲的回應,與前輩相較,其內涵技巧都毫不遜色。另外一首我極喜歡的超現實風格作品〈象國〉,收束尤其警醒精緻,「『那些徬徨與不安,也可以擦掉嗎?』我在心裡問自己。∕『沒用的。身軀有多大,罪孽就有多重。』旁邊的一頭象說。∕『我們都一樣。』另一頭象,悲傷的補充。」其鋪陳與引發的技藝純熟若此,長青如想在這條路上踵繼前賢,基本功底是絕對「過硬」,然而類似以上例子的作品,在集中並不算太多。一剛開始,我將其解釋為長青的自我節制,是刻意不讓自己那麼容易便寫出「像樣」的散文詩,這也有與前輩的路數畫清界線,擺脫影響,自覺負起突圍重任的意味。蘇紹連在二○○七年的《散文詩自白書》自序裡,便曾提到李長青等一批年輕詩人,確實「創作出迥異於商禽、渡也及我不同調性的作品來」,顯然長青的「去影響」是備受肯定的。不過,我隨即想到這樣的評判不但太過簡單,也小看了詩人與散文詩這個文類的主體性,難道我們就非要急著將其塞入文學史的某一位置?況且,文學史很可能存在各式各樣的誤區。
其實關於台灣散文詩的典律問題早有異議,約與商禽同時開始散文詩創作的資深詩人秀陶,便曾戲謔地說:「散文詩有七百三十一種效果,何必獨沽『驚心』一味?」為了扭轉這種偏見,秀陶亦在二○○六年出版《一杯熱茶的工夫》,以示散文詩「淡」、「冷」、「禪趣」的一面,這即是對典律的質疑。我曾撰文考察過「驚心」特色在當時詩壇時空發展下的必然性,但去除了這個背景,散文詩本身一直就該是「無形」的文類,因此長青的散文詩,更重大的意義是重新強化了該文類活潑的本質,跟前輩筆下對生存世界充滿質疑、對自我靈魂深刻鞭打的「劇場性」相對照,散文詩又重新展現了一種紓緩而更具個人化的氣質。我更願相信長青這輩詩人寫的正是自己的初衷,而未必得「逃離」什麼典範。況且,我們實不應小覷散文詩中「散文」二字所蘊含的能耐。
我特別鍾意於詩集名裡的「筆記」兩字,這便是文類得以越界的重要出口。散文詩一詞的最初使用者波特萊爾,常把已撰就的分行詩改寫為同題散文詩,其目的是消去詩語言的高蹈性,而以自然語的面貌邀請讀者親近。有趣的是,長青本集中如〈江湖〉、〈給世界的筆記〉等也都有同題分行詩收錄於之前的詩集,但兩相對照,散文詩卻絕非分行詩的改寫,而是完全獨立的作品,也就是說,長青的散文詩在創作伊始就是完整的意念。「筆記」的散文形式,可能更宜於記錄日常的生活,因為「世界很容易,就被忘記」(〈車庫〉),在捕捉詩思的關鍵時刻,也許詩人更應把修辭韻律分行等雕工拋開,直接形諸熟悉的表現語言。
長青的「筆記」出自一種「靜觀」的態度,對世界「遂如此坐視:如此之坐視」(〈坐視〉),因此筆下往往有道深刻的目光,甚至不妨說其作品原本應屬微微偏冷的色調,但因為散文的特性,使作者必須親自站在第一線誠懇地娓娓道來,這便讓作品呈現了更多的寬和感。長青的散文詩中,少見懷疑與控訴,多的是對人間變幻、世道紛紜的諒解。也正因為如此,長青所記錄的世界中並無所謂的醜惡,遂顯得有種安靜通透的氛圍,這不但植根於作者自身的氣性,也反應了文類本具的特質。或許我們可以這麼看,波特萊爾所凸顯的資本都市之醜惡,或驚心系列呈現的時代、心理困境,乃是屬於「詩」的表現性及衝突性;而長青《給世界的筆記》之優遊從容,乃是又回歸了「散文」(尤其是華文散文傳統)的價值。如長青與蘇紹連皆任教於小學,描述教育與課堂的題材自然少不了,但相對於「『這就是獸!這就是獸!』小學生們都嚇哭了」的震撼,長青的「有一個學生來問我其中一個填充題的祕密。我沒有告訴他。∕我讓他走回自己的座位,走回自己的課本,自己的人生。」(〈填充題〉)展現的「靜和」,顯然可作為另一種散文詩思的對比。
當然,有不少人仍擔心文類界線的定義,憂慮散文詩是否又將放鬆為散文的直白敘述,但在長青等受過嚴格語言淘洗訓練的詩人身上,這個問題其實不足憂慮,詩人反而可以在兩種文類的頡頏中,創造出更無限制且出人意表的句構,如「說好朝夕都要潮汐以沫的詩題,也逐漸失蹄,在地平線沉沒以後沉默了;海笑著海嘯,彷彿,我再也無法以在野的姿態寫詩了」(〈變題〉),其語句語意迴環變化之多姿可喜,不正是散文詩獨具的魅力?況且文類的邊界是否真的重要,這點亦是個迷思,在持續關注文類論題之後,我甚至期待當前文類解構或許能逐步被瓦解,屆時創作者就會擁有更大的自由。散文詩本來就頗富「元文類」(genus
universum)的意味,是種無類的表現方式,準此,當我看到長青集子中如〈塞車〉、〈意義〉等向散文跨界較多,甚至不那麼「詩意」的作品時,同樣能感覺作者在文類拿捏上的慎重,並肯定其價值。
走筆至此,我其實很清楚長青並不需要別人來界定其詩作在詩壇或文學史中的位置,這些與他無關,因為長青最嚴重的焦慮不是源自於前輩、同輩,而是來自於自己。從〈盜墓者〉、〈忘卻〉、〈中生代詩人〉、〈不誠實的詩人〉諸作中,長青並未(或根本無法?)掩飾對純真遠離、靈感枯竭的恐懼,即使在現況中,長青已是六年級世代中聲譽及產量皆名列最前茅的詩人,但這惘惘的陰影仍如影隨形。我當然沒有能力或立場勸其寬心,因為我深知一刀兩刃,壓力即是動力。然而我更確定,優秀的散文詩靠的不是炫眼的技巧,而是與世界作最真誠的互動並如實展現,在屠格涅夫、王爾德、泰戈爾的不朽傑作中,都可找到鐵證。長青創作散文詩的資歷足十餘年,顯然不是為了「蒐集」各種詩型而趨走短線,既然如此,只要長青能繼續在散文詩裡獲得樂趣,他的擔心就不致於成真,因為我堅信,散文詩比一般分行詩更騙不了人。
散文詩是一面澄澈的鏡子,我看到鏡中的詩人仍年輕,世界猶靜好。願長青時時拂拭,為讀者、為自己、為這個他所珍愛的世界裡的一切。
推薦序二
化身或轉世 莫渝
─讀李長青的散文詩集《給世界的筆記》
沒問過,也不知道長青為何挑選散文詩作為文學書寫的出發。
假設,長青已經認識「散文詩」,且讀過不少散文詩作品,商禽的?紹連的?沈臨彬的《泰瑪手記》?波特萊爾的《巴黎的憂鬱》?抑其他書市詩人的作品?
長青的散文詩集《給世界的筆記》是新著,卻非新產品,寫作時間長達十三、十四年。從〈開罐器〉到〈給世界的筆記〉,想傳遞什麼訊息?是警誡的告言?先知的預防?還是,彷彿摸索的少年,找到╱發現了新事物,欲向世界揭櫫某種宣示。
宣示:我是多麼不快樂,多麼茫然,多麼憤懣,多麼憂鬱?
一九九八年〈少年〉一作:「我發現我被窗戶栓留起來,走不出去,跳不出去,透明的窗外是羅列的風景,它們毫不遲疑加入囚禁我的行列。」在封閉的透明玻璃窗,看得見窗外的任何動靜,卻「走不出去,跳不出去」。自我囚禁,抑被豢養軟禁?
憂鬱少年的長青,躲入「散文詩」的「透明清晰的窗戶」般的蛹,從十三、十四年前的一九九七。在蛹內,自我營養,自我修行,自我凌虐,自我啃噬,意欲蛻變?成蛾?成蝶?成詩?
一九九七年的〈憂鬱之傷〉一作,三段,未及一五字,竟用了十三處「憂鬱」,結尾「憂鬱著你憂鬱鏡前的憂鬱」,這樣的措詞,我在美國鬼才文人愛倫坡詩〈The Ravan〉:「夢著凡人不敢夢的夢」(dreaming dreams no mortal ever dared to dream
before)見過一次。夢,也是長青散文詩喜用的字詞。他說:「夢境撫養我長大,夢境督促我度過難關」、「夢境訓練我,夢境栽培我」、「我對夢境祈禱,衷心祈禱。」較之憂鬱,夢對長青友善多了。因而,他喜歡在夢境扮演盜墓者、走索者,以便與詩貼暱。
長青的憂鬱,是哪一種?melancolique?triste?spleen?第三字,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使用的英文字;第二字,「憂傷」、「哀傷」、「哀愁」;第一字,較常譯「憂鬱」。不論何種,它們都是憂鬱,長青的憂鬱?
是否文學少年都多愁善感,把憂鬱掛在臉上,說在嘴邊,寫在筆下?
憂鬱之蟲啃噬的散文詩,一直是法國文學家的少年之愛。法國文學十九、二十世紀的兩位情篤摯友:紀德和魯易,年輕時均有散文詩集的出版,二十四歲的魯易出版《比利提斯之歌》(一八九四年),二十六歲的紀德出版《地糧》(一八九七年)。以小說《日安.憂鬱》(一九五四年)走入文學寫作的女作家莎岡,回憶她年少的閱讀,十三歲讀《地糧》,十六歲讀韓波的《彩繪集》;二書均屬散文詩集。她更直言:《地糧》是「第一本為我而寫的《聖經》,或由我自己所寫的《聖經》」,極盡推崇之譽。《地糧》是紀德年輕時,遊歷北非和義大利之後,以抒情方式,揉合傳統的短詩、頌歌、旋曲等形式,組成歌吟「解放」(自由)尋求感官逸樂的記錄。文類的劃分,歸屬散文詩集。內容上,強調愛、熱誠,排斥固定的事物。
散文詩的書寫,形式上,可以工整的,如魯易《比利提斯之歌》,每首均四段;可以散漫的,如紀德《地糧》。
散文詩的內容,可以是浪漫唯美的詩情畫意,如沈臨彬的《方壺漁夫》,可以是難以捉摸的玄奧奇思,如紹連的《隱形或者變形》。
長青的散文詩,嚴格講,有點像fragments,片簡,片段、斷片、精緻的掌中小語。集合八十九篇加上標題的斷想與片段式的書寫,形成《給世界的筆記》的告白。紀德的《地糧》,看似一小段一小段鬆散的片簡,這些飄忽隨想的意象,有效地滋潤乾渴的心靈。紀德在《地糧》說:「這裡是愛與思想的微妙交流」。長青則要揮別「所有的愛與絕望」(〈給世界的筆記〉)。從這角度看,我有點釋然。原來,《給世界的筆記》是求入定的詩書?
法國文論家羅蘭.巴特說,「文學作品一經發表與出版,即宣告死亡」此意:作品是脫離母體(創作者)的木乃伊。藉由當世或後代讀者評論家的閱讀,它復活了,它重新展現活力。換句話說:作者亡身,作者的靈魂轉化為「文學作品」,仍在人間奔走流通傳閱。那麼,詩(包括藝術品),算是作者的化身、轉世,另一尊作者現身。
散文詩高手蘇紹連自解其寫作的策略是:置身情境的投射、隱形或變形於物象事件裡。對景仰蘇紹連的長青言,散文詩是華麗的陷阱(〈選擇題〉),同時,「這個世界的風沙,仍繼續推擠,馳行,轉身,變形」(〈風沙〉),以及「只是因為我∕不斷變化著我的形貌」(〈遺失〉),「用變形的夢當鰭」(〈游泳池〉)。
長青的化身或轉世,似有所呼應巴特與紹連之說。
序,原本該為解題、贊曰而寫。讀長青的散文詩,湧現太多的問號。這些Q,仍留給長青A吧!
二○一一.六.二十
推薦序三
令人嚮往的散文詩版圖 蘇紹連
─《給世界的筆記》的作品風貌
一
在所有六年級以降(一九七一年之後出生)的詩人群中,李長青的創作版圖是最為寬廣、質地是最為深厚的一位。他不是僅以一種詩風在創作,也不是和詩壇上那些分不出你我的詩風模糊在一起。李長青的詩風,大氣大度,已有本世紀大詩人之象。
二
有一個銷售電器的廣告詞:「要買就買最好的。」什麼是最好的?是指品質和效能;詩不也該如此嗎?「要讀詩就讀最好的」,購買詩刊或詩集,我一貫都是如此,絕不受外表的包裝迷惑,更不受宣傳的花樣欺矇,而忘了翻開內頁讀一讀詩作寫得好不好。李長青的創作心態是「要寫就寫最好的。」他發表的詩作沒有一首爛詩,永遠每一首都是最好的狀態。
三
世界這麼大,台灣出版過散文詩集的詩人,怎麼好像都住在台中。寫《面具》散文詩集的渡也,寫《象與像的臨界》散文詩集的王宗仁,寫《解散練習》散文詩集的然靈,寫《驚心》、《隱形或者變形》散文詩集的我,以及寫《給世界的筆記》散文詩集的李長青,儼然已成台灣創作散文詩的一支先鋒隊伍,不知在天上的散文詩教主商禽是否看到這支隊伍已為台灣的散文詩帶來願景?
四
李長青用「散文詩」來寫筆記,哇,不得了,不僅開創了筆記文學的新形式,也發揮了散文詩前所未有的效能。文學作品其實是不必講效能的,但若是在表現上能符合了某一種形式,在傳達上能承載了某一種意義,而有所影響時,此即為作品的效能。李長青的散文詩筆記作品,給了世界一種新的書寫典範。
五
「世界」是一個巨大的命題,像能擁有一切的王,而個人是渺小的子民。子民寫給世界的筆記,是以恭謁的態度還是以挑戰的氣勢?當世界是美好時,詩人要給世界什麼樣的筆記?當世界是醜陋時,又要給世界什麼樣的筆記?世界與個人息息相關,詩人對著世界的喟歎與呢喃該如何拿捏?李長青在這本散文詩集裡將一一的告訴我們。
六
世界在李長青的眼中是什麼形貌?是扭曲變形的異端嗎?或者「世界仍是一面生瘡的屁股」、「罪惡來來去去,這世界擅長失去」,很令人痛惜和難受。詩人告訴我們「這個不完整的世界如何行走我們滄涼的心田」,我們該惦記著這個不完整的世界,還是把它忘掉?然而人類可以把世界遺失以後還活著嗎?詩人自問:「世界的形貌不斷變化,這就是我,終究遺失它的原因嗎?」我們從詩人的迷惑以及反思中,找到答案:世界,是詩人自身的投影。詩人自己說,是因為詩人不斷變化著自己的形貌,世界才會變化。
七
《給世界的筆記》整本詩集裡的「世界」如何變化,都可看做是李長青自身的投影。然而他又不時與世界對立,抗訴這些投影與映照。李長青的風采,便成了世界的風采,世界的風采卻成了他體悟與反思的對象。「世界就在層層疊疊不停堆累不停迴旋的山水中,照見自己。」這樣的世界是詩人自身的投影與映照,「我終於知道:世界不適用於,我的夢境。」則是詩人對世界的體悟與反思。
八
我們從詩人的體悟與反思的話語裡,讀到一些現象的反差,反差形成詩的張力,把詩意撐開至兩端,愈開則張力愈大。「陌生的自己似乎已經閱歷了許多熟識的自己」,陌生的閱歷熟識的,是一種自我辨識的反差;「眼淚在水槽跳舞」詩句的意象,不禁想起許達然的散文集《含淚的微笑》,「眼淚在水槽」不就像含著淚,「跳舞」不就像在微笑,流眼淚算是哭泣吧,跳舞算是歡樂吧,把哭泣和歡樂的現象結合在一起,就是一種不同情緒的反差。「午后的車潮,以一種獨特的節奏,兀自孤單著」,車潮不是車子很多嗎,怎會是「兀自孤單著」?這也是一種反差的現象描述。
九
我們從詩人體悟與反思的話語裡,也讀到距離感,在距離裡有著很濃烈的變化和隔閡的感覺,斷斷續續邈邈茫茫,或許世界之大,終究成了渺小人類可以拉扯和開展的對象。「他選擇來到自己三十年後的墓地,盜取自己,成名的詩句。」「後來才發現,同一天的早與晚,就是一生。」這是時間的距離;「天涯鑲嵌金黃圓融的暮靄,暮靄飄飄,盈盈裊裊,繚繞老人的房間,讀著或短或長,天涯的信箋。」這是空間的距離;「那些徬徨與不安,也可以擦掉嗎?」、「身體洗乾淨有用嗎?你的心,已經是不誠實的詩」這是心境上的距離。距離愈大,人的無力感也愈大。
十
除了距離感,在李長青面對世界的詩裡,最常看到的是一種宿命式的無力和無法的感覺,如此更證明了人類的渺小及懦弱或是有限。「儘管手持方向盤,也猶然無法帶領陽光,或者風雨。」、「原來春天,是無法預料的。」、「部首規定了我的屬性,是水是火,是土是木,卻無法確立我的脾性。」、「海笑著海嘯,彷彿,我再也無法以在野的姿態寫詩了;」、「我已經無法分辨,世界的高矮胖瘦。」、「我漸漸發現:我,無法溶解。」、「詩人的瞳孔,越來越無法眨動了。」這些詩句真是寫盡了人類的無力感,就算手持方向盤,也無法轉動去帶領陽光和風雨,無法預料春天怎麼,無法確立脾性、無法溶解,甚至瞳孔無法眨動。李長青把人類寫得這麼悲苦傷痛。
十一
因為人生的無力感,詩人唯一的力量形式就是寫抗議的詩句了。但李長青是百分之百溫和的,他的詩句絕對是琢磨得圓潤光滑,不會有尖銳的刺。我們卻在他的詩作裡找到激動的詩句,而這些詩句正是他散文詩的語言特色之一;激動的詩句會令呼吸急促,喘不過氣來,尤其是不斷的疊類重複而不標點的長句,要有足夠的氣力才能一口氣唸完。「憂鬱的方桌憂鬱的搖椅憂鬱的地磚憂鬱的壁櫥憂鬱的一○○燭燈泡憂鬱的沙發抱枕憂鬱的水族箱憂鬱的電視機」、「我在這裡惶惶然我也在這裡特別堅強,褪色的牆垣傾斜的岩層枯竭的浪不固定經緯的落石」、「我們的車庫快樂的車庫永不拉下鐵門永不熄燈;星星就在上面跳舞月光就在地板磨蹭,是車庫讓你表演是車庫讓我偽裝是車庫讓我們彼此摯愛不渝」、「傷口失去了心證失去口供失去情節失去段落失去被害與加害者也失去了目擊證人。」、「在我逃脫了所有的愛與絕望之後請你千萬保重,你的愛與絕望並非全是我逃脫了的愛與絕望啊」,這些長句可以推想詩人是在很悲愴之下用力寫出的,字字句句都力道十足。現實人生已無力,詩人的字句豈能也無力?
十二
李長青不斷的在詩集裡書寫詩人,或許詩人是他最能投射情感及思維的角色,也或許他藉此惕勵自己如何當一位詩人,如何以詩人的身分去對世界說話。李長青一首寫詩人節的詩:「傳說詩人的節,都是中空的」看來對詩人不是怎麼好的形容;對於年輕詩人,嚴厲的說出「年輕詩人擄掠了許多浮濫的獎牌,荒謬的頭銜,怪誕的讀者,不安的聲名。」對於中生代詩人呢?李長青是這樣看待:「中生代詩人對台下的耳朵傳道。信詩者,得永生。掌聲淹沒了他成名的詩句。」似乎說詩人那麼愛名器。他義憤填膺的指責不誠實的詩人「身體洗乾淨有用嗎?你的心,已經是不誠實的詩」看來詩人是如此的骯髒齷齪。他認為詩人應該是這樣:「詩人以筆為刃,抽刀斷念,也希望斷去多餘的天色。」、「詩人寫出來的江湖,擁有廣漠的邊幅。」這是〈江湖〉一詩裡對詩人的期許。李長青本身就是詩人,故而有如此深刻的體會。
十三
由於李長青本身就是詩人,除了詩的創作外也浸淫於理論的研讀,或許在不意間,詩人的思維總在專業的文學用詞裡打轉,自然而然的就把它帶入詩句裡,成為一種充滿文學意味的詩作。「雲氣類疊我們,鋪排我們共存的城市」詩句裡的「類疊」和「鋪排」都是修辭學的用語,現在用來當動詞構成意象;「愛是一種寫作而思念是典故;我們是不斷再版的文本」詩句裡的「寫作」、「典故」、「再版」、「文本」四個文學上的用詞,竟然當作愛的隱喻;「這裡曾經躺滿各式各樣的,詩體:標點,斷句,典故,天氣,以及刪刪改改的暴風雨。」這段詩裡,把「詩體、標點、斷句、典故、刪改」等寫作上的用語和氣候現象並置;還有「重新分行之後,字句仍繼續流血」、「我記得,它們明明套上了文法的大衣,內裡鋪了棉質的修辭」、「那一個安靜的房間,沒有主詞,只有受詞」這些詩句裡,充斥著「分行、字句、文法、修辭、主詞、受詞」等文學用語,頗易令有文學寫作經驗的讀者產生共鳴。
十四
李長青的散文詩常將類似的現象並置比對,替代了事件起承轉合的設局陳述;他不像前一代的散文詩人愛用戲劇性敘事,或在結尾營造驚心效果。像〈字典〉這首詩,用並置的兩段話分別說出「字典」與「我」的心聲,話中的語言採相同的句法,結構相似,結尾兩行亦同。我想起我曾寫過的一首散文詩〈在字典裡飛行〉,是「我」融入「字典」裡,敘述一個奇異的字典探險記,起承轉合的設局。李長青的〈字典〉則字典是字典,我是我,以分開而並置的方式直接相互隱喻,意義性的表達強烈。李長青的另一首詩〈日曆〉亦作同樣的方式書寫。而在〈忘卻〉和〈咳嗽〉這兩首詩裡,第一段和第二段的語法也是相同,並置比對。從這些例子,顯示出李長青創作散文詩的一種律則,是第一段和第二段的語言都為類比並置,第三段則是另一種稍作改變,這樣的律則形成了一種歌曲的意味,第一、二段為相同的主旋律,第三段則像副歌,旋律延展,整首詩的音樂感便豐富起來。
十五
當然,詩人的語言重複習慣便形成他作品的調性,每到各段落的同一個位置就會出現相同的詞語,像樂曲一樣,是調子的主音,由主音帶頭出現,接下來再加上屬音的陪襯,一路演奏旋律迴盪的曲子。這樣子的好處是調性明確,使音樂進行具有強烈的方向感,很容易從主音掌握詩意的線頭,詩意才不會分崩離析。李長青的語詞主音習慣放在段落的第一句,例如:〈尺〉,有三段的開頭都是「它繼續為我量出」,另一首〈搖椅〉有四段,開頭都是「繼續靜靜注視著」,主音是較為完整的語句;但有不少首僅用語句中的部分幾個字為主音的,例如〈忽略〉一詩,就以「忽略」兩字為主音,散布在每一段的第一句裡;另外較為特殊的,是在詩中安排雙重的主音,形成雙重奏,例如:〈隧道〉一詩本以「我想穿越隧道」為開頭主音句子,然而卻有幾段的是以「已經□□下來」分別述說風景、季節和氣流,如此一首詩的調性便有了兩種變化,可以分別體會,也可以相互融會。這些可謂是李長青在散文詩的創作上所開創的個人特色。
十六
台灣散文詩的創作隊伍裡每一位詩人,都知道散文詩的創作原則是分段不斷句分行,得像散文的句子要句句相連,而不像分行詩的以斷句斷詞來分行。但靈活的散文詩作者多少會稍稍打破常規,把散文詩的分段形式給予較多樣的變化。李長青的散文詩分段不拘泥於段就只有段,而是在段中給予分行句子,許多是以兩行句子為一段,例如:
星光還有一點亮,在尚未破曉之前,我們走著。
只是,走著。星光仍有一點亮。
這是同一段的兩個句子,本可連著寫為一行,但李長青卻將它分為兩行,沒有將它斷句斷詞,仍是完整的兩個句子。這樣的寫法似有意向分行詩的形式靠攏,讓散文詩的詩意不受句子的緊密相連所綑綁,而能像分行詩也有一些換行的呼吸空間。像〈字典〉、〈夢境〉、〈現實〉、〈日曆〉、〈尺〉、〈午后〉、〈開罐器〉、〈塞車〉、〈淚腺〉、〈少年〉、〈文明〉、〈咳嗽〉、〈建築〉、〈風沙〉等十多首詩作都有這樣「分行合段」的散文詩段落,在台灣散文詩的創作隊伍裡,除了李長青外,沒有人擁有這個獨特的形式特色。
十七
李長青和王宗仁、然靈都是同一世代的詩人,在散文詩的創作上,王宗仁被稱作「繼承台灣散文詩正統脈絡的第三代主要接班人之一」,因為他的散文詩創作量豐富、技巧成熟,個人特色鮮明;然靈除了是「台灣第一位出版散文詩集的女性詩人」外,她的作品語言陌生而意象新穎,被詩壇視為潛力無窮的才女;那麼也投下許多心力完成這本散文詩集的李長青,該如何看待呢?我想,詩人的任何稱許都需由作品見證,李長青在散文詩創作上比王宗仁及然靈早,也早已走出自己的一條路,這條路特別重視詩的語言錘鍊,以排比類疊為階梯,以映襯反差為斜坡,以重複並置為叉路,以長短句為顛簸,以轉化替代為轉彎,以分行合段為休息站,以隱喻象徵為風景……,就這麼在散文詩的版圖上開闢了李長青個人的一條路,而且可能愈開闢愈遠,所到達的版圖愈廣,所以我預測,李長青只要繼續在散文詩上創作不斷,他將會是「台灣散文詩隊伍裡走得最遠最廣的一員猛將」,正如他的詩作〈江湖〉裡的期許:「詩行裡的招式,合掌後,靜成深深的段落,在心上開展,整座武林。」整座武林,那是多麼令人嚮往的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