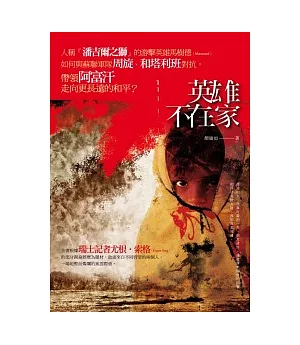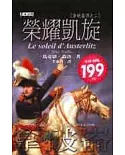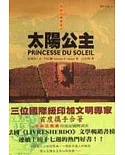推薦序1
還記得那是個美麗的秋天早晨,我在辦公室裡,電子郵件中突然出現一封陌生人的來函。那是一名台灣女子,她希望能把我對阿富汗人馬樹德的報導譯成中文。這真是個意外的驚喜,我欣然答應。事情至今已有十年前,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奇遇會演變成一本書的出版。
馬丁.布伯說,人生就是邂逅。是啊,我,一名瑞士記者,和馬樹德的邂逅是經過再三波折才成就的。對他訪談的時間並沒延續太久,之後,我們分道揚鑣。我們又是彼此不相識的陌生人,過著各自的生活,好似那場見面不曾發生過一般。我們幾乎同樣年紀。我是個自以為是,生活在富裕瑞士的冒牌革命者,直到今天,我的生命不過是些小傷、小痛、小喜的結合;而馬樹德的一生卻遭遇多少殘暴與慘酷的雕琢與刻劃,最終結束在連神都要離棄的阿富汗。
我和馬樹德之間活沛的對比與巨大的差距,不但對敏如造成相當大的震撼,更如影隨形地在她的生活中翻攪,她必須把這種瘋狂(如她自己所言)寫下,才能擺脫所受到的糾纏與盤踞。
馬樹德的死訊是我在前往安哥拉途中接獲的,那是我寫他的故事裡出兩三天之後的事。而文章出刊以前的一個月,我就在他遭到暗殺的同一房間裡對他進行採訪。嚴格說來,我和馬樹德之間從未開始有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邂逅,所以也就沒有所謂的結局。直到敏如打算寫出我和他的故事時,我才又和馬樹德相遇,而且是在一場夢幻中,在一種即便事件多少與事實相符,卻是那麼離奇甚至荒誕的夢境裡重逢。
敏如是第一位,也很可能是最後一位徹頭徹尾知道我人生的人。「英雄不在家」內容中的一半承載我的生命史,現在就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去到我不熟知的台灣。這個事實多麼奇特!
「如果你只看到一個個的個人,這就和從月球上看人沒什麼兩樣。唯有把人和人一起看,才會是一幅真實的畫……看到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也就看到兩個有活力的個體,而人就必須是如此,共同,齊力:給出、收受;攻擊、防禦……」布伯說。
我怎麼知道自己會去採訪阿富汗的游擊隊長?我怎麼知道我會答應敏如的要求,而對她講述我的人生?又怎麼知道由敏如所編織的故事會去面對華語讀者?
三場邂逅,是啊,真是三場稀有的邂逅啊……
Eugen Sorg
推薦序2
顏敏如的創作態度是嚴謹的,為了體會她筆下英雄人物生活背景,她遠到興都庫沙漠旅行,一筆一筆琢刻英雄的血淚史蹟,那是一枝藝術的刀筆。
她生活在高度經濟發展的瑞士,卻對人類獻出勇氣、毅力,甚至生命的英雄人物刻意深入地描寫,她見到一片悲慘的世界,與她生活的瑞士迥然相異;饑餓、貧窮、戰爭、骨肉流離失散……這些筆下人物佔據她生活的空間,日思夜夢……
顏敏如的哲學不是超脫世事,她將人生的苦難背負在自己的肩上,她雙眼流著的眼淚,一點一滴是對生命的憐憫與痛惜,崇拜英雄與內心的英雄意識,也是基於英雄雖不以佛學普渡眾生,卻以出生入死的勇氣去解救人生的苦難。
在小說結束前有一段描述:「我站在平台上,四周是綿延的高山,一股冷從我體內逐漸昇起,那不是讓人顫抖的冷,是種絕望。」
這是一段極為沈痛又極為精緻的描寫。翻閱顏敏如的小說,讀者逐漸離開世俗的世界,進入文學昇華的境界。
呂大明
推薦序3
《英雄不在家》的長處在於小說中「我」與「你」的故事,及其所屬的兩個世界可以形成一種對照或審美的張力。
我們所處的時代,似乎是一個悲劇已經衰亡的時代。在文學中,與原型悲劇英雄大相逕庭的「反英雄」大行其道,更有甚者,是嘲弄英雄的犬儒主義的聲音有成為文學傳聲筒之虞。實際上,在現代民主社會,「悲劇的死亡」並不像某些理論家所估計的那樣樂觀,在專制社會或前現代社會,社會衝突仍然在和諧的假面下劇烈地醞釀和爆發,悲劇時而發生,悲劇英雄仍然在場。令現代社會頭痛的恐怖主義,更是悲劇的雪上之霜。
處在和平社會的作家,以開闊的文學眼光來觀察、比較和描寫本土以外的世界,是他們的文學有可能步入崇高文學殿堂關鍵的一步。生於臺灣的顏敏如,走出了「睜眼看世界」的第一步。這對於作家,尤其是那些囿於「鄉土意識」的臺灣作家來說,無疑是具有啟迪意義的。
傅正明
作者序
沒有月亮的夜晚,星星卻是一整個黑空地亮著。兩名年輕男人走在前面。冷風襲襲。幾次問,這麼漆黑的四下,他們為什麼看得見路?怎麼知道腳步應當如何擺置?「好幾年,走慣了。」是唯一得到的簡短回答。
我騎坐的駱駝穩步前進在山石嶙峋的荒野峻嶺之中。牠不急,我的心悠悠地醒著,在一條顛簸暗蕪的冷路。
幾年遊走世人所認為的危險地區,因為逃脫不了心底幽微的聲聲呼喚。我想知道人們口中的傳評,究竟和事實相距多少。我想了解神秘古國裡的子民為何無法明白,一名女子如我,怎能穿梭遊歷、來去自如;正如同我無法明白,他們的小女兒如何以一個歪鍋煮出十二個人的伙食那般。
「駱駝平均可以活多少年?」「三十年。牠們工作二十三年,最後七年就在房子四周走走。」
我的坐騎是隻識途老駱,牠安靜而規矩,牢靠得足以讓人放心在牠背上打坐沈思。我的雙腳寒冷。
南西奈的沙漠山嶺,是否和喀布爾南郊的荒山有著相似的品質與氣勢?可是我的英雄在北邊。往北向上才是我該去的地方。
那個和蘇聯軍隊周旋,和塔里班沒有勾結的阿富汗人,我不認識,他卻有如在我腦中流竄的精神螻蟻,不剷除,日子又該怎麼過?是的,我的英雄在我腦中生活多年,他的形影在我身體內外川流不息。他踐踏我的腦神經,使我日夜頭疼煩躁。他從那個不長一物卻又茂盛豐沛的陌生山谷,帶著他遍受撻伐卻又驚心動魄的故事,開動他顛沛流離卻又能飛越雲端的越野吉普車,穿過地域時空,來到夏日裡草樹就要綠得滴汁的小鎮,硬要在我的生活中拉扯,不給安寧。他的故事不落實在我筆下,即便遙遠的或就近在咫尺的那個應該死亡的時刻來到,我也不能入土為安。
寫下吧,雖然是延宕多年,困難重重。然而,另一個性別、另一個國度、另一種領域、另一種思想、另一番經歷、另一頁人生,該當如何處理?怎麼型塑?如何拿捏?面對再也無法理出頭緒的成堆資料,在一種不得不平行書寫另一長篇文字的情況下,我在五個月內塑造出心目中的那個人,那個據說只要不遭到暗殺,便能改變阿富汗國家命運的人。
兩名貝都因男人走到後頭了,他們說,接下來這一段路駱駝認得。
「怎麼看得見,沒有光線啊!」「駱駝在夜裡看得比白天清楚。」「噢,像貓。」
近三千公尺的高山。我的腳好冷。
故事寫完了,我又在另一國度裡流浪,為的是要將那英雄從我記憶中剪除,不給他蹉跎我歲月的理由,更要他還我心緒的沒有牽絆。就在我徒步登上山頂,呼吸著冷冽的空氣,看到參著灰黑天空背景的橘紅光線出現時,似乎聽到嗡嗡轟轟的機器聲響,那載著阿富汗游擊隊指揮官被炸裂開身體的直昇機正在升空。遠在西奈半島的我,怎麼還能聽得到十年前他斷氣時的聲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