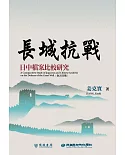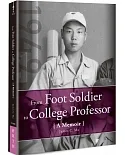前言
革命與戰爭,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的主軸。
近代以來,中國人在很長時間裡有一個基本的“焦慮”,即在西方列強有形的壓迫和無形的壓力下,一種持續性的“亡國”危機意識。“救亡圖存”這個詞,我們的歷史書也許說得太濫了,受眾難免有些麻木。但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說,“救亡圖存”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國家快要亡了,“救亡”刻不容緩。由急迫、急切,進而急進、激烈,幾乎是那一代中國人的普遍心態。
近代中國革命具有鮮明的階梯式、遞進式特徵。革命不斷推進,一次比一次激烈,總認為前一次不夠徹底,或者是不夠成功,還要“再起”革命。上層革命不夠,還要下層革命;城市革命不夠,還要鄉村革命;不單要對外革命,還要對內革命;政治革命不徹底,還必須通過社會革命“根本解決”……從而形成一種不斷革命、反覆革命的格局。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不久,革命者就覺得中國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還要繼續革命。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時,梁啟超即發表感想稱:“歷觀中外史乘,其國而自始未嘗革命,斯亦已耳,既經一度革命,則二度、三度之相尋相續,殆為理勢之無可逃避……革命復產革命,殆成為歷史上普遍之原則。”為甚麼“革命復產革命”?一個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後,“革命成為一種美德”,“革命”被視為神聖,“群眾心理所趨,益以謳歌革命為第二之天性。”於是一部分人“認革命為人生最高之天職”,以革命為職業。革命失敗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還要不斷革命。職業革命黨人的革命心態和行為慣性,在短時間內很難消除,動不動就採取革命的手段。
在中國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個關鍵的年代。1920年代開始,革命成為多個政黨的共同訴求。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產黨的“階級革命”,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幾乎同時並起,並形成一種競爭態勢。革命不僅為中國多數黨派所認同,也為多數無黨派的知識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種普遍觀念,認為革命是救亡圖存、解決內憂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於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識青年尤其成為革命的崇拜者和謳歌者。五卅之後,知識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熱潮。革命的目標,不僅僅是要“改造中國”,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為當時革命青年的口頭禪。
由於革命被建構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正當性,再沒有人敢於公開表示反對革命。當革命被神聖化的同時,“反革命”也被建構成為一種最大的罪惡行為。1927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反革命治罪條例》出籠,第一次將“反革命”作為一種刑事罪名列入法律。從此以後,“反革命”既是一項最嚴厲、最令人恐懼的法律罪名,又是一個最隨意、最氾濫的政治污名。亦因為此,“反革命”有時實實在在,有時則是虛無縹緲。難以數計的中國人被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地籠罩乃至葬身於這一名稱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廢除。兩年後,“反革命”一詞才徹底從憲法中被剔去。
中國革命在不斷遞進的同時,其路徑也具有內在的連續性。20世紀中國有過兩次命名為“大革命”的時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兩次“大革命”,並非僅是名稱的相近,其“話語”與方法均具有相當的連續性。第二次“大革命”中耳熟能詳的一些“革命”語詞,只要翻閱一下中共早期的機關報《嚮導》週刊,幾乎都能從中找到。第二次“大革命”中常見的一些“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掛胸牌、遊街示眾、大會批鬥、群眾公審,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等群眾暴力,湖南農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運用自如。
學界比較關注1905年廢科舉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實際上,廢科舉對1920年代的“大革命”也有非常直接的影響。
從科舉制度廢除,到新式教育的大量興辦,有一個過程,有一個過渡階段。辛亥革命時,主要由海外留學生主導,國內學生基本上沒有群體性地參與。到五四運動時,“國產”知識分子成為主體力量。1925-1927年的“大革命”,知識青年更為活躍。從新知識分子的成長歷程來看,1905-1925年,正好是一個世代更替的時程。
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中共的革命能夠發動廣大農民參與,是因為它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若看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一說法很難解釋得通。1926-1927年間,湖南有450萬農民被發動起來。這麼短的時間裡,這麼多農民被發動起來,堪稱奇跡。據毛澤東的報告,湖南農民起來以後,首先打“土豪劣紳”而不是分田分地。實際上湖南農民運動始終沒有發展到分田分地的地步。而且被打的“土豪劣紳”,並非普通的地主,而是那些在地方上比較有權勢的人物。種地的農民為甚麼首先把矛頭對準“土豪劣紳”,而不是對準從土地上直接剝削他們的普通地主?其實湖南農民運動中最活躍的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一批鄉村小學教師和從城裡讀書回鄉的知識青年。毛澤東考察的長沙、湘潭、衡陽等縣,是當時湖南農運最活躍的地區。這幾個縣,每縣均有一兩千小學教師參加農運。在當時中國鄉村教育非常落後的背景下,有這麼多的小學教師參加農運,是令人震驚的。當時長沙縣的鄉村共產黨員中,近60%是小學教師,真正貧農黨員僅佔30%。這裡面實際反映了科舉制度廢除以後新學堂大批量產生出來的知識分子的出路問題。這些在省城、縣城的新式學堂受過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小知識分子,他們往上晉升的空間極小,很多人在城裡找不到出路,只好回到鄉村去辦新式的小學,或變相的私塾。這樣的小學教師在1920年代的湖南數量非常龐大。共產黨能夠把湖南的農民發動起來主要依靠這批小學教師和回鄉知識青年。正是因為這批人領導農民運動,所以農民運動的鬥爭目標首先對準當地有權勢的“土豪劣紳”。實際上就是這批小學教師和回鄉知識青年跟鄉村既有的“精英”爭奪權勢、爭奪資源。
早在1925年底,中共中央就專門通過了一個《鄉村教師運動決議案》,指出“為要發展我們的鄉村工作,我們應當首先注意於在鄉村中智識比較進步而有領袖地位的鄉村教師”;“鄉村中教師多系青年,窮苦被壓迫不能升學的師範中學學生”;“可以做我們農民運動的著手處”;“他們可以用種種方法輸入革命思想於青年農民中間”。所以,發動鄉村教師參加革命並非湖南一省特色,而是中共中央決策的產物。
總之,1920年代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型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青年黨固然誕生於這一時期,中國國民黨也在這一時期改組“再造”。三黨不約而同地厭棄西方議會政黨體制而選擇有“主義”信仰的革命政黨體制,其影響極其深遠。
20世紀的中國革命,與18世紀末期的法國革命、20世紀初期的俄國革命,被並稱為世界歷史上三次最具影響的革命。和另外兩次革命相比,20世紀的中國革命持續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規模最大。一般認為,法國革命自1789-1799年,只有10年左右的時間;俄國革命最早從1899年算起,最晚到1921年,也不過20餘年。而中國革命如果往前追溯到1905年同盟會成立,往後延伸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則長達70餘年。早在192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中國革命已經成了一場“慢性革命”。
也可以說,中國革命是一場漫長的革命。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將中國革命的下限延伸到文化大革命結束。1949年的“解放”,只是國家政權的更替,並非中國革命的終結。1949年以後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仍在繼續。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國的局部地區進行,而1949年以後的每場運動,無不席捲全國。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參與革命的人數尚有限;而1949年以後的革命,則是全民性的社會動員。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看,1949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更劇烈,更複雜,經驗和教訓也更豐富。
革命不是孤立發生的,革命史也不應該孤立地研究和書寫。20世紀的中國革命應該放回到20世紀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會文化的大視野下考察,不僅要研究“革命”,同時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將革命的主體力量和革命的敵對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個歷史場域來考察,才能再現其“眾聲喧譁”的複雜歷史本相。
本書大體由四個相互關聯的專題研究彙集而成。第一、二章試圖從思想史的視角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社會思潮的流變;第三、四章側重從文化史的視角分析北伐時期中國三大政黨的“革命”話語;第五、六章從社會史的視角描述共產黨在城鄉基層社會的動員;第七、八、九章則從政治史的視角探討國民黨高層權力機構的演變以及黨在軍隊、大學的組織形態。
本書先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2010年出版簡體字版。此次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慨然出版繁體字版,首先得感謝陳翠玲總編輯的熱心關照。與簡體字版相比,繁體字版不僅調整了裝幀編排,內容也有所精簡,減少了以下四章內容:一、湖南會戰:戰時國軍的作戰能力;二、紳權:鄉村權勢的蛻變;三、縣長:基層地方官的轉型;四、區鄉保甲:縣衙與村莊之間的政治。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