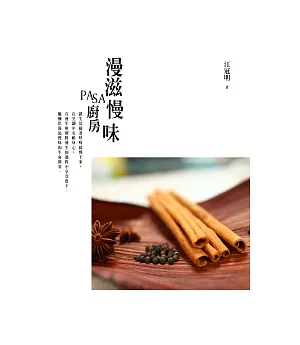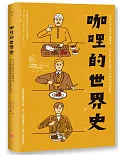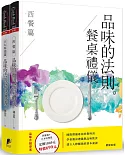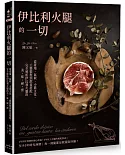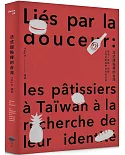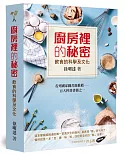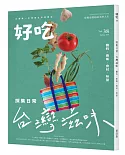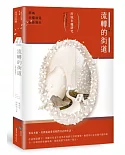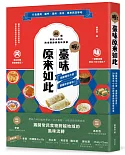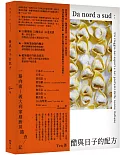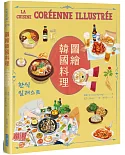選書緣起
TVBS週刊總編輯、生活旅遊美食家邱一新喫遍臺灣美食。有一天當他拜訪了江冠明的PASA民宿,品嚐了PASA廚房的美食之後,心中不禁感嘆,這麼一個美好的減法烹調理念,以最少的調味料,料理出食物的真滋味,若不介紹給更多人認識品嚐,豈不太可惜。
於是,在邱一新的推薦下,我們公司同仁也在過年期間團訂了五十幾顆PASA廚房的招牌創意年菜——都蘭豬腳。以慢火炭烤數小時的都蘭豬腳一片片切下來可以下酒、配飯,冷吃熱食各有風味,香味四溢、Q嫩彈牙,完全不油膩。剩下的豬大骨還可熬煮出一鍋十人份白色湯頭,在過年期間贏得了全家大小的讚譽!
經過這麼多同事、家人親自品嚐過後,我們更加確定,烹調不需高深的學問,料理也不必過份繁複,只要食材好,簡單的調味,也可以創造出健康美味的食物來。
江冠明的料理都是自己研發,由於不是廚藝科班出身,因此沒有太多複雜的烹調技巧。他講究食物的滋味互搭、互提、互補……,簡單易學,十分適合沒有烹飪基礎的一般大眾。
序
風箏與滑翔翼
冠明是我見過的朋友當中生命力最旺盛的一位,他始終保持對許多事物的好奇與熱情,並從不吝嗇將自己歸零,投入另一個對他來說可能是完全陌生的領域。出入之間雖不至於說是毫無掙扎、困惑,但他那頗為自戀又容易自我感覺良好的性格,總是讓他很快地走出死蔭的幽谷,迎向一個被他「說」得有生有色的世界。冠明實在是一個很幸福、很自主的男人。
1997年他放下台北的一切瓜葛,住到我台東故里pinaski部落。我沒問他原因,按我對他的瞭解,詢問一個浪子為何要去流浪,本身就是一件荒謬的事。打從80年代末期他扛著一架厚重的大攝影機,和一位小助理闖進我東吳大學哲學系的研究室起,我便強烈地感受到冠明是一隻大風箏,總是乘著風高高揚起,繫住的線又緊又難以駕馭。果然,在台北相處期間,他充滿熱情和自信參與我們山海文化雜誌社的各項活動,橫衝直撞於紀錄片、社造、原運、學術辯論等大大小小的場合之中。他下筆既快又有主見,不但批判漢人學者的立場,對原住民知識菁英的挑戰也毫不手軟。可以想見,像他這樣一隻東飄西盪又難以駕馭的大風箏,當然不可能歸屬於任何一個group。那一年的東移,應該是他對都市和所謂學術圈各種各樣虛矯框框的厭倦。他不想跟台北玩了!族人告訴我,不知何時來了一位皮膚白皙、體態頗為健美的白浪,戴墨鏡、穿短褲、露大腿在部落遛狗。兩年之間,他和我的部落族人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大風箏顯然還不想把繩子放下來。
後來我知道他搬到「人文薈萃」的都蘭,一個靠海、迷人又閒慢的阿美族部落。名叫「都蘭」,非常能相應那些厭惡「體制」者的情緒。其實那個時候都蘭早已聚集了一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風箏。我們的「大風箏」會在此一待十年,他雖說當時只是隨興選擇閒置農舍落腳,但照我看來,這多少帶有幾分必然性。卑南族都蘭山的神話傳說裡,也提到大風箏,敘述兩兄弟與山下古遺址主人一場驚心動魄的恩怨情仇。都蘭山原來就是放風箏的地方。
談起pasa廚房,冠明強調他的慢食慢味,主張一種素樸原汁的減法哲學,並反覆見證他那無心、即興、當下的調味禪悟。那些往來於pasa廚房的可憐的都市人,羨慕冠明對野性的狂熱,欣賞pasa調理出爐的美食中所溢出的既自在又自由的風格。但,當這些身負家庭事業乃至於國計民生之重責大任的都市朋友,慨歎地表示退休後也將歸隱山林時,冠明一眼就看穿說這些話的人恐怕永遠達不到自己的期待;因為他們根本不是風箏,他們「腳踏實地」到完全不敢離開地面,這是我們大部分人的宿命。
其實,要當風箏並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首先,你必須要有一種本事,在毫無依傍的情況下,仍然有生活的能力。沒有錢、沒有科技,單憑自然所賦予的本能,便能充滿安全感地應付周遭的挑戰。冠明初到都蘭,自己動手動腳接水管、種樹、修籬笆、蓋涼亭、搭廚房、做餐桌…....,看清書本知識、職業知識和生活知識的差別。這是要成為風箏的第一步。其次,你必須常常保持自我感覺良好,避免自我虐待。冠明懂得欣賞自己,總是有辦法將自己的情況和看法用非常吸引人的方式表達出來。二十多年來,我很幸運常有機會或在深夜、或在午後接到他的電話,聆聽他像個大孩子一樣,興奮地朗讀他剛寫給某雜誌社的新作,並熱烈地補充闡釋自己的觀點。這是要成為風箏的第二步。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慷慨。對時間、對成本、對感情、對自己所擁有的事物的不計較、若即若離,隨時可以做歸零的處分。冠明從做紀錄片、參與原運、寫後山音樂、搞民宿、弄廚房,甚至對待自己的婚姻,都能舉重若輕、揮灑自如,他是一個對自己、對別人都非常慷慨的人。他是風箏。
坦白講,我認為無論從民族性格或歷史遭遇來看,原住民比冠明更有條件成為風箏。他們保有豐沛的自然本能,自我接受度高,又慷慨粗放,不斤斤計較;長期的歷史潰敗,也讓原住民無可歸零。都蘭部落聚集那麼多來來往往的原住民風箏,當然不會是偶然的事。但令我好奇的是:為什麼唯獨冠明的風箏得以虎虎生風、近悅遠來?原住民朋友「即興」了半天,既弄不出pasa,且疲軟猶若扯不高的風箏。其中的差別到底是什麼?問題常在我腦海縈繞。
仔細回想二十幾年來冠明的生活軌跡,逐漸體會到他浮沈漂泊的浪子生涯,背後其實有他積極、自負又不服輸的一面,他的即興和流浪是充滿自主性的。我愈來愈認知到冠明之所以看起來像隻「大」風箏,是因為他根本不是風箏,他其實是滑翔翼,對風向和氣流有著精準的掌握,起降不假他人牽線,隨緣卻自主。不僅如此,冠明的隱居既不槁木也不死灰,透過網路和筆耕,他有他自己和主流社會對話的方式與管道。他喜歡且擅長說故事,讓人聽了也想跟他一起去流浪、去隱居。他寫pasa廚房每道菜色,過程的描述彷彿禪宗語錄,兼具哲學和文學的壓力,令都市俗人自慚形穢。
我因而對冠明開始有另一番期待,想請他設計一套課程,就像他教授「民宿學」一樣,為我們散列在台灣各地的原住民風箏上課,教導我們怎樣從風箏轉變成滑翔翼,大家一同自主的去流浪。
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主任委員
導讀
都蘭有PASA: 「飲食即存在!」
都會的文人雅士與老饕客,如果到現在還不知道台東都蘭山中有傳奇的PASA廚房,那可要多注意了。一位來自台北的江冠明已經在此自建農舍、悠閒慢活快十年,而他嚮往「原味、減料」的烹調與田園山居,一不小心就征服了各方訪客的味蕾。
冠明是肉食者動物(吃素的人不要靠近),他最初靠「紅酒羊排」,發展出碳燒慢烤的絕活,繼之又研發了令人垂涎的獨門「青醬」,甚至挑戰自己的極限做出驚奇的「野菜素麵」,令很多遠地聞風而來的挑剔美食家也感覺驚艷,嚐過的人都說讚!從來沒拜師學藝的他,個性爽朗喜歡招待朋友,又做菜又寫文章,特別是當他處於微燻的狀況。「美味」拉近了理性與感性,都市與山野,朋友與陌生人,是他進行溝通的橋樑。而這本書似乎正要揭開他的江湖一點訣,把他的遊戲般的廚藝與生活體驗,寫成「食譜」,彷彿應證了「料理鼠王」劇中
”Anyone Can Cook”的名句。
「食譜」究竟是什麼?食譜記載關於烹飪使用的原料與料理方法。可是究竟是關於「誰」的烹飪呢?傳統的家常菜多靠口傳,媽媽的美味用不著食譜。食譜現身最早的歷史,並不是因為平民百姓的需求,而是為滿足宮廷貴族無止境的挑剔胃口與地位炫耀。17世紀後半歐洲出現新興的資產階級,有錢大戶更開始用「宴會」、「舞會」來「比闊」、「鬥場」。近代社會從封建而資產階級化,無意間誘發了第一波的「食譜」的大眾普及與流行。
其實東西方追逐奢華美味,誇富擺宴的情形相差不多。傳說中大清皇朝的「滿漢全席」是經典代表。在帝國瓦解後,熊掌魚翅、□魚燕窩,百道山珍海味「名菜」在20世紀港、臺二地也借題發揮,成為有錢人爭奇鬥豔的華麗宴席。
時空流轉,1960年代台灣開始工業化,打破農業生活與傳統束縛。年輕婦女進入工廠成為作業員,或者進入都市服務業,「女強人」也不再是小說的夢想。離鄉少女對自由戀愛與白馬王子的渴望,對婚後的小家庭的欣羨,從學校到職場的快車道,無意間讓很多人喪失了「家傳的媽媽手藝」。而正在此刻,「台灣電視公司」的開播(1962),不但創造了「瓊瑤式」的七點通俗劇,同時也創造了傅培梅在電視教做菜39年的傳奇,導致今「培梅食譜」仍被廣大華人社會奉為家庭廚房的經典。彼時的兩項流行,愛情劇與電視烹飪,不約而同地伴隨者台灣中產家庭與「職業女性」誕生,標誌著嶄新時代的降臨。
台灣在90年代所經歷的全球化與民主化體驗,也悄悄地改變了我們的飲食品味。前者帶動了都市人對異國飲食的欣賞,後者激發出強調本土化與個體性的「創意」料理。而冠明的《慢滋慢味.PASA廚房》的出版,或多或少也反映2000年後的另外一種「新台灣人」的面貌:他們經歷過80年代後社會運動的狂飆,逐漸厭倦政治的反覆與勾心鬥角、工商社會的勢利與掠奪、都市的緊繃與拘謹、甚至對學術研究的框架也覺得虛矯。好像冠明在當時似乎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在獲得碩士學位之後不知不覺地走上了「自我放逐」之路,彷似隨浪而擱淺在東海岸的漂流木。但誰料得到轉眼間,他不但發現自己正「粘」在都蘭的土地上,而且生長成一種自由自在、隨興烹飪、回歸原味、在田園勞動中尋求滿足的鄉野生活。《慢滋慢味.PASA廚房》帶給人的不只是味蕾的愉悅回憶,而是一種將飲食美味、個人風格、鄉野景緻、人情溫暖,巧妙融合在一起,令人難忘的人文與美學經驗。
張茂桂
社會學者、大學教授
作者序
漫滋慢味的餐桌人生
醞釀《慢滋慢味.PASA廚房》的生命歲月,彷彿詩人惠特曼在田野中漫步的詩,帶著赫曼.赫塞小說漂泊悠遊的鄉愁,穿越奧德賽史詩的天空,徬徨在杜甫與李白千山萬水間,漫遊於泰戈爾《園丁集》的浪漫歌聲中,讓一切思緒如晨霧般飄浮在庭園涼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