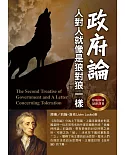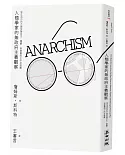序
王汎森
二十年來,余範英女士及她主持的「時報文教基金會」、「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秉持著知識分子的熱情與使命感,前後舉辦過八次公與義系列研討會。這本論文集收錄的正是今年四月一、二日所舉行的「余紀忠先生百歲紀念研討會」,也是第八次公與義系列研討會。
從第一屆「公與義系列研討會」開始舉辦以來,我便是發起人之一,此後在歷次會議中,因余範英女士的鼓舞與催促,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參與。在我看來,以「公與義系列研討會」來追念余紀忠先生是一件再恰當不過的事,因為與會者和余先生之間皆有一個共通之處,即知識分子對時代的關懷與批判。余紀忠先生曾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後入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繼而從軍、辦報,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人,想要參與時代、批判時代、並且進一步塑造時代的知識分子典型。而「公與義」這個論壇的參與者,則代表一群當代讀書人在過去若干年來關懷時代、批判時代,並且努力希望形塑一個公平且正義的社會。兩者在實際行動與議論方面,當然會有出入,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力也有不同,但是在以「知識分子」自期,希望盡自己的力量為社會做事的想法卻是一致的。
然而,我最近注意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逐漸趨於沒落。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是從十九世紀中期的俄國開始,而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大概是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在法國德雷佛上尉事件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但法國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認為早在西洋中古時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了。這裡倒不是想針對這個爭論作任何討論,而是想說明「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與理想,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輝煌年代之後,現在已經有沒落的傾向。
美國的雅各比(Russell Jacoby)於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於二○○一年出版了《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 a study of
decline),這兩本書在西方引起極大的迴響,但是不知為什麼,當時居然未引起我太大的興趣。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當時尚未察覺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有任何危機。然而最近兩、三年,我開始覺察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處於沒落中。
為了印證這個觀察,我在今年六月初請同事上「聯合知識庫」查詢(感謝陳亞寧替我查詢,查詢時間為2010年6月8日),結果得到如下的數字:「知識分子」一詞在一九五一-一九六○於該資料庫中出現六四○次;一九六一-一九七○年之間出現一一○○次。它的高峰是一九七一-一九八○(一九一○次)及一九八一-一九九○(二五九○次)。所以一九七○-一九九○這二十年是台灣「知識分子」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時代,此後的十年,一九九一-二○○○比前十年少了一千多次(一五二五次)。而最近十年(二○○一-二○一○)又比前十年少了約五百次,共有一○一九次。
我又進一步整理出二○○一年到二○一○年這十年間的數字,發現二○○一年至二○○六年之間,「知識分子」出現的次數大約維持在一百多次,可是從二○○七年開始由三位數變成兩位數二○○七年六十一次;二○○八年五十五次;二○○九年六十一次,到了二○一○年六月共有二十二次。同時,我也發現到「公共知識分子」一詞先前從未出現過,二○○四年是第一次出現,僅有二次、二○○五年二次、二○○九年一次,到二○一○年六月為止則有二次。可見這個詞的出現是過去五、六年間的事,且出現頻率頗低。
上面這個簡單的統計,當然存在著偏差的可能。但是它卻多少印證了我的直覺,即「知識分子」一詞確實正在逐漸消失中。這個詞的起落,蘊含了重大的歷史意義,即一個以「知識分子」自許的階層正在消失中。無獨有偶地,在我寫這篇序的同時,我注意到有兩篇文章提出近似的觀察。它們分別是洪裕宏的〈台灣公眾知識分子的末日〉刊登於今年六月號的《當代》(一四○期),及吳介民、范雲、顧爾德主編的《秩序繽紛的年代--一九九○-二○一○》(二○一○年七月)一書中的郭力昕〈公共知識分子的隕落?〉。「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有九十年左右的榮景,沒想到卻在近年的台灣社會中逐漸消失了。
因為本文性質所限,無法在這裡將我最近幾個月對這個現象所做的初步研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陳述。不過我必須指出這是一件有重大意義及深遠影響的變化。凡關心「公與義」的朋友們都應屏息凝視,密切注意:將來「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將由什麼樣的階層來扮演,或是將來的社會根本不需要「知識分子」等一連串的問題。
本文一開始我便已經提到收在這本論文集中的文章作者都關懷社會,他們對現狀有所批評也希望對未來有所開創,而他們大多與余紀忠先生有過交往,對余紀忠先生一生的志業有著深刻的理解。
所以我接著想要談談余先生。我與余紀忠先生的接觸開始於一九八○年代,但因為我們的年輩相差太遠,所以我對他多彩多姿的一生了解並不多,只知道他在南京中央大學就讀的時期便是一位憂國憂時的學生運動領袖。
一九八○年代我偶然讀到一本英文書(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其中居然提到學生運動領袖余紀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中央大學學生群情憤怒痛責政府守土無方,他們聽到一種謠言說外交部長王正廷事先收到從日本大使館傳回的情報,知道日本即將進攻東北卻毫無作為,事變發生時還流連西湖,一群憤怒的學生遂衝進外交部辦公室。美國學者John
Isreal在書中這樣記載:「學生領袖余紀忠先生說:學生對外交部長王正廷的憤怒,來自一份教授的報告。這位教授的兄弟當時正擔任駐日外交人員,這份報告說王正廷忽略了來自駐日外交人員的警告─日本即將進攻東北,而當日軍進攻時,王正廷還在西湖遊玩。這個消息迅速傳遍全校。校園裡到處有人咒罵王是惡棍、叛徒,於是學生們計劃懲處王正廷。
中大學生與一些教授(尤其是何浩若)直接衝進外交部大樓找王正廷。找了一陣子,不得要領,一大群學生遂轉向,衝入行政院,數百個仍留在外交部的學生則繼續找尋王正廷。學生們後來找到一個房間,門口站著刀已出鞘的衛兵,而王正廷就在裡頭。
王正廷一見學生湧入,遂衝向窗前,王正廷的頭部被一瓶紅墨水砸中,臉上流下兩道深紅色的墨水。」
John Isreal說這一段史實是他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台北訪問《徵信新聞》的余紀忠時所做的記錄。這本書中還有兩段與余先生有關的文字,主要是與十九軍抗日時知識青年的激越情懷有關,這裡不再詳引。有趣的是在一九九○年代後期,我一度問余先生這本英文書的作者及這段訪問,余先生竟完全不記得了。
我只是想以上述這段文字說明,余紀忠先生在青年時期便已是一個熾熱關懷時代的知識分子,在他往後的人生中也以同樣熾熱的心情關懷與參與近代歷史。我印象中的余紀忠,並不愛回顧過去,一旦經過深思並決定方向之後,便招集志同道合的人不屈不撓地去做。他不願隨時代的波濤浮沈,總是要引領時代的風勢,到處成為一種力量。
我從二十幾歲起,就因為種種機緣,得到余先生許多鼓勵與支持。我必須說余先生鼓勵與支持過的人很多,我絕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但是對於一個感受力正強的年輕人,他當年那些或有意或無心的支持與謬賞,對我產生很大的暗示作用,並激發我努力的意念。如今,二、三十年過去了,我也到了兩鬢飛霜之年,迴思當年那些熱情的談論,內心依然波動不已。所以當主辦單位要我替論文集寫序時,我雖因自忖份量不夠一再推辭,但是最後仍因感念於過去的情誼而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在這個知識分子文化急遽沒落的時代,除了回顧余紀忠先生一生的關懷與志業外,我們還應當鄭重地思考知識分子文化未來的動向與職責。
【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黃榮村
紀忠先生是有古代士大夫之風的領導人,也是一位真正的時代先驅者。他是一位特大號的民間報人,在辦報之時一直具有時代感的見識與彈性,從各種角度來尋找國家社會的出路,在很多不確定的疑難時刻,經常有膽識作出日後看來堪稱正確的決定。吾生也晚,未能及時多向余先生請益,可說是平生憾事之大者。懷念一位大人物,常觀察其在動亂不確定之時艱困之時的洞見與言行,我祇有一句大家熟悉的話可以說,那就是「哲人日己遠,典型在夙昔」。
此次為余紀忠先生百歲所舉辦的紀念研討會「面對公與義:再談社會發展與變遷」,呼應了十來年前開辦「邁向公與義」系列研討會的主軸,那次會議余先生親臨主持與總結,這是一個古老但恆久的重大課題,紀忠先生在余範英協助下,當成一件大事來辦,若無燒不盡的熱情與清晰堅定的理念,何以致之!那段期間剛好也是台灣五十多年來第一次政權即將轉移之時。十年下來,台灣社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學習政權轉移的教訓,終於了解到國家重大政務具有連續性,重大到不能當作意識形態鬥爭的平台;也深切了解到國家領導人的氣度與格局,真的會實質影響到國家競爭力與國家前途,所以應有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胸襟與作為,往外開疆闢土,聯合友善待我之人士爭取終將對我有利的難纏之人,共創有尊嚴有發展性的未來,而非在宮中府內自度春秋。
本次紀念研討會對國家、社會、兩岸、區域、以及政黨、政治等項,都提出甚多論述及實踐方案,認為應在過去的傳統與未來的場景中往前看,找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讓台灣保持生命力,提高競爭力。在會議中,大家都不由自主的想到,假設站在紀忠先生的高度與觀點上,我們是否應問台灣該不該有下一步的改革,要怎麼做下一波的改革?如何去體會台灣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與漸趨邊緣化?要如何在這些限制條件之內思考應有的改革?歸納起來,很多問題沒有答案,但有可以努力的方向;大家心中仍有焦慮,但遏止不住心中那股知識分子的關懷與理念。
六月底我帶了二十多位醫藥學生與醫師到非洲「重返史懷哲之路」,沿路上問了學生幾個問題:(1)史懷哲是先有熱情再於三十歲之後才去唸醫學院,還是當了醫學生之後才被教育出熱情?(2)什麼樣的熱情與什麼樣的中心理念,可以讓他一生無悔的關懷投入一輩子,除了非洲行醫還持續關心人類文明的發展與存續?我想,同樣的思考方式也可以用來理解紀忠先生。他是一位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事事關心的人,這是背後驅使余先生一輩子持續關心與熱情投入的源頭。很早就在燃燒的熱情促使他排除萬難開辦徵信新聞報,與日後的中國時報,在此過程中則發展出有系統的中心理念並予以實踐,持續一生。
過去的紀忠先生心繫台灣,參與了關鍵時刻的諸多決策與報導;今天的余先生魂遊故園,想必有更多的憂國之思。今日台灣的知識分子,行走在多風的彎路上思索國家社會的未來,偶而瞥見前方似有引路的巨大身影,心中不祇興起一股「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的歷史感,趕路的腳步也應有不時奮起的現代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