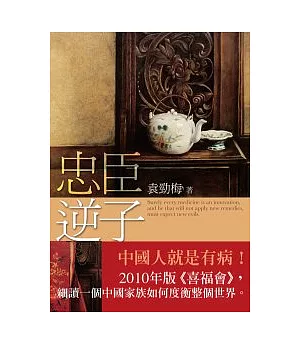推薦序
天生的小說家
北京豆瓣讀書網說袁勁梅出身大家族,曾祖父是前清戍邊功臣,祖父是辛亥革命志士,父親是著名生物教授。若真,則這背景和〈忠臣逆子〉中的戴家小姐相似。前教育部長吳京,是她的表哥。
為了分別「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毛澤東在一九二五年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以為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把中國當時的階級細分如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中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自耕農、手工業主、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半無產階級(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無產階級(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工人)、以及遊民無產者(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中國三、四○年代的小說主軸,要不是寫這些階級間的鬥爭,就是寫對這些鬥爭不休的世界感到絕望;前者就是革命文學,後者就是頹廢文學。事實上,這兩種文學對於中共的革命都有實質的幫助。以後,要到一九八○年代,鄧小平堅持改革開放,大陸在借鏡和追求現代化的同時,現代主義思潮才開始更加湧入大陸的文學創作,而有了文革後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以及隨後我們熟悉的各種現代流派以至後現代。袁勁梅的小說圖像,難免改革開放後的色彩,但是,〈忠臣逆子〉幾乎可以看成三○年代小說的總複習,而且為那個時代的革命小說和頹廢小說整體寫了續篇,這因為〈忠臣逆子〉中的戴家,是毛澤東「中國社會階級分類」之首,被說成中國革命最壞的敵人。可是這戴家看起來並不全是那回事,並不那樣壞,而且忠順臣服極了,也就糊裡糊塗倒了門楣,花果飄零;一點兒也不像無論是國共分裂前的國民黨或共產黨所要鬥爭的土豪或劣紳。在那種革命的年代,真正的土豪和劣紳隨時可以搖身變臉,幻成國民黨或共產黨;倒楣後的戴家故事,相關好幾種階級,也就證明了那場革命的虛幻。
〈忠臣逆子〉中戴家的崩潰瓦解,我看是遑遑如《紅樓夢》的賈家。但是,在《紅樓夢》的結尾中,賈寶玉光頭赤腳,披一領大紅猩毯在雪地向父親拜別,出家去了,極其苦楚;戴家小姐則乾脆認賠,更加入世,寫了〈忠臣逆子〉來開示一種無比的寬容和睿智:
可是,在我還時常出入於我奶奶的廁所和劇院的時候,上流、下流在那中國的局戲裡是分得很清楚的。為什麼要分得這樣清,一是因為中國那齣戲的戲局是根據「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哲學設的,二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家像中醫,從一代代先人帝王治國的經驗中收集出無數「鬥」的法子,一一拿來試。人多,人窮,「鬥」就成瞭解決社會問題、控制社會權力的一劑藥方。
我和我奶奶一起看戲多了,我奶奶還教了我幾條看戲的法子。她說:「人年輕的時候都在演戲,演戲的時候,就跳不出那個戲局,到老了就愛看戲,看戲的時候,還是跳不出那個戲局。人在戲局裡,好壞都由戲局定了。啥時候人演戲、看戲的時候,都時時知道那不過是個戲局,人就真會看戲了。雖是這個理,就是怕人做不到。(袁勁梅,忠臣逆子)
這樣的戲局,在台灣看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第一次在二○○三年「聯合文學新人獎」中篇小說決審作品中讀到這篇小說,雖然字裡行間多的是頑笑或自嘲,我還是能夠深深感受到作者對人性的悲憫;這和詩人雪萊讀《堂.吉訶德》,說「這個悲劇讓人淚水中帶著微笑」的感受,我想當是相似的。事實上,我後來也知道她每年總會帶美國學生去大陸的窮鄉僻壤,做旅遊和戶外教學。
袁勁梅當是在評審紀錄中,讀到我的善意;我對於這位可能的戴家小姐,確實也很同情,當然我非常欣賞她的寫作潛力。二○○三年,我那時在聯經出版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兼〈歷史月刊〉總編輯,就請她為月刊系列撰寫〈美國小鎮文化〉,鼓勵她既然離開故土可以寫成美國作家,如此就得好好認識美國;美國畢竟不是電視或電影上的五光十色和膚淺,何況她任教的大學所在還有法、英和印地安文化。我這樣建議是不希望她終究會像大部分的華裔作家,寫盡故國材料後,隨波逐流,在現代或後現代的形式中泡沫化(我們文學界常在跨科際的借用中把思想削足適履成形式)。我當然知道她訪問過一些美國小鎮,但是在本書她的自序中讀到她走訪了一百多個小鎮,讓我非常吃驚;美國小鎮間不像台灣的人居聚落多是櫛比鱗次,其間距遼遠開闊多有詩人艾蜜莉所見的荒蕪,或者隨時可能跑出小說家福克那筆下的熊。至於在〈羅坎村〉那樣比較中、美文化、人性以及農民的性格,而且能夠生動有趣的寫出美國小鎮的人物和生活,是她自己的天份。
因為忙,我很少給人家出書寫推薦序;為袁勁梅寫,因為她表示自己是在「聯合文學新人獎」中獲得鼓勵和自信,而能開始在大陸投稿,且即連獲殊榮。所以,我特地寫來讚美「聯合文學新人獎」,但是,袁勁梅確實也有特別值得讓人欣賞和學習的,因此,我也以為非寫不可。
相當的程度,聯合文學忘了這位自己肯定的作家;一方面因為各種文學獎中因緣際會多的是曇花一現的新人,一方面因為袁勁梅自己的憨厚,她沒在大陸的小說和小說集出版,或在台灣的出版社用掉〈忠臣逆子〉,說是:
這幾年,在大陸發了不少散文和中篇。基本是每年都有入選〈年選〉、〈年鑒〉或獲得文學獎。所以,總是有約稿,一忙,就把為台灣讀者寫作放下了。心裡是愧疚的,因為畢竟我的作品,是在台灣文學界首先得到肯定的。正因為〈忠臣逆子〉是在台灣得的獎,所以,覺得出書,又名叫〈忠臣逆子〉(五個相關中篇),一定是應該在台灣出才對。也算給台灣讀者一個報告。得了獎之後,這個作者都幹了些什麼﹖這五個中篇應該說都是好的,是可以拿出去見人的。這就沒有辜負“新人獎”。也有朋友讓我在大陸的〈中國作家出版社〉出,我好像覺得還是應該在台灣出才對。(袁勁梅致東年,2009年12月6日)
這讓我想起哲學家、數學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素,曾經回憶兩位小說家。他批評一位極富盛名的小說家汲汲營營以沽名弔譽,人品極壞(我姑且隱其名),另讚美康拉德;說自己曾在康拉德死前看過他一次,又說康拉德曾經埋怨有人不了解他的海洋文學,而辯護說他的文學同樣是在追求人類的秩序。羅素沒說康拉德表示的人類的秩序是甚麼意思;我想我可以替羅素或康拉德說個清楚。那種秩序,就是航海精神。航海是一種團隊的探險,需要勇氣、忠誠、服從、踏實、協調,以及要有能夠容忍困境、損失和各種苦腦的修養和訓練(這正是康拉德小說的主題)。這種精神其實也無關海洋不海洋,無關個人的自由和發揮,有關人際或公民社會的標準,也正是中國和台灣社會所欠缺的。戴家小姐,在〈忠臣逆子〉中坦然面對自家在大時代中瓦解的困境和損失,正同這種精神。
乍看我提起羅素這樣說兩種小說家,袁勁梅一定訝異,我如果再寫維根斯坦,她一定更吃驚;這因為我剛想起去年她給我的一封信裡,提到她的符號邏輯學導師科比教授(I.M.Copi)是羅素的學生、維根斯坦的同學。
維根斯坦有一本小書《邏輯哲學論集》是二次大戰後那幾年中最具影響力的哲學著作。這本書向讀者提出一系列簡潔、封閉的「命題」;其中大部分的命題都以「不證自明」的方式表示出來,而且都被認為是「等值」的。他以「只要是可以說出來的話,都可以說得很清楚」這個命題為起點,證明「可以說出來的話的確很少」,而「這些極少數的話都可以用邏輯符號或最好是用日常語言來表達」。我以為這樣的概念在小說寫作來言,說的正是「圖像語言」和「口語」。他還主張人們所提出的大多有關哲學的命題和問題並不是「不真」而是「沒有意義的」。我以為小說寫作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小說寫作問題,不是好不好真不真,而是沒有意義。
袁勁梅糊裡糊塗選了科比(I.M.Copi)的課,以後才知道他是符號邏輯之父、現代電腦語言奠基人。她是他的關門弟子,得意門生;我在「袁勁梅的BLOG」讀到她這樣回憶她的恩師:
我們這些貧窮的中國留學生,就那麼一點獎學金,去買菜都是揀最便宜的買,有點錢還想著往家裡寄,我路過"金環/王環"無數次,從沒動過進去吃一頓的念頭。科比博士把我帶去了,我大吃了一頓不說。沒吃完的菜又都給我帶回來,不僅如此,以後每隔一個星期,科比博士就把我帶到"金環"大吃一頓。我每次得意洋洋帶著沒吃完的菜回到系裡,其他同學就會不無羡慕地說:"科比博士又請客了?"....科比博士不僅請客,還講老故事給我聽,這些老故事天南海北,有的深刻,有的幽默,每個都充滿人性。(袁勁梅,人性和符號──我和符號邏輯大師I.M.科比博士的故事,blog.sina.com.cn/yuanjinmei)
這樣我們看到了科學、哲學對一個小說家的技術和思想傳承,看到了「感性」和「精確」並存;而我藉此要說的是,寫作,特別是寫小說,主要是使用右腦。當然,因為大家已經習慣把包括小說的文學,視為「藝術」,是使用左腦;所以,我將左右腦的官司功能,分列於後,讓大家比較參考。左腦功能:說話、閱讀、寫字、綜合性的語言記憶、抽象的分類、學習音樂的能力、連續性的細微動作、一次可看見一項以上的事物、詳細畫面。右腦功能:閱讀中能掌握隱喻的含義、容貌識別、身體左側及視覺空間的合一、空間知覺、路徑探索能力、視覺結果、音樂的感覺、綜合記憶的形成能分辨左右、適當畫面的形成。(Thomas
R. Blakeslee,1981)。我相信讀者,特別是小說創作者,可以在〈忠臣逆子〉的文本中,讀到寫作的右腦。
袁勁梅在自序裡說了不少自己的作品,我就不再畫蛇添足;寫完了戴家,我們也會期待她多寫別家,或者再寫中國革命的第三部曲,因為現在大陸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多如牛毛,需要幽默。她的寫作態度、現象,特別是她的小說語言和思想,以及「聯合文學新人獎」如此奇妙,也都是我極力推薦的。
東年
作者序
本來我並不能肯定我可以寫小說。二○○三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獎」告訴我:你可以!這個「可以」,在我眼前打開了一扇門,門牌叫:「可能性」。我心惴不安,又無比興奮地走進去。一路都感到《聯合文學》的文學前輩們對「新人」的扶持和指導。這種長久的扶持與指導,在多年之後,讓我認識到「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意義不僅是對「新人」說一聲:來吧,你可以走進文學殿堂,而是把一棵偶然從地裡長出來的橡樹芽兒澆灌成橡樹。我就是那個非常運氣的橡樹芽兒。
在這幾年裡,二○○三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評委東年老師指導我幹了一件大事:研究美國文化,從最基礎的美國小鎮研究起。一次又一次我覺得沒啥可研究的了,東年老師又給我指出一個新的方向。一走進去,果然又是柳暗花明。在走訪了一百多個小鎮之後,我覺得,我對西方文明可以說話了。
故事有各種各樣的寫法,我選擇了寫中國;中國事,中國人,中國文化。西方文化是一池水,中國文化是另一池水。以西方文化作參照系,看中國文化,如同一條跳出池塘的魚,回頭一看,自己待慣了的池塘原來只是幾個池塘中的一個,並不是唯一的一個。那裡的生活到底是怎麼回事?出了池塘反而看得更清楚。這本書裡的故事都是站在池塘外面寫出來。中國古話叫:知己知彼。沒有東年老師叫我做的,細緻的「知彼」工作,我寫不出好的「知己」小說。
我的二○○三年得獎中篇〈忠臣逆子〉開了一個頭。下面的幾個故事都是從這裡開始,以東西文化比較的手法寫下去的。〈忠臣逆子〉從一個家族——戴家——的變遷史,看中國百年一次次革命的近代史。從曾爺爺的辛亥革命,到戴家大小姐走出國門,後一代人革前一代人的命,都以為自己走的是條新路,卻不知道那「革命」本身就不是什麼好果子。用暴力奪來的權力,只能用暴力來維持。把悲劇用喜劇的語言講出來,是戴家大小姐對家族史作的反思。
人當然有純人性,但把一個家族放到中國歷史中去了,寫作就自然從「純人性」轉成了寫「中國人性」。人,可以是社會人,社會人依然是人,這是我想寫的人性。從這個中篇開始,故事的枝椏就向各個方向長出來。戴家人在中國的歷史中活著,走到哪也擺不脫一條長長的影子,這個影子叫「中國文化」。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故事,中國的現代,都是這個文化的海洋裡翻起的波瀾。若在寫「人性」的小說裡,不能畫出幾張文化臉,其實,就根本沒有什麼好寫的。文化不是抹在臉上的粉子,是人性下面的東西。講吃喝是人性,可講到劃拳和行酒令就是文化了;講上床是人性,可講到在喊床的時候叫「挨千刀的」就是文化了;講愛情是人性,可講到「東邊日出西邊雨」就是文化了。
這樣的文化如此深厚,即便中國人走進了現代化,也還在這個文化裡折騰。於是,就有了〈羅坎村〉。故事從「歷史人」轉到了「當代人」。當代的生活,反迫使戴家大小姐研究起兒時生活過的羅坎村。羅坎村是一個很小的村子,也是一個大社會。這樣的村子很普通,隨便一指,前方那個就是。羅坎村的根牢牢地長在中國的土地上。走進羅坎,一定能看到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人性」的問題是一個「家文化」的問題。中國歷來有災有難,卻依然成了一個人丁興旺的國家,對家庭關係的規範和熱愛,是流在羅坎人血液裡的道德密碼。而這密碼裡的每一個符號都是從土地裡長出來的。我們是農民,在山多地少的村落裡住了三千年。我們有我們的價值觀,親緣關係是我們的社會秩序。我們認命,認官,認親朋好友。正義不正義不是我們關心的,我們關心人系關係。是非對錯,靠包青天裁決,「公眾利益」靠父母官代表……。突然間,在短短的三十年裡,中國人不想當農民了。有了高速公路,有了物貿中心,有了市場,出了國,選擇了工業化,成了自由勞動力。可是在這些新地方,我們還是只會靠人際關係來維持社會秩序,結果,這就像咱們爺爺輩腦袋後面拖得那條封建主義小辮子,又難看,又可笑,又氣人,還滋生腐敗。這就是我挖掘出的現代中國人的人性。中國人走到哪也沒走出羅坎這個圈子。(〈羅坎村〉在大陸獲「二○○八北京文學排行榜」;「二○○九茅臺杯《人民文學》獎」;「二○一○茅臺杯《小說選刊》獎」)
每一種文化其實都是有一些陋習的,只不過文化這種東西像空氣,像水,在一個文化框架裡生活時間長了,有些陋習就成了習慣,雖然我們並不喜歡,可也就這麼做了。但是,如果有另一種文化作鏡子,也許就可以看清楚我們陋習的可笑。這樣就有了〈九九歸原〉。放蕩不羈的戴家大小姐,到了美國,在一個談「形而上」的中國精英人士的圈子裡,拿起西方文化不同的價值觀念作鏡子,肆意調侃我們的民族劣根性。圈子裡一群從中國文化裡走出來的男男女女,都是聰明人,他們出了國,在很短的時間裡和西方社會接軌。他們的初衷是想要摘西方文明樹上結出的好果子:民主、自由、愛情。可在他們的小圈子裡,好果子剛拿到嘴邊就變了味。那不是因為他們不愛這些果子,而是因為他們腳下那塊有幾千年深的農耕文化土壤,沒有讓這些果子健康成長的地方。在很短的時間裡學會穿西裝,喝香檳酒不難,但文明遠不止這些。文明起碼要有一套健康的價值觀。戴家大小姐說:我們是一群農民,懦弱、荒唐、小心眼。我們急急忙忙向現代化趕去,要把自己西化了。可是,我們就算開進了美國,折騰來折騰去,到臨了依然還是只會按著農民社會的價值觀行事。我們的文化基因上帶著病。(〈九九歸原〉登上「二○○六年北京文學排行榜」。)
這病在哪兒呢?從五四開始,中國人就想要「德先生」進門。但是民主是有代價的。戴家大小姐在海外生活,像嫁出去的女兒,看見西方的好東西,就想往娘家搬。西方的民主好,西方的民主教育好,這個大蘋果該摘了送回去。可搬回去能不能用,用起來會有哪些衝突?先看一個試驗。〈老康的哲學〉寫了戴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和西式教育下長在的兒子戴小觀的衝突。老康正合中國男人的模式:滿身活氣,卻不求真理只認等級;熱情洋溢,卻不願守法律,喜歡變化無常;雖留洋在外,卻時刻不忘吃五花肉。形像不是阿Q,卻有一些叫「阿Q」的祖輩。撒謊,好新,傳統,沒有野心,嚮往好日子。老康是個普通人,性情中人。普天下這樣的「老康」多多多。傳統的中國人老康,兀突站在另一片沒有中國文化的土地上,孤軍奮戰。身上無處不散發著中國特色。這時候,這個中國人就不再是一個「老康」了,而成了一系列我們不自覺地固守著的中國傳統價值觀,成了「中國哲學」,體現著中國哲學。中國哲學中許多信條和西方的民主有根本衝突。民主,在五四之後,以「德先生」的名字到過中國。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但民主的生活方式怎樣?為什麼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卻沒有自己生出個「德先生」來?從外面請一個來,是借來的,是客人。我們中國人好客,但光好客還不行。借來的機制是衣服,不是實質。借來的機制只能以「借來的機制」發揮作用。如果實質不變,玩民主也會選出土匪頭子來。選舉制是民主的衣服,是民主的操作方法。還不是民主本身。老農民都會用豆子計票,選舉出村長、保甲長來呢。選出來還不是照樣橫行一方,太上皇一樣。民主的日子到底怎樣過,我們不知道。﹁德先生」進了中國,在中國也坐不住。我們的文化裡沒有他的位置。和「德先生」衝突的是我們幾千年的等級制。(〈老康的哲學〉由《小說選刊》二○一○年一月刊重點推薦,並組織專家討論。二○一○年郁達夫小說獎入選待定)
不是我們不想好,是我們一代一代的目標沒有一個正中靶心。路走了一圈,「明天有多遠」?陰錯陽差,戴家大小姐的兒子,在美國長大,倒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他一改戴家大小姐對自家革命史的否定態度,饒有興趣地和母親一起追溯歷史,又走進現代中國。兒子,用美國式的寬容,理解上輩人。母親卻繼續批評前輩的革命。並且,在二十年後,中國經濟發達了,深諳中國人性的戴家大小姐又把對社會的批判轉向了自己這一代「實業派」。現代中國是這代人努力的結果。可是,奇怪得很,前人有的毛病後人又接著犯。前人費盡力氣要掃蕩的東西,風一吹,全回來了。思維模式不變,等級制不變,家族關係不變,官場遊戲不變,換所有制、建高樓大廈,都不管用。說一句不中聽的大實話:「中國反封建的道路還沒走完」。中國與世界先進價值的差距在:還沒有活出「人」來。不是生物意義上的「人」,是「理性的人」,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明天有多遠〉首次發表)
戴家的故事是一個家族的故事,從祖爺爺講到祖孫子。戴家的故事也是一個民族的故事。一個古老的民族,不惜代價尋找出路的故事。對也好,錯也好,重要的是他們在尋找。
最後,我衷心感謝《聯合文學》將這五個中篇系列結輯出版。它們既是一個系列,又是五個獨立的故事。如果讀者喜歡,那就是我對「二○○三年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臺灣的文學前輩和臺灣讀者的彙報和致謝。
二○一○年五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