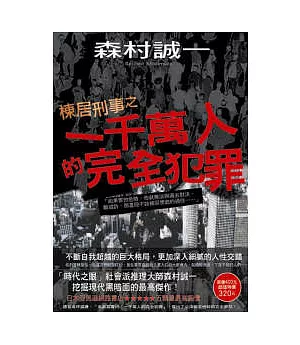閱讀森村誠一
以「時代的眼睛、社會的良心」自勉的傲骨作家——森村誠一
心戒
一九八一年五月,趕忙著在截稿日前伏案振筆的森村誠一,被突如其來的電話鈴響打斷了思緒。當時的他,正於《赤旗》週日版上連載最新的小說《死的器》--由於任職六本木高級軍政VIP接待所的青梅竹馬麻利突然人間蒸發,新聞記者平野與負責尋人的私探片山只得依憑手中僅有的資料,循線追查,怎知事件竟若滾雪球般地越滾越大,兩人即將挖掘與面對的,竟是首相、美國上將夥同國際武器販子聯手開發軍用核子武器的驚人內幕。五年前,森村誠一發表《人間的証明》後大受歡迎,一舉躍上暢銷作家與頂尖推理小說家之林。原欲以兵器產業和政治金融界掛勾黑暗面為題材的《死的器》,現在卻有讀者打電話來,帶著濃厚的關西腔,提醒森村誠一:作品情節與真實狀況出入太大,不真實!
當時的森村誠一怎麼樣也料想不到,這通夜半時分的電話,將讓他的寫作生涯,攀上另一座高峰,卻也將為他、為他的家人、為他身邊的親朋好友,甚至是工作上的伙伴們,帶來生命上的威脅。
困頓生活中的社會觀察
一九三三年生於日本埼玉縣熊谷市的森村誠一,出身商賈之家,從初中到大學,森村誠一的求學之路頗為順遂。然而,一九五八年從東京青山學院英美文學系畢業後,因為景氣的關係,森村誠一面臨謀職上的困境,加上考試失利,迫於生活的他只得放棄再次挑戰與志趣相符的日本交通公社,轉往飯店業發展。一九五八年四月,森村在新大阪飯店當起櫃檯招待,負責與客人應對進退,協助旅客填寫登記簿後,露出專業的微笑並遞上鑰匙。
這般枯燥單調的生活,顯然與森村誠一熱愛登山的性格不符。即便不久後他與飯店高層之女結婚,更進一步轉往新大谷飯店升任「櫃檯主任」,但一成不變的工作性質與飯店封閉的環境,不僅讓森村誠一深覺「自身性格完全被消磨殆盡」,更促使他於日後發表《鐵筋的畜舍》,透過推理小說的形式,將日本企業形容成關著牲畜的鋼筋建築,一抒任職飯店業八年的苦痛回憶。之後,森村離開飯店業,轉職經營學校後出任講師。
一九六八年,彼時的森村誠一已分別於日本文藝社、青樹社等出版社發表過隨筆與小說。雖然青樹社當時的主編那須英三頗欣賞森村誠一以上班族進入競爭激烈的職場後,面對強調「犧牲」、「奉獻」的日式管理制度,遭逢挫折、出賣靈魂為題的「企業職場小說」,一連出版了《大都會》(《無情都市》)、《分水嶺》等五本長篇小說,但沒沒無名的新人透過小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在毫無宣傳的情況下,終落得湮沒浩瀚書市的命運。
對寫作生涯幾乎不抱希望的森村誠一,百無聊賴之際,偶然於書局翻閱《小說現代》雜誌,映入眼簾的,是僅剩一個月便截止的「第十五屆江戶川亂步賞」徵文活動辦法。當時由松本清張帶起的社會派推理小說風潮席捲書市,加上青樹社主編那須英三的建議,森村誠一決心改以推理小說背水一戰,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閉關思索,終日奮筆,終於趕在截稿日當天,懷著忐忑的心情將參賽稿件寄出。半年後,《高層的死角》(《高層的死角》)在橫溝正史、高木彬光等評審皆以「新鮮」盛讚的情況下,奪得當屆首獎。
有趣的是,讓森村誠一感到索然無味的飯店櫃檯工作,不僅是促迫他提筆寫作的動機與關鍵,更多次成為他作品中最獨樹一幟的鮮明特徵(另一個則是他所喜愛的登山活動)。在早期的企業職場小說《銀的虛城》中,森村誠一便以商業間諜成功臥底並製造食物中毒事件為開端,反過來寫盡職場上「狡兔死,走狗烹」的利己主義陰暗面;而在一戰成名的得獎作《高層的死角》裡,森村更以觀光飯店為舞台,精心設計一道結合雙重密室及不在場證明的「凶手是誰?(Who
Dunnit?)」謎團。雖然後半段破解不在場證明的過程失之冗長,但即便以現代標準重新審視《高層的死角》,前半段破解密室之謎的心理性詭計,歷經四十年的歲月考驗,依舊簡潔亮眼。
挑戰道德與生存的人性證明
獲得江戶川亂步賞後,三十六歲的森村誠一正式以推理作家的身分出道。這時期的作品,無論是以新幹線時刻表詭計為核心的《新幹線殺人事件》(《新幹線謀殺案》),抑或是發生在東京機場飯店三樓的雙重密室謀殺案《東京空港殺人事件》(《東京機場謀殺案》,表面上看來都是典型以詭計為主的本格解謎作品,然而,森村誠一在議題取捨上,已然透露出他日後藉由小說關照社會問題的傾向。《新幹線殺人事件》中,森村誠一以一九七○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開幕表演為題材,揭露演藝界金絮其外,敗絮其中的醜陋與虛空;而在《東京空港殺人事件》內,森村誠一則透過兩次空難事件,不止寫盡宛若影集《Lost》(《Lost檔案》)第一季為觀眾帶來的道德與生存間精彩的兩難拉扯,更藉由揭露空難原因背後的重重黑幕,以一百八十條人命為媒介,深入探討企業組織和個人為爭取利益不惜一切的明爭暗鬥。
這樣的嘗試,在寫作模式上與早期的松本清張非常接近,皆從重視謎團的本格推理形式出發,而後將目光坐落於作家所關注的社會現象與盲點之上。一九七三年,日本推理作家協會將第二十六回「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的榮耀,頒給了森村誠一的《腐食的構造》與夏樹靜子的《蒸發》,正式宣告這類以本格解謎性質為骨,包覆著社會寫實與弱勢關懷血肉的寫作方向,即將引爆風潮。
受到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的鼓勵,當角川書店社長角川春樹邀請森村誠一為創刊不久的《野性時代》執筆連載時,苦思多日的森村誠一,終於決心以深埋心中二十年的印記,透過推理小說,書寫對於母親的溫柔回憶與懷念,並藉此回應角川春樹邀稿時那句言簡情深的「請寫出彷若作家資格證明書般的自信之作」期許。
於是,一名原籍紐約哈林區的黑人少年,胸口著刀後,竟從車程至少半小時之遠的命案現場,拖著身子前往日本皇家大飯店,而後於通往頂樓摩天餐廳的電梯中,失血過多而亡。藉由離奇的異鄉人之死,森村誠一在《人間的証明》中,串起紐約與東京兩座城市間橫跨時空的關聯,透過三段關於親情、良心的追查,森村誠一藉燃燒著復仇火焰的刑警棟居弘一良,在戳破美好家庭幻象的同時,亦帶來人性本善的根本證明。
森村誠一經常在作品中採用多線交錯並行的寫作模式,讓原本看似無關的案件、不相干的角色,在錯綜複雜的事件中交織混紡,而後一條線、一條線地逐步收攏,讓讀者得以釐清其面貌與位置,最後收束出關於人性、宿命,關於社會、公理與正義的醍醐味。
一九七七年,角川春樹請來當時極受歡迎的演員松田優作擔任森村誠一筆下最為著名的棟居刑事角色,挾帶著電影超高人氣,熱銷的《人間的証明》宛若平地一聲雷地將森村誠一推而上暢銷作家之林。創下至今暢銷七百七十萬冊、三十年內四度改編日劇之紀錄,並讓橫溝正史以「雄偉的交響樂」形容的《人間的証明》,成了森村誠一寫作生涯的代表作。同年,森村接續以《青春的証明》和《野性的証明》構築而成的「證明三部曲」,接連兩年位居年度作家收入榜首。多年後,無論是穿梭於山脈與政界之脊,透過兩則墜落死亡的案件,在染黑的官僚制度內描繪孤獨純白人的《純白的証明》,抑或是在《棟居刑事的一千万人的完全犯罪》中,藉由兩名離奇失蹤的女子,揭露一千萬人共同犯罪的絕對之惡,經由棟居刑事一角,森村誠一不斷地帶領讀者探尋、追問為人的條件,並在荒蕪淒冷的社會中,試圖肯定人性本善的可能及其尊貴。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七○年代後期可說是森村誠一的時代。即便當時新人輩出,但森村誠一憑藉著縝密嚴謹的推理布局、饒富懸宕的氣氛,輔以他對世俗人情的洞察,以及社會議題的選擇,讓他成了最具實力挑戰松本清張社會派宗師地位的作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正是那通帶著關西口音的讀者來電,令森村誠一的生活,起了極大的變化。當時來電的神祕男子,清楚指出森村誠一於《赤旗》週日版上連載的小說《死的器》,其中關於日本陸軍傳說中「細菌作戰部隊」的描繪,與事實的各處偏差。這通電話令森村大為驚訝,幾次通話後,對方終於答應現身見面。不久,森村誠一在記者友人下里正樹的協助下,一同採訪、蒐證、集照。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森村誠一在光文社出版了震驚日本的報導文學《惡魔的飽食》(《惡魔的飽食--第七三一部隊》),大膽揭露日本於一九三六年在大陸東北建立的第十七號軍事基地(簡稱「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暗中以中國戰俘進行活體研究、實驗病毒與生性武器,泯滅人性的細節與事實。四個月內旋即以破百萬的銷售站上排行榜之首,隔年四月出版的續作《□.惡魔的飽食》亦同時擠上銷售排行榜前十名,一時間舉國譁然。
正當森村誠一與下里正樹於新大谷飯店接受世界各國媒體的訪問同時,《惡魔的飽食》正、續兩作竟傳出「偽照」疑雲,導致出版這兩本作品的光文社將書全面下架銷毀!經調查後發現,當時森村誠一誤將一張施打預防針的照片判讀為七三一部隊以中國戰俘為生化實驗對象進行病毒施打的紀錄照片。這讓當時原本居於劣勢、噤聲中的右翼份子爭相鼓譟,不僅緊咬著當初刊載森村作品的《赤旗》其身為共產黨機關報的事實不放,投石、潑漆、鎮日威脅生命的電話更是鈴響不斷,就連當時森村誠一想出門買東西,神奈川縣警局都得加派員警保護,並呼籲森村穿上防彈衣以防萬一。
面對如此棘手的狀況,森村誠一選擇正面而且誠實地面對問題。他在記者會上公開表示道歉,並釐清他與共產黨間毫無關聯的清白立場,更將續作《□.惡魔的飽食》版稅全數捐出。然而,森村誠一也明確表示,他承認誤用照片,並不表示關東七三一部隊曾犯下的罪衍亦可一併抹除。他更進一步提醒讀者與媒體,試圖批評的人,應當針對歷史事實表明立場,而非藉由攻擊作者來轉移話題。
當時,森村誠一身邊的親友為顧及森村的安危,紛紛建議他不須以社運人士自居。槍打出頭鳥,為何不回頭乖乖寫可以賣錢的推理小說呢?然而,面對右翼人士的攻訐與威脅,斷然回絕的森村誠一卻選擇正面無懼地接受挑戰。他在接受訪問時便曾答覆記者:「如果我就此怯懦,往後將有何面目以作家自居?不敢發行這類作品的出版社,將被譏為營利至上的懦弱出版社;同理,我也將被比作為只知稿費與版稅的作家,而那是我最無法容忍的事!」
一九八二年,一邊修訂《惡魔的飽食》正、續兩作錯誤的森村誠一,選擇以作家的武器迎戰。他將報導中駭人的事實,透過推理小說的形式呈現,讓更多讀者有機會了解事情的始末。分成上下兩冊的《新.人間的証明》以中國女翻譯員楊君里遠渡重洋至日本尋找親生女兒,卻突然在計程車上痛苦痙攣後猝死開場。再次面對異鄉離人,棟居刑事在波詭雲譎的抽絲剝繭中,為求真相不惜走遍全日本,更飛往美國探查實情的熱血精神,引領《新.人間的証明》再次攻佔銷售排行榜。而負責出版的角川書局,不僅再版修訂《惡魔的飽食》正、續兩部作品,更推出《惡魔的飽食第3部》。一九八四年,森村誠一將關東七三一部隊進行生化實驗的公案,再次從日本憲法的角度切入,而後輯成《日本國憲法的証明》出版。
森村誠一曾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談及當年這段引起國際媒體爭相注目的往事。多年後,森村僅輕描淡寫地以「只有這作品放不下」帶過,看似書不盡言,卻蘊含了他從櫃檯接待時代對於世俗人情與公理正義的澄澈觀察。
或許對森村誠一而言,寫作是一種身處道德與現實劇烈衝突的過程中,不願保持沉默的人性拉扯。而他發自內心、盈滿勇氣的創作,都源於己身對國家熱烈與深情的關懷,堅信,唯有透過魂魄發出正義的判詞,才得以消弭補綴傷痛,而後攜手向前。
二○○四年,森村誠一迎接四十週年的作家紀念,並獲得第七屆推理文學大賞(相當於歐美推理獎項中的大師獎和終身成就獎)。近年他對於寫真俳句的推廣不遺餘力,卻仍不忘時時呼喚棟居刑事,揭露社會不義。
也許,對森村誠一來說,很多事既然看見了,就不能背過身去。唯有透過寫作,才是他一路走來,關於作家的證明吧。
(撰文者為知名推理評論者、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
推薦序
洞悉社會真實、揭發時代之惡的銳利筆觸
余小芳
森村誠一出生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為埼玉縣熊谷市人。高中時,向朋友借閱約翰.狄克森.卡爾(John Dickson
Carr)的密室推理小說而著迷於此類型文學,之後大量涉獵國內外的推理作品。一九五八年自青山學院英美文學科畢業,先後任職於新大阪飯店及新大谷飯店,這段為期九年的飯店業工作經歷,對其後來寫作甚有影響;一九六七年轉換工作,前往日本經營學校擔任講師,同時從事長篇企業小說的創作。
企業小說是六○年代於日本興起的新形式小說創作,初始十年,投入此文類的撰寫作家不多,內容尚且處於嘗試階段。森村誠一正好在此時踏入文壇,於一九六七年撰寫《大都會》,之後接連書寫《銀的虛城》、《虛無的路標》等五本企業小說,皆由青樹出版社負責出版業務。然而森村誠一是個未曾得過任何文學獎的沒沒無名作家,加上出版社的規模難以為其大肆宣傳而鮮少為人知曉,最終消失於茫茫的書市內。反倒是森村誠一日後成名,才回頭來改寫、潤飾這些作品,投入更豐富的元素和寫作技巧,讓它們得以重新出版面世。
當時推理小說大行其道,容易暢銷,青樹出版社的負責人認為森村誠一的企業小說具備推理小說的氣氛,力勸其改為創作推理小說。某日,在書局翻閱《小說現代》月刊,偶然撞見離截稿日僅剩下一個月的江戶川亂步獎徵文廣告,他因此拋開手邊的一切事情,將全部心神投注於小說創作。花費三天時間構思故事和設計謎團,並實際走訪警視廳和新大谷飯店。於第四天開始依照原定計畫寫作,每日寫到手痛到無法提筆才肯罷休;截稿當天於郵局郵寄時,甚至不自覺地對著放有稿件的包裹合掌祈禱。
一九六九年,由於《高層的死角》獲得第十五屆江戶川亂步獎而使得森村誠一正式進軍推理文壇,日後並成為重視寫實刻劃的社會派中堅作家,然而他的作品內涵及本質又與社會派開山始祖松本清張的小說核心有所差異。
松本清張於五○年代末期至六○年代初期致力於文學書寫,接連推出《點與線》、《眼之壁》、《砂之器》等赫赫有名的作品,以橫掃文壇之姿,促成風潮達二十年之久。他的作品富有文學性,奠基於日本的社會基礎,描寫真實罪行的源頭與解剖人性深處隱藏的犯罪動機,並透過平日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情為主體,用以取代異常的犯罪行為,減卻強調高度詭計的設計,並突破以往重視邏輯解謎的本格派,以及描繪變態心理、充滿幻想妖異風格的變格派,從中開闢新的推理小說寫作路線,並引發讀者的高度重視及支持。
松本清張引領的社會派推理小說一時蔚為主流,成為出版界的新寵兒。當中,森村誠一及夏樹靜子亦以黑馬的姿態崛起於文壇,觀察他們的作品,其內容奉行寫實主義,脫胎自現實生活,與時代的脈動有著緊密的結合,於此之外,也納入引發人興趣的謎團和反覆推敲、驗證的解謎過程,使得作品獨具匠心與特色,兼具現實根基及圈套詭計的雙重性格。
在森村誠一的作品之中,有以新宿西署牛尾刑事為系列主角的《終點站》等書,亦有以棟居弘一良為主的探案系列作品,而以後者為名的《棟居刑事之……》作品更是多不勝數。
七○年代,即便推理小說界的新人作家輩出,森村誠一在當中依然毫不遜色。一九七二年以《腐蝕的構造》一書和夏樹靜子的《蒸發》(又譯《失蹤》)共同榮獲第二十六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日後亦推出膾炙人口的證明三部曲,分別為《人性的證明》、《野性的證明》、《青春的證明》等,之中又以《人性的證明》獲得最多的迴響,並多次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搬上大螢幕。
著名的棟居刑事即是在《人性的證明》裡登場。
在小說的設定中,他是個三十歲的青年。幼年時期,由於母親另結新歡而拋下他與父親,因此他對於母親的長相毫無記憶;陪伴著他長大的父親出身於教育世家,是名小學教師,對於妻子的舉動未曾有過任何埋怨,只是默默忍受妻子離去的寂寞,將關懷全數投向兒子,過著冷清的單親日子。
棟居對於童年的印象,所有的記憶都是寂寞的,不論是昏黃的燈光、散發著冷冽氣息的空間,和父親對坐著吃飯時的靜默,簡直到了刻骨銘心的地步,究竟是物資貧乏造成的苦,還是失去母親的孤獨導致,棟居自己也無法確定。日後寂寞的印象不斷擴大,漸次地從對於母親的思慕之情發展成憎恨,然而對於父親的感情,他是珍視且欣喜的,只是這個和自身相依為命的父親,在一場意外中喪命。
唯一的保護傘,在四歲時的寒冷冬季,被無情地抽離。
當時的街道上滿滿是流浪漢及無家可歸的孩子,棟居在傍晚的寒冷車站蜷縮著身子等待父親的歸來,那天父親遲了半小時,通過剪票口之後,所給予的紙袋,裡頭溫熱的豆沙饅頭溫暖了棟居的小手,然而正當兩人朝向歸途方向行走,卻發生了足以影響棟居人生觀的那件事。
幾名喝醉酒的美國大兵正在侵犯一名年輕女子,該名女子不停呼救,然而其他人卻只是站著圍觀,而挺身而出的父親則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圍毆。不管棟居如何哀求,無意離開現場的眾人無人出手制止,待警察出場也已太遲;事發後三天,父親因為腦出血而黯然辭世。
成為孤兒的棟居為了向全人類復仇,毅然決然當上刑警。也因此,他不相信人類,憎恨著所有人,深深相信所有的人類都是醜陋不堪的,不過有趣且悲嘆的是,在《人性的證明》內,棟居卻是以人性為最後賭注來與兇手進行正面對決。
《棟居刑事的復□》在橫渡刑警過世之後,讓原本擁有火爆性格的棟居刑事開始收斂自己的脾氣。失去摯愛妻子的棟居,於《棟居刑事的情熱》與二十來歲的本宮桐子相遇;在《棟居刑事之花的狩獵人》和戀人桐子熱切地討論案情,棟居當時相信能夠探查到事件的真相,乃是由於犯罪者內心尚且保有人性的緣故,無奈爾後桐子也撒手人寰;至《純白的證明》,棟居的待人處事逐漸圓滑的背後,其實背負著沉重的情緒及惘然,「棟居也曾有過夢想。在那個夢想裡,山佔據了大部分的位置。但在失去了疼愛的人以後,他同時也失去夢想了。就好像可以互相分享夢想的對象消失了,夢想本身也消失了一樣。在那之後只充滿憂愁。而憂愁是沒有色彩的」。
即便《棟居刑事之一千萬人的完全犯罪》的書名是以棟居刑事為系列主角的作品,然而他出場的次數卻相當零散且稀少。本書首先描寫兩名年輕女子的自發性失蹤,她們在東京的街頭上分別與男子邂逅的情節,致使書籍初始散發著愛情因子及懸疑元素相互雜揉的風味。
在推理小說的作品中,有一些前有所本且具有英美語系原文的專有名詞,其中之一為「失蹤人口」(Missing
Persons);顧名思義,其意指為失蹤的人。然而在推理小說中,我們也許偶爾會發現有個人失蹤了一段時間,但有時失蹤者並不一定是人,也可能是其他的物品或是房子之類的物質;無論是失蹤的人或物,皆造就了令讀者疑惑且好奇的謎團。在設定上,人之所以消失,背後原因通常與犯罪脫離不了關係,可能和謀殺、綁架有所牽連,有時也與黑函有相關。
在推理文學書寫的進程裡,Missing Persons最早的源頭來自於愛倫.坡(Edgar Allen Poe)的〈瑪莉.羅傑之謎〉(The Mystery of Marie Roget),夏樹靜子的《蒸發》亦探討人口失蹤的問題,此後尚有艾德.麥可班恩(Ed McBain)八十七分局探案系列的《So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再見寶貝,再見》(Gone, Baby Gone)等書,這些都是運用失蹤的題材,透過變化轉型而來的小說。
莫里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曾撰寫《奇怪的屋子》(La demeure mysterieuse)、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於中篇作品〈上帝之燈〉(The Lamp of God),描寫晚宴過後的隔天,窗外可見的神秘黑屋離奇失蹤,徒留一片雪白的大地;而愛德蒙.克里斯賓(Edmund Crispin)的《玩具店不見了》(The Moving
Toyshop),內容描述深夜之中的玩具店發生一起謀殺案,隔天卻變成一家雜貨店,幾天過後,玩具店竟然現身於另外一個地點。
有時真實社會發生的失蹤案件亦被拿來改編為推理小說,比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間,曾經有兩台載著黃金飛越南大西洋的飛機前後消失無影。該事件後來被Karen Campbell改寫成《Suddenly in the Air》,此書也成為這類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本書內,警視廳搜查一課的棟居在意的是,東京都內、鄰近市鎮及近鄰縣市的失蹤者協尋申請不斷增加,而被提出協尋申請的失蹤者裡面,有自殺疑慮的特異失蹤人口上升;不少失蹤人口經由網際網路的自殺網站相識,進一步離家出走。這些人之中,有以集團方式自殺或相約同時自殺,造成社會新型態問題。行蹤不明的自殺願望者及特異失蹤人口,背後是否牽扯令人難以預估的風險和犯罪事件呢?
由此可見,Missing Persons確實是個歷久不衰的小說元素。
《棟居刑事之一千萬人的完全犯罪》所透視的社會問題,除了失蹤人口以外,還有協助自殺者重生的「更生工作者」議題。基本上,本書是個環繞著二男二女所延伸出去的故事,這幾個人之間有錯綜複雜的前後人際關係,並且因為目睹了一樁交通事故,以及後來發生的秩父殺人棄屍案而衍生更大的連結性。
森村誠一向來不以華麗的詞藻為著稱,在他的推理小說中,雖然有時會出現如《高層的死角》或《搜查線上的詠嘆調》這類以高度解謎性質為依歸的作品,然而總體說來,卻少有複雜難解、異想天開的詭計出現。他憑著深厚、矯健的書寫筆力,製造出大謎團下的眾多小謎團,再透過多線收攏的方式,緩緩道出每個人物之間的人際糾葛和激盪,以及因為「失落的環節」或「偶然的發想」而得以讓這些人物、事件持續交流、互動,並進一步地揭露出關注的重要核心社會議題。
原本森村誠一即滿擅長於敘述企業及政治界的勢力鬥爭及消長問題,而處於大團體之中的小人物,有如鑲嵌於上的小小齒輪,既無法遠離團體的束縛而自行運作,亦無法由下而上地改變組織內部的巨大結構。在本書當中,雖然不以商場競爭及政治黑暗為描寫對象,然而相似條件重構於更生組織及暴力集團之內,依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失去一切記憶的更生工作者兵藤英之,對於組織下達的指令開始感到疑惑且不安,然而這正也是毀損自己和組織的危機引爆點。
「人」,永遠是書寫上的重大主題,這也是為什麼一代一代的作家總是能透過不同的人物組合及事件搭配,創造出一本本永難忘懷的經典佳作。充滿傲骨精神的森村誠一,數十年來創作不輟,即便引領風騷的社會派時代已然褪去,然而他獨樹一格的風範仍然在眾多著作中大放異彩。森村誠一擁有洞悉社會真實、揭發時代之惡的銳利筆觸,雖然過程內難免碰觸黑暗、不光彩的犯罪情事,但是在事件背後,我們仍舊能察覺人的內心深處依然存在著光明及人性的可能,而這剛好是引發讀者共鳴與激賞的溫暖傳遞,亦是作者撰寫上的原始初衷。
(撰文者為暨南大學推理同好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