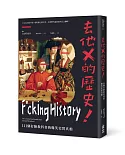作者序
個人色彩的序言
本書是對現代主義---其興起、勝利及衰落---的一個研究。讀者很快會發現,這書是一個歷史家的作品,因為除非是有必要或覺得有用,我的敘述都是按年代順序進行,章與章是這樣,同一章之內也是這樣。這也是一本歷史家的書,因為我並未自囿於小說、雕塑與建築的形式分析範疇內,而是把現代主義者的作品放回它們所座落的世界去理解。
但這書不是一部現代主義全史,因為有關的材料是那麼汗牛充棟,要用一本書去涵蓋現代主義的歷史是難以想像的,若勉強為之,只會流於浮光掠影。為什麼現代主義小說家之中我沒談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和貝婁(Saul Bellow)呢?為什麼現代主義詩人之中我沒談葉慈(William Bulter Yeats)和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呢?為什麼現代主義畫家之中我沒談培根(Francis Bacon)和德庫寧(Williem de Kooning)呢?又為什麼我談馬蒂斯(Henri Matisse)會談那麼少,而且只談到他的雕塑家身分?我略過科普蘭(Aaron Copland)和普朗克(Francis Poulenc)等作曲家不談,或略過諾伊特拉(Richard
Neutra)和沙里寧(Eliel Saarinen)等建築家不談是合理的嗎?難道我只談了區區四個導演,就可以涵蓋石破天驚的現代主義電影了嗎?我為什麼沒談歌劇和攝影這兩個領域?如果我要寫的是一部現代主義全史,那上述的人物和領域當然都是不能不談的。但誠如我在序章「現代主義的氣候」指出的,我要尋找的是現代主義者的共通處,以及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讓他們繁榮或蕭條。
因此,在談到任何畫家、劇作家、建築家、小說家、作曲家和雕塑家時,我都只是要以他們為例子,來說明哪些元素是現代主義不可缺少的。雖然有選擇性,但我力求讓我的選擇加起來足以定義現代主義,足以體現它的範圍、侷限性和它最典型的表述。我得強調,在挑選人選時,我沒有讓我的政治觀點充當嚮導,起碼是沒有自覺地這樣做。別的不說,我至少詳細談論了一些我不喜歡的現代主義要角,如法西斯主義者哈姆生(Kunt
Hamsun)、高教會派盲信者艾略特(T. S. Eliot)和歇斯底里的反女性主義者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lberg)。我譴責他們的意識形態,但卻不能否認他們是現代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正如我說過的,我的目的不是要將現代主義的所有流派和所有主要人物一網打盡,而是要去探索現代主義者與時代文化的關係,以及嘗試找出是什麼把他們結合為一個單一文化實體。我的座右銘來自美國開國先賢: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
那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又如何?他算不算是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當然,就品味來說,他完全配不上現代主義者的頭銜。就藝術、音樂和文學的鑑賞力來說,他都是個徹底保守的布爾喬亞。他欣賞易卜生(Henrik Ibsen)卻閉口不談史特林堡;小說家之中,他喜愛技巧高明和社會觀察力敏銳卻談不上前衛的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但看來沒讀過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小說(哪怕吳爾芙和丈夫是他作品的英國出版商)。他掛在牆上的畫作顯示他對奧地利的現代派畫家克林姆(Klimt)或席勒(Egon Schiele)興趣缺缺,他家裡的家具則反映維也納現代主義者的實驗性設計得不到他青睞。所以說,他固然反對自己階級的社會態度與文化態度,但反對的理由不在藝術品味方面。
然而,只要看看二十世紀有多不情願接受甚至激烈反對弗洛依德的一些觀點(特別是有關性慾的觀點),那他作為一個不妥協異議者的角色就會迅速變得清晰。如果說弗洛依德有關人類動物(human animal)的許多觀點在今日已經變得不甚稀奇,那乃是社會花了大半個世紀向他靠近的緣故。我們的社會接受了許多精神分析學的語彙,如手足敵意(sibling
rivalry)、防衛性操弄(defensive maneuver)、被動侵略性(passive
aggressive)等,卻拒絕承認這種借用。因此,我們把那些從一九○二年起每星期於弗洛依德在維也納的住家聚會的同道稱為心理學的前衛分子,並不為過(在這個「星期四小組」後來組成「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之後更是如此)。它始終跟傳統的醫學和精神治療為敵,也始終是由單獨一位自信滿滿的開創者所牢牢領導。誠如我們將會看到的,未來主義者馬里內蒂(F. T.
Marinetti)和超現實主義者布魯東(Andre' Breton)在各自領導的運動中都佔據一個與弗洛依德相似的位置。他們是自己族人中的弗洛依德。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論對現代西方文化的影響力迄今未受到充分評估。毫無疑問,這種影響力是巨大的(哪怕大部分是間接的),對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尤其巨大,而他們的品味跟現代主義的起源與推進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影響力表現在父母不再忌諱跟子女談嬰兒的來源,男女同居不再那麼驚世駭俗,同性戀愈來愈被社會接受,還有人們愈來愈認識到人類侵略性的兇殘(遺憾的是這種認識並未足以影響政策)。當然,這並不表示弗洛依德的思考方式已經深入人心:某些圈子排斥他的激烈程度並不亞於一個世紀以前。
不過,我不是這些人的一員。我知道,精神分析學對一些臨床和理論議題的看法(如夢的起因、女性性慾、談話療法相對於使用藥物的效力等)至今仍充滿爭議。但不管這些問題的最後結論為何,都不會讓弗洛依德對人類心靈的看法成為過時。簡單來說,他是把人性看成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受生理和心理的因果法則管轄,被潛意識迂迴地操縱,原慾(libido)與侵略性永遠處於不和諧狀態。精神分析用於促進病人自由聯想的技巧,相當於印象主義者把畫架搬到戶外,或相當於現代主義音樂家放棄傳統的調號。弗洛依德自稱是心靈的科學家,而在他的世界圖像裡(許多現代主義者也是如此),矛盾心理(ambivalence)佔有一個中心位置。這種悲觀視野把衝突看成任何歷史(包括現代主義的歷史在內)的基本元素。
以上也扼要地說明了我在本書裡對人類處境所持的假設。每當我覺得有幫助,便會以最直接的方式引用弗洛依德派的觀點。但即使沒有明說,這種觀點仍居於我對現代主義的解讀的核心。
我沒敢給現代主義來一趟精神分析。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我是弗洛依德的忠實追隨者。當談到藝術天才的創造性根源,他退一步聲稱這不是精神分析學全面解釋得了的。一九二八年,在一篇談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M.
Dostoyevsky)的文章中,弗洛依德更是坦白地說:「在有關詩人小說家(Dichter)的問題上,精神分析學必須縮手。」在本書中,我並不打算超越弗洛依德。但不管讀者對弗洛依德如何評價,都應該感覺得到我秉持著以下一個信念:不管才華有多麼傑出、不管有多堅決要顛覆流行的美學成規,現代主義者仍然是人,所以逃不出精神分析認定人皆有之的各種內心衝突。
彼得.蓋伊
二○○一年六月於紐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