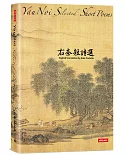前言
創作是林亨泰對生命、對詩最好的註解
-林巾力
這部詩集收錄了林亨泰在一九九五大病之後的作品,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人的存在〉、〈生命之詩〉以及〈《愛彌兒》讀後〉。其中,除了〈人的存在〉直接由中文寫成之外,其於兩部都是日文的創作,由我進行中譯。
林亨泰在超過一甲子的創作生涯中,詩風也隨個人的生命經驗與大時代的思潮變遷而展現出不同的風貌。就大時代的歷史軌跡而言,林亨泰歷經殖民與後殖民、極權而至民主,創作語言亦從日語跨越到華語;就個人的生命經驗來看,則是有早年的失親之痛而至中年以來的病痛折磨。儘管人生有著太多的波折起伏,幸運的是,這些都成為詩人的心志淬鍊,並且融入詩中成為豐富的養分。
這本詩集之所以特別,是因為當中收錄了詩人在大病之後的創作。一九九五年一場嚴重的腦血管栓塞被醫師宣告病危,不僅奪去了詩人最為倚重的語言能力,同時也影響了肢體的行動能力。儘管在不屈的復健後,情況有所好轉,但是歲月到底不會縱放衰老的身體,詩人的視力日漸模糊,握筆的手力不從心,思索的速度再也比不上瞬息萬變的世間。於是,詩人把詩的探索沉澱在生命的關照裡,將人生的思考還原到生命的本真。
〈人的存在〉與〈生命之詩〉呈現出一種走過生死邊界之後的透明,詩作沒有刻意的形式雕琢,也沒有震耳的抗議與吶喊,唯有對生命的真摯紀錄。而〈《愛彌兒》讀後〉則是詩人以自己的方式向思想家盧梭致敬,他將盧梭的「文意」以「詩意」的方式重現,既是為了要對盧梭思想進行正確的解讀,同時也是對詩創作的可能性所展開的另一次探索。
高齡已屆八十五的林亨泰,每日,依舊持續不斷地在創作,這正是他對生命、也是對詩最好的註解。
後記
林亨泰
一、關於「將文意改為詩意」
我不曾正式學過法文,也非盧梭的研究學者。對於盧梭之所以產生興趣,是因為我在日治時期曾經擔任國民學校的教員(大約在1944年左右),並在戰後就讀師範學院(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時,由於立志當一位教育家,便毅然從博物系轉到教育系,而在眾多的教育思想中,盧梭關於「對自然的喜悅」與「兒童的發現」等主張,對我而言有著無比的魅力。對盧梭著作的喜愛,就這麼持續了五、六十年。
自我罹患腦血管栓塞以來,到今年五月正好屆滿十四個年頭。隨著年老侵蝕肉體,衰老的現象日益顯著。每當外出散步的時候,身體僵固不聽使喚,實在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拖著艱難的腳步蹣跚而行。但是閱讀盧梭的樂趣卻使我無法忘懷,專注於閱讀,是我老後,也是我病榻纏綿間聊以慰藉的活動之一。而我在閱讀上所盡的最大的努力,便是對於盧梭的思想內容進行「正確地理解」,也因此,我決定以自身的方式來實踐,於是就有了「將文意改為詩意」的嘗試。盧梭思想內部充滿著強烈的個性與情感的震盪,行文之間令人讀來有著一股如詩般的感動。要將盧梭的文字改成詩,其實並不是那麼困難的。
於是,我從「將文意改為詩意」找到另一種新的閱讀與理解的可能性,盧梭的文章就好比一齣華麗的歌劇,舞台上既有歌手也有管弦樂的伴奏,而我的構想正是企圖將歌劇最基本的元素──也就是像「歌詞」一樣的內容表達出來。當然這僅僅是我的構想,如果成功了,這樣的作品可以是如歌如詩的,但如果失敗了,就當作是一種正確理解盧梭思想的閱讀嘗試,我想我還是很有收穫的。
然而,為何我要選擇盧梭的《愛彌兒》來作為「將文意改為詩意」的嘗試呢?理由就如前述,是與我對於教育思想的關心是有所關聯的。《愛彌兒》這本書的副題是「關於教育」(ou De
l’education),明顯的,盧梭的這本著作原本就是為了教育而寫,而教育是我一直以來所認定的天職。盧梭曾在另一本自傳體的著作《懺悔錄》中提到,《愛彌兒》是一本:「需要二十年的省察與三年寫作時間的書。」盧梭在一七五六年開始著手書寫《愛彌兒》,並且在一七五九年完成了最後的第五卷,只是定稿後並沒有立即出版,而要等到稍後的一七六二年才面世。
盧梭還有一本劃時代巨作《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在同年稍早出版,《社會契約論》與《愛彌兒》在思想上的關係非常密切,同樣都是以探尋人類幸福為目標的著作。《社會契約論》第一章第一篇劈頭就是這樣開始的:「人是生來自由的,卻無處不在枷鎖中。」而《愛彌兒》在書中開頭也是這樣說的:「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裡,就全變壞了。」這些,無疑都是在人類的思想史劇中敲下一記震撼人心的鐘響,前者是「自由」與「枷鎖」的相互對照,後者則是「自然」與「人為」的反差,盧梭運用了一般人所意想不到的觀念與意象的對比,充分展現出他高明的文學造詣。
為了將文意改成詩意,在這兩冊的巨著當中,我選擇了《愛彌兒》作為試驗。盧梭對於教育看法,也就是他在《愛彌兒》的序文中所提到的,是一種「塑人之術」。然而,這「塑人之術」究竟是要透過怎樣的教育而形塑出什麼樣的人呢?對盧梭而言,具體來說,就是「自然人」,也就是「自然的人」與「自然狀態的人」。盧梭關於「自然」概念,與過去以來的自然法思想是非常不同的,如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認為的人類自然狀態是:「萬人對萬人的鬥爭」,是一種適者生存的進化邏輯;另外一位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也強調人類在自然狀態下,是無法保障自身權利與財產的,因此所謂的自然狀態,只是讓人不斷地暴露在受他人侵害的危險之中。霍布斯與洛克雖然都對自然人的狀態有所討論,但他們對於自然人的認識,卻是不脫野蠻與殘忍的意象。然而盧梭的看法卻大不相同,盧梭認為自然與自由是人類的原貌,自然是一種善的狀態,但是後天的人為制度卻成為人類墮落的根源。因而盧梭在《愛彌兒》裡塑造了一種理想的教育,也就是自然人的教育。透過愛彌兒這樣一位虛構的學生,盧梭以小說的筆法闡述他的自然教育理念,便是要去培養一個不受傳統束縛,身心健康並且擁有思想自由的人。
盧梭的「自然」概念除了指向人性自然本真的狀態之外,也包含了大自然的概念,盧梭在《愛彌兒》一書當中讓主角愛彌兒置身於法國美麗的鄉間,讓他接近大自然,並且透過關於大自然的知識與介入其間的勞動,引導孩子從中獲得保衛自己生存的技能,並在回歸自然之中塑造一個沒有受到人為社會的束縛所扭曲、異化的人的狀態。
二、盧梭與我的鄉土教育經驗
盧梭的思想都是與「人」的處境息息相關的,他從各個方面來探討「人」的議題,因此他的影響不僅在教育,同時也在政治、甚至是文學方面都有著他不可磨滅的蹤跡。關於盧梭的影響,我想舉出一個與我個人的成長經驗相關的例子,那就是鄉土教育。鄉土教育曾在戰前席捲日本與台灣的教育界,它可以說是以盧梭的「回歸自然」與「生活陶冶」為理想而發展出來的一種教育。姑且不論鄉土教育後來在日本日益升高的帝國野心下被國家所收編,它在實踐的初始其實是有著自然教育的理念在背後作為支撐的。
我出生於大正十三年(1924)十二月,那時,也就是「大正」時代接近尾聲的時候。大正時代是一個怎樣時代呢?日本兒童文學研究家桑原三郎在《「赤鳥」的時代──大正的兒童文學》一書中的〈兒童與文學──序文〉提到:
大正時代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年代,這個年代不僅誕生了普通選舉,同時,勞工運動亦開始此起彼落。
在閱讀島崎藤村或其他作品時,會覺得大正時期在某個意義上來說,是一個文藝復興的時代,也是一個發現人、發現兒童的時代。
日本大正時期普遍吹起一股自由民主的風潮,人民開始對自身的權益有所覺醒,而許多社會的不平等現象也受到挑戰,因此一般是將這股風潮稱為「大正民主運動」。只是這所謂的大正民主風潮不僅席捲日本,當時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韓國等地也都在大正民主風潮的影響下,以各種不同的面貌衝擊著殖民地社會,如勞工運動的興起與爭取自治的「民族自覺」等構想,無疑都是這股風潮的內容之一。
而大正民主風潮也深入了教育思想的領域,並吹起了大正的新教育運動。當時新教育運動主要著眼於打破明治以來舊式教育的權威主義、形式主義、填鴨式等等由國家所主導的教育,而引入歐美的自由教育、個性教育與「生活教育」等概念,進而「由教師中心轉變為以兒童為中心」、「從拘束轉為自由」、「由教學∕教授轉為學習」、「由他律而為自律」等等批判式的教育思想型態。
現在回想起來,從我出生以來直到接受「公學校」基礎教育的這段期間,其實正是在前述的大正民主風潮的遺緒中成長。我在昭和六年(1931)四月因為搬家的關係而不得不暫時在埤頭庄的小埔心公學校一年級就讀,第二學期之後才轉到故鄉北斗街的北斗公學校。當時的北斗公學校在第十四任校長荒謙助先生的指導下,整個學校呈現著一股盎然的生氣與活力。日本雖然從昭和二年(1927)開始便在全國的師院附小裡實驗性地設置「鄉土科」,而文部省也於昭和七年(1932年)廣設「鄉土教育講習會」。但是前述的這位荒校長則搶先一步,在昭和六年,也就是我轉學的那一年引領全校師生進行「鄉土調查」,這是一個認識自身鄉土的活動,其成果便是一部長達三百六十六頁的鄉土報告書。
說起一般的教育易流於抽象的空論,與具體的現實世界分疏,也往往不根基於事實而流於形式,而招來缺乏生命之譏。而真正的「鄉土教育」展現了教育最深的根源,是根植於現實世界的真實生活裡面。「鄉土教育」是讓兒童從身邊最貼近的、從最清晰的直觀所能夠獲得的生活範圍乃至經驗為開端,然後從此加以延伸、擴大。因此所謂的鄉土,既可以是如同休普蘭卡(E.
Spranger)所言:「鄉土乃是精神上的根本情感」或「與土地的被體驗與被體驗的全體統合」等就主觀層面向來觀看之;也可以是像威爾曼(O.Willmann)所說:「是超越了興趣與同情之對象的,與鄉土共同成長,鄉土感是倫理統合的契機……鄉土是眾人所渴望的一種財產,是所有陶冶倫理的統合中心點。」等等從客觀立場來論。鄉土情感的根本,姑且不論主觀或客觀面向,畢竟是因為其兼具兩者的特性因而可以在教育意義上獲得充分發揮。
而除了讓孩童認識它的環境周遭之外,我在北斗公學校還親身體驗了另外一種鄉土教育,那是一種與大自然直接接觸、並且是透過身體的勞動來累積自然的知識。當時所接受的「鄉土教育」概念,是直接承襲大正民主運動所遺留下來的新教育運動概念,廣義地來說,也可以將之視為「生活教育」。當時,在北斗公學校的實際教育中,各班級都有其分屬的田地,學生們可以在分屬的田裡種植蘿蔔、胡蘿蔔、茄子、花椰菜以及甘藍菜等等,或者,甚至也可以依四季推移而種植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學生們必須早晚勤加澆花鋤草,並且不得假他人之手,全靠自動自發而協力開展。在升上了較高年級之後,還會分配到佔地甚廣的水田,學童就像農夫一樣全程參與播種、插秧、鋤草以及割稻的程序。此外,還有以磚瓦築成的「堆肥小屋」,屋內高高疊有乾草、稻桿,每天從廁所挑出糞尿置於小屋之中,待其腐爛並且輪班定期翻攪。每當一靠近堆肥小屋,沖天臭氣撲鼻而來,而七十年前的肥料就是以如此的方式製作出來。這些差事都是利用下課或假日期間來進行。我在堆肥小屋做了數不清的工作,在水田裡的插秧、鋤草與割稻的工作也記得很清楚,這是再普通不過的工作,沒有什麼特別好提出來的。完全是出於自動自發,這已經是完全日常生活化的現代教育了。
這些教育深深地在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投下了深刻影響,對我個人而言,這早期的「鄉土」經驗一直是心內感動的原風景,也是文學創作的原點。而盧梭思想當中那些關於人的發現與解放,也一直是都是我詩作所追求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