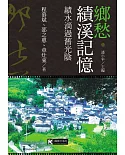新版序
二十年後 ∕李黎
就在不久之前﹐有位母親托朋友問我要一本【悲懷書簡】 -- 她的兒子一年前病逝﹐朋友從圖書館借出這本書給她看﹔她讀了﹐想要有一本留在身邊﹐可是不知哪裡買得到。我立刻把書寄去給那位母親﹐同時看著家中書架上僅存的寥寥數冊﹐心想﹕該是重印的時候了。
開始寫這本書裡的文字是二十年前。寫了整整一年﹐然後大致按照書寫的時序﹐整理之後出了書。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就這樣流逝﹐連自己都感到難以置信﹔而今原先的爾雅版已經絕版﹐但我不希望這本書從此絕跡﹐因為這已不是我一個人的書了 -- 十幾年來﹐已記不清送了多少本給我相信是需要讀它的人﹔更無從知道有多少人自己讀了﹐又送給了他們覺得需要讀的人… …
二十年是漫長的歲月。當時出書的一個主要的念頭是﹕寫下來﹐印出來﹐記憶就保存下來了。在舊版序言裡我開頭第一句寫著﹕「這是一本為生命中有過大失落的人所寫的書。」當然亦是實情。但以當時的心情﹐書寫﹐首要還是療傷﹐是為著安撫自己和逝者的靈魂。
後來的許多年 -- 先且不說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我自己生活和思想的變化﹐這本書有多少人讀到亦不得而知﹔但我知道這已經不是一本只屬於我自己的書了。二十年後﹐我已與生命達成了和解﹔我的「悲懷」早已深化、轉化成遠遠超越悲傷的領悟和接納。可是書名並沒有變﹐還是「悲懷書簡」 -- 但這裡的「悲」懷﹐到了現在﹐是慈悲的悲﹐是悲願的悲了。
「慈」.「悲」兩字﹐以我個人的理解﹐是有不同的。我覺得兩者相比﹐「慈」心比較容易﹐而「悲」心比較難﹔因為慈心只需善念﹐但悲心需要深切的體會﹐理解﹐感同身受。如今我之能「悲」﹐因為我經歷過﹐我懂得。
我曾對自己許下悲願﹕對於那些失去子女的父母﹐我願贈書﹐同時附上我的聯絡方式﹐讓他們知道﹕任何時候﹐都可以找我談心。我告訴他們﹕請隨時給我寫信﹐或電郵、電話﹔我的心﹐永遠對另一個母親﹐或者父親﹐打開。
我與許多失去孩子的父母親﹐尤其是母親﹐有過心與心的對話。他們想跟我說話﹐因為覺得﹕在那樣的時刻﹐全世界只有另一個有過相同經歷的父母才能懂得。悲傷是最最寂寞的情緒﹐而這份寂寞更加深了悲傷的痛楚。知道世上還有別人也承受過相似的遭遇﹐至少悲傷不再是那麼寂寞了……那是療傷的第一步。
即使不是失去子女的父母親 -- 任何人﹐失去了自己的所愛﹐不論以何種方式失去﹐這本書也為你打開﹐請你閱讀。
讀過一位智者寫的一篇題為〈落葉〉的文章。智者說﹕最難被人們接受的死亡,就是孩子的死亡。每當他幫忙主持孩子的喪禮時﹐需要面對的不僅是父母親人的悲痛甚至罪惡感的折磨,還要解答「為什麼?為什麼是孩子﹖」的困惑。於是他敘述了一位森林僧的頓悟 --
一位簡樸的僧人獨自在森林的茅篷裡靜坐。一天深夜,山林裡颳起非常強烈的暴風雨。黎明時分,風停雨住﹐僧人走出茅篷視察災情。突然吸引住他的,不是許多連根拔起的樹和散落地面的斷枝殘榦,而是舖滿森林地上那一層厚厚的落葉 --
地面上大部分的葉子都是年老枯焦的黃葉,但也有些是綠葉﹐而且這些綠葉當中有的還非常鮮嫩﹐顏色翠碧,可能在幾個小時前才剛從芽苞裡萌發出來呢。當下,這位僧人的心明白了死亡的本質﹕
當死亡的風暴吹襲著人們,通常帶走的是年老的人 -- 那些「斑駁枯焦的葉子」;同時也帶走很多中年的人,像那些發黃的葉子﹔可是正值黃金年華的年輕人也會死亡﹐正似那些早落的鮮嫩綠葉。有時候死亡奪走年輕孩子寶貴的生命,就如大自然的風暴奪走了一些新發的葉芽一樣。死亡的本質就是這樣,正如森林中的暴風雨是大自然的本質一樣。
智者的故事當然富有啟示﹐但接下來我們的疑問是﹕「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曾經常向「老天」或「命運」問過的問題。是啊﹐新出芽的綠葉也會被吹掉﹐但為什麼偏偏是我的那一片呢﹖
後來 -- 經過了許多年的學習和思索﹐我終於比較能夠換個角度看待這個疑問了﹕首先﹐為什麼不該是我﹖為什麼該是別人﹖為什麼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是不公平﹐那麼發生在別人身上呢﹖
其次﹐為什麼當好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就多半不會問「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我如此幸運? 」
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更能幫助促進我們思考和自省﹖
當我們想念著先我們而去的所愛之人﹐我們記住他們﹐同時希望這個世界也有其他的人記得他們。每個人有自己保存記憶的方式。無論以何種方式﹐全都是美的。而最最美好的﹐莫過於化悲痛為慈悲。
我認識、也聽說許多父母﹐以去世的子女名義成立慈善或教育基金會﹐或為有特殊意義的機構做義工﹐或捐贈書籍回饋鄉里……。多麼不可思議啊﹕即使是如死亡這樣絕望的事﹐都能經由慈悲的力量﹐轉化成帶來希望的行為。也唯有如此﹐逝者中斷的生命記憶才能延續﹐才不會在我們走後便被這個世界遺忘。
孩子逝世兩年之後﹐我懷著依依難捨的心情離開他的長眠之地聖地牙哥﹐遷來史丹福定居。當我得知史丹福的建校歷史﹐立刻對新居產生了親切之感。一百多年前﹐一場傷寒症奪去了史丹福夫婦十五歲獨子的生命。就在兒子病逝的那一天﹐這對還在震驚悲悼中的父母親﹐已經做出了一個決定﹕以他們的愛子之名﹐在家鄉設立一所教育機構。「從此﹐加州的孩子就是我們的孩子。」他們這麼說。
從此﹐不僅是加州﹐全世界許多優秀的孩子﹐都來到這處曾是那個早逝的男孩騎馬馳騁的莊園裡上學。
悲傷的淚水可以侵蝕臉頰﹐也可以化為滋潤枯草的春雨。
去年的四川大地震﹐死了多少孩子﹖(我不忍記住那些報導的數字。)那段時日﹐有多少傷心欲狂的父母親﹐若不是在哀悼﹐就是還站在廢墟前痴痴等待 (哪一種折磨更殘酷﹖)… …而走的幾乎全都是獨生子女。
痛苦的感覺是孤獨的﹐因為旁人難以感知﹔但痛苦的人其實不是孤獨的﹐因為周遭有太多人正在受各式各樣的苦。
許多不幸的事發生﹐我們或許沒有選擇﹐但如何應對﹐有時候我們是可以有一些選擇的。比如我在兒子剛走之後﹐心情最最低落的時日﹐有時真不想醒來面對新的一天﹐我就問自己﹕
我還要活下去嗎﹖(要﹐因為我還有責任﹐我還有個小兒子﹐丈夫﹐以及年近八十的老母親。)
那麼﹐我是要好好的活呢﹐還是像行屍走肉似的活﹖(既然要活﹐就好好的活吧。)
怎樣好好的活呢﹖於是我強迫自己起床、梳洗、換上整潔的衣服、出門辦事﹐不知道我的人看不出我是前一天還不想活了的人。
於是我就這樣一天一天的活過來了﹐並且告訴與我同樣經歷的人﹕你可以做得到。不要想這天是什麼日子﹐不要擔憂這天將要怎麼過﹐只要儘量好好的去過每一天。過一天﹐就是跨過了一道心障﹔然後﹐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我告訴他們﹕我就是這樣過下來的﹐你也可以。他們願意相信我﹐因為我們都是從同一條路走過來的。
在一份華文報紙的地方版裡﹐我讀到一則新聞﹕一個健康活潑的華裔男孩忽然病逝﹐家人師長如何震驚哀痛… …我立即找到寫這篇報導的記者﹐托他轉告那位母親﹕如果願意﹐請她隨時跟我聯絡。
我和那位母親開始通電郵、電話。她讀了我寄去的【悲懷書簡】﹐寫信告訴我﹐她不久前埋葬了自己兒子的心情。我在回信中這樣對她說﹕
「請妳這麼想吧﹕我們『埋葬』的並不是我們的孩子﹐那只是一個軀殼﹐一件不再能用的『太空衣』 -- 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旅行訪問時穿著這身衣服來﹐穿到破舊不能再用時﹐我們留下這件舊衣﹐回到我們來自的地方… …
「我知道妳現在所做的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找墓地﹐埋葬他﹐為他立墓碑……我都經歷過。妳只好不斷提醒自己﹕這樣做是為了他﹐為了不要讓這個世界忘記他。你是在為自己所愛的人做這一切。想到是為自己愛的人做事﹐就不那麼辛苦了。」
她說﹕多麼希望這只是一場夢啊!夢醒時我的孩子還好端端站在我眼前……
我回信說﹕「其實看長遠一點﹐人生整個的就是一場夢。夢是會做完的﹐只是做的時候感覺很真實﹐ 尤其在痛苦中的時候。所以只好打起精神面對這場夢﹐和夢中人的悲歡離合﹐儘量做好它。……我寫過一個短篇小說﹐主題跟這個想法有關。記得那時心情很苦﹐有一天忽然有一種頓悟﹐很快就寫出來﹐寫出來以後竟然就覺得好多了。」
我指的就是〈棋局〉這篇﹐我非常願意相信的一種可能。所以我把這篇加在這本書最後﹐作為新版的外一篇﹔以及﹐給予自己的一個解答。
校稿時重讀〈秋天的信〉那篇﹐發現那可能是我全書中最苦澀、最絕望的一篇。讀著自己囚禁在那樣的「心獄」裡寫下的文字﹐感到萬分的不忍。而今﹐好似大難之後的倖存者﹐我多麼慶幸自己走出了那個心獄 。重出這本書﹐就是我走出來的見證。
二十年後﹐書中對話和提及的人﹐有的健步成長﹐有的安穩前行﹐有的卻已隨歲月離散。〈悲懷四簡〉裡那個聰慧的小女孩黎明﹐現在是一對可愛的雙胞胎女兒的媽媽﹔而以那般誠摯的話語勸慰我的Echo﹐竟已離開世間整整十八年了﹗人事變幻﹐豈是滄桑兩字足以形容的呢。
最為感念的﹐還是書中提及的那些位當年扶持、至今依然相伴的人 -- 與我走過這一路的人﹐是我終生愛惜的友伴。
回首這段人生﹐無論是悲是喜﹐其實都是無常﹐終究都會過去。我們慨嘆好景不長、快樂時光如飛而逝 ﹐其實同樣的﹐悲傷也終究不會是永遠的 -- 任何一種狀態﹐無論好的或是壞的﹐都不會是永久的。
然後﹐悲傷可以化為思念﹐化為了悟﹐化為慈悲。
二十年後﹐唯有思念仿彿如昨。我的孩子長眠在陽光明媚的聖地牙哥北邊一處青草地下﹐不遠之外便是太平洋的萬頃碧波。蘇東坡的【江城子】是最感動我的一闋悼亡詞﹐我作了些改動﹐借來自述情懷﹕
廿年生死兩茫茫﹐長思量﹐總難忘。綠草孤墳,依然話淒涼。縱使相逢應難識,容已改,鬢如霜。 夜來夢回舊時光﹐天倫樂﹐聚一堂。相顧狂喜,醒來淚千行。從此年年腸斷處,藍天下,碧海旁。
2009年1月26日﹐於美國加州史丹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