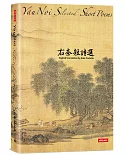推薦序一
登岸不捨舟,舟在岸方在
廖咸浩
─序義芝詩集《邊界》
應允寫序已有時日,但乍見《邊界》,仍覺強震襲來,且餘震不斷。這本詩集是陳義芝二○○三年之後的第一本詩集。在這期間,詩人經歷了喪子的人世至苦至悲,也從堅守多年的工作崗位轉入全新的生涯─學術界,如此巨大的變動似乎也預示著一個新的生命及新的詩觀即將的誕生。
如詩集的標題,這是一部接近「邊界」的詩集。邊界是什麼?詩人必是在無數次行近邊界時,面對各種不同的真象與幻象,而追索己身歷劫之始末、探問我佛諸象之變異。結果便如詩人在集中數度引言所證:時而在邊界之外必能著陸,時而奔走邊界尋尋覓覓,時而便只是懸擺著。確信「著陸」之可能或因情仍流連?不斷「尋覓」之必要顯係肇因於與現實之碰撞與往還。而「懸擺」便更接近人世終極的提問了。
詩集分三卷,看似有某種進程,但因為時間交錯,詩人的思緒其實也往返交織,前後呼應。詩人可以說是不停的進出不同的叩問人世的模式。而每次進出都不由自已的在邊界盤桓試探。
卷一重情,尤其是隱晦的情欲。那個抒情的陳義芝還是在我們身邊自在如昔:或借景寫情(〈海邊的信〉,〈沙灘二帖〉),或寓情於物(〈可不可以,阿勃勒〉,〈槐花〉,〈山行薄明〉,〈封印〉),都信手拈來、毫無滯礙。偶而的俏皮也運用自如,如〈海邊的信〉:
除了燈火翻譯的山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
除了勞倫斯詠嘆的蛇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
想必是觀音……蛇游進他看不見的詩裡了
或〈傾斜〉:
今夜敢教我的筆顛覆火狐的床
令花托傾斜
達達是
永遠的主義
但也許就是這幾年的經歷,詩作中即使離邊界未遠者,也時有矇矓不可及之時:比如,經過徹夜的歡愉,今晨的白鴿或只是「昨夜的霧」?(〈沙灘二帖〉),又如,男人與女子互相思念、但永遠錯過(〈風吹土耳其玉藍〉),馴至〈秋天的故事〉發生了亦如未曾發生。
但更撼動讀者的則是越過優美與感傷的竹林後,乍現的深谷。當他「一跪一拜進到山深處∕回望地上的火把∕都是歡娛的星∕掩住∕全山的暮色」(〈跪拜〉),是捨?是不捨?似猶待定奪。而面對莎弗的殘篇時,他只覺得那是「海天最後的光」,令他「戰慄」,並「掏空〔他〕的心」(〈凝視〉),就更非尋常之情。
在本集中,「戰慄」實是貫穿其抒情的基脈之一。悲傷與無常所反襯下的情欲,總是金底而鑲著黑邊,黑色的雲在背景中隱約而固執的暈染著:
疾馳我身體
貼住你心跳
悲傷的呼吸在戰慄
交疊著你
荒煙的密語
—〈黑夜的風〉
情欲的高潮不免戰慄於生死交界之模糊,而認知「血比夜更深∕比睡更宿命」,他遂向「最幽邃的礁石」朝拜,並偕「黑夜的風」朝異域疾馳而去(〈黑夜的風〉)……
卷二擴大呈現了詩人過去已有的支流─與社會現實的對話─角觸益廣、鞭辟益深。如對環境沉淪的義憤(〈遙遠的河〉)、對政治現實的針刺(〈蚊子世紀〉、〈夢卓夢采〉、〈未完〉)、對於父祖的原鄉無法抗拒的牽掛(〈一輩子的事〉)、對戰爭的反省(〈死者與苟活者〉)、對人道的關注(〈緬甸的孩子〉、〈第一時間已經過了〉)等。
其中與商禽對話,寓寫父祖之輩雖如風中殘燭,而仍全心投注於詩的鍛造;最後勉力說出「bird」這個域外的字眼,更似猶有展翅高飛的老驥之志。對比詩首老詩人一句:「可惜∕鄉音在十五歲離家那年∕就亂了」(〈一輩子的事〉),更分外襯出結尾之哀傷如離群之候鳥:
是逃亡的天空嗎?
他說不,是哀鳥,一面張開肩膀
想起身去找。微弱的
他說……bird……
在〈遙遠的河〉這首環境倫理詩中,只見那個身披「青衫」的少年、那個悸動於「不安的居住」的中年人,在「大雨過後第七天……一人孤獨地沿河走」。但他迅即發現那河已消失於「蒸發」,自己也已變成「遙遠的泡沫」,在人生的邊緣可有可無的浮沉著。〈遙遠的河〉確是一首關懷環境的詩,卻也飽含著詩人自己的滄桑。蒸發的是河?還是生命的能量?在此,我們也看到了詩人雖含悲茹苦,卻反而擴大了自己的生命尺度。
而且,我們也再次看到了卷三的伏筆。第七天原是創世的圓滿之日,但如今天地已變色,有若時光退行,又回到洪荒。變成了「遙遠的泡沫」的自己,爾今以後,將何所依憑?卷三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心被掏空、外在世界遭蒸發、無限接近死亡,也屢屢側身幻境的詩人,如何在此孤絕之境,試圖尋找最後的依憑。
詩人也曾如卷一〈歸來〉一詩中所述,倦遊歸來,忽聽見「心底的聲音」問「你好不好」時,仍勉力對人世心懷薄願:
銀河的車窗全開著
祈願的香頭全燃著
越過重山後我們又歸來
水岸的燈火仍搖晃著
面對川震中孩童的死亡,他也能在廢墟中聽到一絲歌聲、看到一縷香煙:
學校也只剩一支折斷的旗桿
你仍聽到孩童的歌聲
不斷地,不斷地傳來
即使入睡
仍越過斷崖,堰塞湖
在廢墟悠蕩著
像半熔融的岩板焚燒
一炷炷香
—〈第一時間已經過了〉
然而一旦轉入另外一種叩問人生模式中,即使來到佛教之鄉,卻仍無法時時專注:
我盤腿獨坐樹下
默誦經文如訪迷宮
日光左移三吋心也游移三吋
只聽得啾啾的林鳥
發出一聲聲單音
─〈仰光〉
面對金碧輝煌的佛寺時,亦不免思及根底處的無常:
二千五百年金塔一瞬可成灰
何謂輝煌?當日光隱入層雲
驟雨即將降下
—〈仰光〉
詩人既與佛結緣卻仍遲疑躊躇,乃是因為至苦至悲之後,世事已恍若隔世:
從前優游的廣場
今成交錯的道路
從前爛嚼在心的魂魄
今成穿雲的哀歌
—〈無岸五首:故事不存在〉
世事之無常在詩人內心已築起一座深邃無底的黑屋:「有人∕在黑屋∕無依傍的∕河中∕漂浮∕失聲地∕哭」(〈哀歌〉)。於是,詩人遂如風中飄傘,無枝可棲:「強風中我一心想著陸的傘∕兀自擁抱著黑夜∕無邊無際的呻吟」(〈罌粟〉),或蜷曲自鎖如一向內旋轉之漩渦:
我在荒山野嶺找棧道
在寂寞天地找斜長的樹影
黑夜如哭的日子
扭絞自己成握拳的漩渦
—〈無岸五首:岸〉
及至極悲處,遂向天地呼求:
傳我一柄火裂的木琴
叫天地靜穆
把難以相信的死
也托住
—〈晚課〉
詩人也曾在情欲中試圖寄寓「白屋」(〈風吹土耳其玉藍〉),但山腰上的黑屋卻是永恆的異色誘惑,需剃度為絕情之尼以絕之:
一幢黑屋在山腰
每晚我拾級而上
去開它的門點它的燈
一幢黑屋在內心
每晚我睡臥野地
直到黑屋消失在曙光裡
—〈無岸五首:絕情尼〉
詩人一次又一次接近邊界,一次又一次嘗其苦寒,其最寒冽處已是:「天色乍明∕枯葉∕似冰涼的∕白刃∕掠過∕夜夢已∕無蹤」(〈哀歌〉)。至此,詩人不落痕跡的做出了人生最終的提問:源源不斷、彌天蓋地而來的文字,包括詩人自己鍾愛、努力冶煉的文字,是否如枯葉般,無法追索那變幻若夢的人生;或枯葉之掠過,徒然將夢驅逐無??經過大悲大苦後詩人所悟乃是:
當所有的字都消失
還有命運那熒光一閃
藏身在
無律法的
基地
—〈斜坡五首:消失〉
但關於命運與律法的迷團,仍需詩人與佛進一步的交融,才能漸入空境,體悟求生與求歡都有如羅漢趺坐密林之中,空空如也(〈密林〉)。但在更近悟道處,佛是師父無所不在的「彩虹的身體」,佛更是自己諸般的苦難與無端的我執(〈彩虹的身體〉)。如果依精神分析論者拉崗的說法,在全無依憑時,主體懸擺(dangling)於虛空中,反利於證成道身於「病徵」。而「懸擺」正是詩人此刻的絕境與化境。
但最終而言,詩集不是一部心智演化史,而且一本詩集也無法被一篇短序所窮盡,畢竟詩人是易感而多樣的、是翻來而覆去的。但詩人主要的脈動倒確是落在佛語入詩之時刻。以佛語入詩,頓時似經若偈,卻能成詩也能壞詩。但詩人以此展示成住壞空與「我」的因緣時,在掙扎外另有一種自在,或就是在無心間已得禪宗的三昧─登岸不捨舟,舟在岸方在。
推薦序二
飄泊之風,抵達之歌
陳芳明
─讀陳義芝詩集《邊界》
細讀他的詩,可以感受濃烈的秋天顏色。那是季節垂晚時釋出的成熟氣味,是歲月飽滿時呈現的醇厚色澤。秋天意味著國境的遼敻,情感的極致,想像的巔峰。必須歷練過生死離合與恩怨情仇,生命的質感才有可能累積起來。跨過中年的陳義芝,迎接的正是這般風景。他的詩筆溫暖中暗藏悲涼,熱情裡透露冷靜。詩風的形塑,絕對不是通過文字的刻意追求,而是生命經驗的自然流露。
嘗盡傷害的滋味,承受折磨的苦楚,他終於到達那裡。那裡是生命的邊界,鄉愁從此迤邐展開。他選擇停佇在邊界,既看到完整,也發現殘缺;既回望從前,也遠眺未來;既面對真實,也徹悟虛幻。詩人之眼具有雙重視野,只因為他到達邊界與越界交接的地方。
風的意象,注入他的詩行。在詩的密林吹拂著看不見的風,一如思想的飛翔,情感的流動,於靜默的對話中感知它的存在。然則,那是充滿聲音與節奏的風。他可能是同輩詩人中最具浪漫主義特質的一位。如果把他放在台灣的抒情傳統,那種拘謹卻雍容有度的風格,確實帶來了無盡的喜悅。他擅於釀造欲開未開、欲止未止的語言;流動性很強,卻不致過於濫情。這種詩風很難命名,稱之為邊界詩風,庶幾近之。情與景相互支撐,也相互牽制,而造就了圓融之美:
我十分靠近你無法碰觸你
四月的風不停穿梭
流星雨一般的你
我不能看著你渴望碰觸你
可不可以,阿勃勒
五月的陽光已一瓣瓣
撥開風,撥開了
金色全裸的你
—〈可不可以,阿勃勒〉
當作情詩閱讀,是這首詩產生的歧義。當作詠物詩來讀,意義又不止於此,而終於造成欲言又止的效果。陳義芝早期的情詩,可能都是為不存在的情人而寫,卻有特定的指涉。這首詩面對著一種絕美植物,竟疑真疑幻浮現一位情人的形象。阿勃勒是風情萬種的夏樹,英文稱為黃金雨(Golden Shower
Tree),綠葉黃花,動人心弦。詩中第一段是四月的風,第二段是五月的陽光,精確點出暮春初夏的季節。詩人投入情感時,靜態植物立即化為動態人物。詩題〈可不可以,阿勃勒〉,暗示一種渴望;詩行「我不能看著你渴望碰觸你」,則又揭露一種焦慮。全詩因「金色全裸的你」而帶有禁不住的誘惑,由於無法碰觸而自我壓抑。第一行與最後一行之間,緊繃著拉扯的張力,未完成的慾望撐起了一首已完成的情詩。說清楚了甚麼,又甚麼都沒說,正是他欲擒故縱的技法。
他的情詩特別偏愛聲音與節奏,藉由律動的迴旋,把壓抑在體內的歌釋放出來。這種無法具體詮釋的情感,再次訴諸於風的意象。捉摸不定的情愛,徘徊在隱晦與顯影之間的可疑地帶,唯風差堪比擬。
血比夜更深
比睡更宿命
朝拜最幽邃的礁石
黑夜的風
我帶你去異域
—〈黑夜的風〉
看不見的風,在黑夜更看不見。然而,因情的加持使風變得可以觸摸。不容易定義的情感,並非不能定義,主要它是「比夜更深,比睡更宿命」的熱血。在到達最後一段之前,情愛是鬼火的雨,是流螢的風,是荒煙的密語,挾帶著深沉的憂傷。在一定的邊界裡得不到寬容,越界而去後便容許存在。邊界詩風於此又獲得印證:「黑夜的風∕我帶你去異域」。然而,那竟是未完成的隱喻。真實與虛幻,期待與實現,兩者之間似乎是彼此悖離。這樣的悲歌,反而是情詩最為媚惑之處。
抒情的聲音,既真切又不確切,因為它比生命巨大,也比生命渺小。搖蕩之情啟動時,可以震撼天地。但是在發生的時刻,卻又無人能夠察覺,畢竟那是屬於私密的世界。他的情詩之令人著迷,在於他處理語言時,把濃郁的感覺化為客觀景物,終於稀釋了過於稠密的情緒。他稀釋的技藝,仍然訴諸風的流動:
是風問還是人在問
你好不好?
夜來坐看跨岸的橋影
迅速掠過你脖頸的一抹月光
驀然聞到甘蔗香的蓮霧
我說好。不是風
是心底的聲音
—〈歸來〉
詩中語言的跳接有其內在邏輯,毫不相干的意象並置在一起,為的是暗示背後有一線情感牽繫著。坐看河岸夜景的兩人不需任何語言,迎風之際內心其實是在對話。情到真處,時時都在問好。把彼此含蓄的關切都歸諸於風,正是這首詩的動人所在。詩人刻意顧左右而言他,納入橋影、月光、蓮霧,無非都是在構築共同的記憶。微風的撩撥,使內心的答問產生流動,這正是陳義芝苦心營造情詩的神來之筆。
在中生代的詩人朋輩中,陳義芝的情詩直追鄭愁予、楊牧、林泠。在抒情傳統中的現代詩人,往往不是勇於語言的實驗,而是完全從情感的體驗中自然衍生語言。世間的愛情可能都不可理喻,但台灣的抒情語言卻完全在合理的語言中發展。陳義芝更是如此,他從未創造石破天驚的句法,卻能夠開出令人意外的想像之花。以〈手稿〉為例,情感的親密與疏離是這首詩的主題。他以如下四行寫出情愛的相互依賴:
我們,是門與門鎖
床與床墊的關係
沙發與脊骨
餐桌與手肘的關係
門鎖、床墊、沙發、餐桌,烘托出一個家的格局。只有親密的愛人,才能建立起牢不可破的關係。這樣的關係斷裂時,詩中以如下四行結束:
我留下一部未完的手稿
給你
你留下一個不關的窗子
給雨
最後一段的你與我,鮮明刻畫了兩人的關係。未完的手稿,是未完的愛情遺物,也暗示詩中寫作者曾經辛苦經營兩人的關係。不關的窗子,則暗示情人負氣離家出走的場景。這首詩的前半段是說理,後半段是敘事,結構看似突兀,卻非常和諧。幾乎很少有詩人敢於做這種嘗試,但陳義芝做了相當合理的結盟。尤其是最後兩行,具有高度的故事情節。「你留下一個不關的窗子∕給雨」,頗能引發聯想。詩人捨棄排比對仗的句法,寧用「給雨」,而非「給我」,使想像空間更為開闊,整首詩更強化了「未完成」的氣氛。有一種殘破悲涼的氛圍,徘徊不去。
現代詩裡出現對仗的句型,有時可能容易淪為庸俗。但是,陳義芝卻大膽使用,而把古典詩與白話詩隔行並置,不能不催生讀者連綿不絕的聯想。〈未完〉這首詩,迥異於古典詩的改寫,兩種文體竟可並行不悖,從而造成奇異的問答,更衍生奇異的美感:
不知江月待何人
漂泊的江北人變身漂流的江南人
但見長江送流水
不歸的海峽人變身不安的海島人
白雲一片去悠悠
未名的天涯人變身無名的天下人
青楓浦上不勝愁
相思的中國人變身相忘的台灣人
〈未完〉由兩首構成,這是第二首。其中的古典詩引自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千年來中國古典詩描寫鄉愁的傑作。全詩主要以「江」與「月」的意象拉出離愁的歷史場景。陳義芝拿來描繪一位在海島出生的「外省族群」共同心情。超過半世紀以來的懷鄉意識作品,一直是流亡者、放逐者的最佳寫照。但是,從未有詩人以古典詩做為引子,點燃現代漂泊者的痛苦之思。古典詩體意味著千年不變的鄉愁,現代白話文則揭示五、六十年來流落島上外省人的心情。張若虛筆下的主角是一位思婦,對於離鄉背井的情郎有深不可測的寄情。陳義芝創造出來的白話詩句,則是描繪島上外省人的矛盾情結。如果把古典詩抽離出來,詩中的白話句式顯然沒有任何感發力量。在抑揚頓挫的古典詩行之間插入白話鄉愁,竟產生一種問答式的回應。張若虛提問:「不知江月待何人」,陳義芝回答:「漂泊的江北人變身漂流的江南人」。這一問一答,竟然可以把現代最大的流亡圖勾勒出來。受古典文學薰陶出來的詩人,敢於做這樣的實驗,正好反映了古典絕對不是僵化的古典。同樣的,一位從事現代詩創作的詩人,敢於向古典汲取詩情,也更加印證現代詩運動不必然就是反傳統。〈未完〉一詩,暗示了一個未完的工程。現代詩人如何與古典建立對話,顯然還有無窮盡的想像等待挖掘。
〈問答詩〉也同樣以文言文問候,以白話回答。
平居與誰相從?
有可與語者否?
總因過於相信枕頭
以致落了枕
過於相信側睡
以致傷了左右手
這首詩看來似乎答非所問,卻點出問者與答者之間的友情。只有可以推心置腹的人,才會告知最尋常、私密的瑣事。在問答的過程中,陳義芝的幽默令人會心一笑。這樣超脫與豁達,也許不是青年時期的詩人可以輕易獲致。歲月驅趕他到達年齡的特定關口之際,詩境也自然開闊。
對生命的體悟,對人情的透視,絕對不可能從語言訓練而來。從前未曾看到的世界真相,只有在生命墊高之後才能看得明白。詩藝的深化與淨化,誠然必須求助於人生歷練。然而,最痛苦的試煉,卻是來自生離死別。那種精神上的刑求,非親身體驗者無法理解。陳義芝的散文集《為了下一次的重逢》,一字一淚鏤刻著喪子之痛。失去孩子的詩人,唯一的救贖就只能通過文字,當所有的對話管道完全切斷之際:
除了經文爐香和對菩薩的跪拜
你已將一生得自父母的骨肉蜷縮進
一尺見方的骨罈,告別眼中淚心頭血,告別
四季分明的異鄉長夜最後的輾轉
我們誰也說不出來的話
—〈焚燬的家書〉
死神降臨在毫不設防的心房,那是絕對而絕情的毀滅,人間的情愛如何精心營造,都無法抵禦死亡的瞬間到來。在那時刻,詩人驟然被押到生命的邊界。到達那裡,前生今世判然分明。陳義芝偏愛昆德拉的那句話:「只需前進一點,無限小的一點點距離,人就會發現自己是在邊界的另一端。」在最絕望的時刻,詩藝是不是從此放棄?孩子的死,使詩人在最短期間頓悟生命的真與幻。他終於選擇向邊界之外前進一點點,正是那小小的移動,使他整個詩觀全盤調整。他並未偏離浪漫主義的基調,只是輕染秋天的氣色:
天色乍明
枯葉
似冰涼的
白刃
掠過
夜夢已
無蹤
—〈哀歌〉
寫於暮秋的這首詩,意味著他對世界的感覺。從未使用簡短句式的詩人,完全依賴澄明的意象來烘托心情氛圍。乾淨俐落的節奏,見證夜夢的消失沉沒,以一張冰刃的落葉姿態。在情愛世界漂泊之後,像看不見的風跨越邊界,詩人抵達了另一個詩境:
早於前生的海
藍晃晃
早於前生的天
紫濛濛
早於前生結跏趺坐的我
乃妙齡剃度一絕情尼
—〈無岸五首:絕情尼〉
這絕情尼藉由詩人再生,投入烈烈紅塵,以曠達之心擁抱世界。他的投入是浪漫主義的延伸,他的詩藝是抒情傳統的擴張。他挺起詩筆,向前移動,抵達邊界另一端。
二○○九年四月二日政大台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