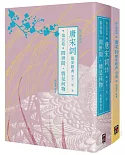〈孔雀東南飛〉號稱中國五言詩長篇之聖,就筆者看來,內容主要是敘述焦仲卿、劉蘭芝夫婦的家庭、婚姻與愛情問題。不過,此詩歷來論者甚多,意見莫衷一是,甚至辯鋒四起。基本上,他們多認為本詩是反映蘭芝反對封建禮教以爭取自由,最後不惜殉死之作;並為此將蘭芝定調為勇敢,仲卿為懦弱,焦母為凶惡,劉母為慈愛,而劉兄則定調為勢利,使人格鮮明、問題清楚。
此在筆者看來,他們固然跳不出善惡二元的思考模式,甚至也跳不出反封建、反禮教、反權威、反家父長權,以及爭取自由的老套。然而,本詩所述牽涉漢末以至魏晉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制度之大變動,更牽涉仲卿、蘭芝的工作、家庭、婚姻與愛情之複雜糾紛,真的能做如此作簡單分析與詮釋嗎?
為此,筆者意欲針對本詩所述內容,從心理與行為、個人與社會、人權與價值,以及本詩作者的教化之旨,進行另一角度的論證與詮釋,冀對本詩之愛好者能貢獻一己之愚見,使真相能有更深入與全面的瞭解。
作者簡介
雷家驥
國家文學博士,現任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常在兩岸大學歷史系遊訪講學,連本書迄今著有書籍八部、論文六十篇,本書姐妹作《史詩三首箋證》亦近將出版,所著《武則天傳》已列入大陸之「中國文庫」史學類。
目錄
自序
論〈孔雀東南飛〉箋證之所謂自由—為世變與蘭芝家變關係及本事之所由起進一解
一、前言
二、本事之發生以及當時之自由觀
三、蘭芝夫婦之勞動權、休息權與自由權問題
四、焦、劉兩家背景與蘭芝之所謂「自專由」及「自專」
五、結論
〈孔雀東南飛〉箋證
一、證題
二、證序
三、證詩
四、結論
論〈孔雀東南飛〉箋證之所謂自由—為世變與蘭芝家變關係及本事之所由起進一解
一、前言
二、本事之發生以及當時之自由觀
三、蘭芝夫婦之勞動權、休息權與自由權問題
四、焦、劉兩家背景與蘭芝之所謂「自專由」及「自專」
五、結論
〈孔雀東南飛〉箋證
一、證題
二、證序
三、證詩
四、結論
序
自序
初中受黃超海老師啟發,喜好詩詞歌賦、書法國畫,以至油畫琴笛,陶然醉焉,夢想他日能成為文學藝術家。家父見流連不已,誡以是世家子弟不務之急,丈夫應習實學,以俟日後能養妻活兒,故於上學之時,集余所有書畫工具一併焚之,琴笛亦去向不明。吾父教子嚴急,遂不敢違,自傷而已!然而詩詞歌賦為所不能燒,以故仍保持興趣,習作不輟,於今已四十餘年矣。我讀詩以兩漢迄全唐為主,尤好樂府,所讀之多應不下於研習中國文學者,暇興之來亦頗有偶作;然港、臺之間遷徙數次,舊稿百不存一,喟然可為歎息!
由於興趣在此,故讀新亞研究所時,承錢賓四師治史應兼習文哲,以待會通之國學教風,又蒙嚴歸田師首肯,遂以〈曹植贈白馬王彪詩並序箋證〉為題,兼以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為法,作為論文研究。其後執教於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亦以此教旨方法與諸生講習,開設「中古史詩專題研究」課程多次。其間,曾有兩詩—〈悲憤詩〉與〈孔雀東南飛〉—箋證之作獲得國科會獎助,另一篇—〈木蘭詩箋證〉—則是為首次赴大陸參加唐史學術研討會而撰。〈白馬詩箋證〉、〈悲憤詩箋證〉及〈木蘭詩箋證〉均已先後發表,但〈孔雀東南飛箋證〉則因篇幅逾十萬字,刊登不易,故迄未發表,似有失信於國科會之嫌,是用耿耿於懷。近因休假一年,整理舊文,蒙蘭臺出版社同意將四詩箋證結為專集。蘭臺以為四箋篇幅均甚長,故將〈孔雀東南飛箋證〉連同余曾做主題演講的〈論《孔雀東南飛》之所謂自由—為世變與蘭芝家變關係及本事之所由起進一解〉一文,合併為冊,仍名曰《孔雀東南飛箋證》;餘下三箋則另成一冊,名曰《史詩三首箋證》。茲以出版在即,故序其概略,用志其意。
詩者何?《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毛詩.關雎》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則詩為言志之作,原非為述事也。此所謂志,其實就是心意及心意之所趨,因而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並無道德儼然的意謂。
今所箋四詩,三首作於漢末,僅〈木蘭詩〉作於北朝。本人以為四詩皆是「史詩」。〈悲憤〉與〈白馬〉是自傳式史詩,作者蔡琰與曹植於詩中均自述其苦難遭遇,大有面對苦難命運而痛苦、無奈、承受之意。〈孔雀〉與〈木蘭〉則是他傳式史詩,前者表達主角面對苦難命運之痛苦、反抗、不接受,以致最後悲劇收場。然究其實,〈悲憤〉、〈白馬〉與〈孔雀〉三詩均是詠嘆命運之苦難、痛苦與無奈,以故感人甚深;只是〈悲憤〉與〈白馬〉詠嘆其本人之面對苦難、承受苦難,而自我消解,而〈孔雀〉的作者則試圖以「悲劇之圓滿」作為結局罷了。至於〈木蘭詩〉,卻是雄健雅正、激勵人心之作,與此三詩風旨大相逕庭。四詩之中,除了〈白馬〉較少之外,其餘皆論者甚多,主觀者有之,偶感者有之,隨筆者有之,僅為欣賞者亦有之,不勝枚舉,頗多不符學術研究之旨,因此本人於箋證中,非必要均不贅引。要之,四詩的確皆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之作,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化,寓「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教,只是〈孔雀〉之作者於詩末更直接挑明「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的說教旨意而已。
余之所謂「史詩」,固與對史起興抒懷的「詠史詩」不同,亦與歐美之「Epic」定義頗異。本人認為所謂「歷史」也者,是人類在過去特定時空曾經展現發生過之情感思想行為事件,而又可印證覆按者,此即所謂「史事」,亦即司馬遷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者是也。據此而論,「Epic」僅是「敘事詩」,所述雖有故事的完整過程,但是不免滲有大量的誇張、傳說以及神話成份,甚至可以是「虛」構的,此即「作」也。至於余所謂之「史詩」則不盡然,它是詠述過去「史事」之詩,是可印證覆按的,是「實」的,屬於「述」的性質。據此淺見,四詩不論內部構造以及外部構造,均可承受歷史論考覆按之考驗,尤其〈悲憤〉與〈白馬〉二篇,不僅與作者之時代可以相考論,抑且也可以與其個人之人生相印證;至於〈孔雀〉與〈木蘭〉則因是他傳性質,以故「史詩」之中不免兼有「敘事詩」的性質,而對主角之人生印證不易。「史事」經他傳作者之渲染則變成「詩事」—即詩文所述之事實。然而,印證不易的主角人生,仍可分由兩途以資探索,一是透過歷史時代由外部構造進入內部構造以作解釋,二是透過詩文所述之完整「詩事」以作分析,內、外考證兼用,以史證詩、以詩證史與及以詩證詩交辯,「史事」與「詩事」互證,然後析而解之、詮而釋之,庶幾猶可有得。
我讀論者對諸詩之分析與詮釋,常覺得他們大都在對「史事」乃至「詩事」未求甚解之前,即對事情及其意義逕予論斷或詮釋,以故對諸詩不僅迄無定解,而且爭議叢生。此詮詩方法上的缺憾,縱使前人深於文史者如王安石與司馬光等大家亦然。我在新亞研究所之所以選曹詩為題撰寫論文,正由王、馬二人酬唱〈明妃曲〉所啟發。按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大意勸王昭君不要再年年思念漢朝與家人了,因為「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所以應該珍惜當下;但是昭君之去國,在胡真的快樂嗎?司馬光讀後,作〈和王介甫明妃曲〉,持論大唱反調,大意謂漢主要昭君「和番」是出於傷心無奈,因此她即使不能適應胡俗,在胡中不樂,欲有「終期寤人主」之心,然而還是要勸她效法「被讒仰藥更無疑」的太傅蕭望之,對人君應該忠心與服從。不過,昭君在胡中的孤寂以及不適應,溫公能體會嗎?夜靜一再誦詠,復覆按兩《漢書》,覺得二子不免忽視史實以及昭君的自主感受,未必得到昭君無辜入宮而負氣去國之意,遂代昭君草作〈答明妃曲〉以奉和,於今猶記得其辭略云: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衫鬢腳垂;縱然惹得帝驚看,落得清談飯後餘!
誰憐弱女氈城泣,此去空然無所得;夫子非愛兒非類,日夜思親徒焦急!
不意荊公開金口,作曲勸妾休回首;君在上邦奈妾何,為君再撥春風手:
身屬荊州南郡城,長在民間已娉婷;孰料天子春念動,虛度清秋掖宮庭。
入得禁內已無言,盼望君王垂眼憐;不意畫像看來醜,當時恨無十萬錢。
桓桓單于覲元首,馬躍龍騰京師走;漢家君臣齊失措,贈與侍女結長久。
去國心知難有為,嗟歎天漢世運低;遂教泱泱大國女,嫁了單于嫁若鞮。
此事焉能向誰語,君教妾身如何處?失意果然無北南,付與梨花春帶雨!
野闊天高兩茫茫,風吹草偃見牛羊;年年目送鴻雁歸,唯託琵琶訴衷腸。
幽咽難得留至今,後人不識前人心;出塞逸調唱千古,冷寂那堪告知音。
滄桑彈遍世人知,豐容靚飾不可恃。若能締結真緣份,天大幸福莫遲疑!
君不見乎:
玉環飛燕皆塵土,西施與妾已荒槁;縱然嬌豔動天地,到頭仍然難討好!
或許我也未得昭君之心,然而漢女不易適應胡人生活文化,卻可從蔡琰〈悲憤詩〉中體會。要之昭君的入宮去國、赴胡和番、夫死嫁子,以至親生子因非純種而遭排斥,最後被殺,在在束縛而無自由可言,其事尚可按諸史傳。不先究明其情其事即予論斷詮釋,則所言之志、所述之事終將有誤,可以無疑。此所以我對〈孔雀〉、〈木蘭〉兩篇,仍必須贅證其詩文所述之「詩事」也。
《禮記.經解》述孔子之言,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余素性急切,雖遍讀眾詩,但猶無得於詩教之化;只是若非好詩,則恐怕急切尤甚於今!余為二兒取名為中行、中和,典出《論語》與《中庸》,蓋盼吾兒毋效其父,而亦以自誡也。是為之序。
初中受黃超海老師啟發,喜好詩詞歌賦、書法國畫,以至油畫琴笛,陶然醉焉,夢想他日能成為文學藝術家。家父見流連不已,誡以是世家子弟不務之急,丈夫應習實學,以俟日後能養妻活兒,故於上學之時,集余所有書畫工具一併焚之,琴笛亦去向不明。吾父教子嚴急,遂不敢違,自傷而已!然而詩詞歌賦為所不能燒,以故仍保持興趣,習作不輟,於今已四十餘年矣。我讀詩以兩漢迄全唐為主,尤好樂府,所讀之多應不下於研習中國文學者,暇興之來亦頗有偶作;然港、臺之間遷徙數次,舊稿百不存一,喟然可為歎息!
由於興趣在此,故讀新亞研究所時,承錢賓四師治史應兼習文哲,以待會通之國學教風,又蒙嚴歸田師首肯,遂以〈曹植贈白馬王彪詩並序箋證〉為題,兼以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為法,作為論文研究。其後執教於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亦以此教旨方法與諸生講習,開設「中古史詩專題研究」課程多次。其間,曾有兩詩—〈悲憤詩〉與〈孔雀東南飛〉—箋證之作獲得國科會獎助,另一篇—〈木蘭詩箋證〉—則是為首次赴大陸參加唐史學術研討會而撰。〈白馬詩箋證〉、〈悲憤詩箋證〉及〈木蘭詩箋證〉均已先後發表,但〈孔雀東南飛箋證〉則因篇幅逾十萬字,刊登不易,故迄未發表,似有失信於國科會之嫌,是用耿耿於懷。近因休假一年,整理舊文,蒙蘭臺出版社同意將四詩箋證結為專集。蘭臺以為四箋篇幅均甚長,故將〈孔雀東南飛箋證〉連同余曾做主題演講的〈論《孔雀東南飛》之所謂自由—為世變與蘭芝家變關係及本事之所由起進一解〉一文,合併為冊,仍名曰《孔雀東南飛箋證》;餘下三箋則另成一冊,名曰《史詩三首箋證》。茲以出版在即,故序其概略,用志其意。
詩者何?《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毛詩.關雎》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則詩為言志之作,原非為述事也。此所謂志,其實就是心意及心意之所趨,因而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並無道德儼然的意謂。
今所箋四詩,三首作於漢末,僅〈木蘭詩〉作於北朝。本人以為四詩皆是「史詩」。〈悲憤〉與〈白馬〉是自傳式史詩,作者蔡琰與曹植於詩中均自述其苦難遭遇,大有面對苦難命運而痛苦、無奈、承受之意。〈孔雀〉與〈木蘭〉則是他傳式史詩,前者表達主角面對苦難命運之痛苦、反抗、不接受,以致最後悲劇收場。然究其實,〈悲憤〉、〈白馬〉與〈孔雀〉三詩均是詠嘆命運之苦難、痛苦與無奈,以故感人甚深;只是〈悲憤〉與〈白馬〉詠嘆其本人之面對苦難、承受苦難,而自我消解,而〈孔雀〉的作者則試圖以「悲劇之圓滿」作為結局罷了。至於〈木蘭詩〉,卻是雄健雅正、激勵人心之作,與此三詩風旨大相逕庭。四詩之中,除了〈白馬〉較少之外,其餘皆論者甚多,主觀者有之,偶感者有之,隨筆者有之,僅為欣賞者亦有之,不勝枚舉,頗多不符學術研究之旨,因此本人於箋證中,非必要均不贅引。要之,四詩的確皆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之作,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化,寓「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教,只是〈孔雀〉之作者於詩末更直接挑明「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的說教旨意而已。
余之所謂「史詩」,固與對史起興抒懷的「詠史詩」不同,亦與歐美之「Epic」定義頗異。本人認為所謂「歷史」也者,是人類在過去特定時空曾經展現發生過之情感思想行為事件,而又可印證覆按者,此即所謂「史事」,亦即司馬遷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者是也。據此而論,「Epic」僅是「敘事詩」,所述雖有故事的完整過程,但是不免滲有大量的誇張、傳說以及神話成份,甚至可以是「虛」構的,此即「作」也。至於余所謂之「史詩」則不盡然,它是詠述過去「史事」之詩,是可印證覆按的,是「實」的,屬於「述」的性質。據此淺見,四詩不論內部構造以及外部構造,均可承受歷史論考覆按之考驗,尤其〈悲憤〉與〈白馬〉二篇,不僅與作者之時代可以相考論,抑且也可以與其個人之人生相印證;至於〈孔雀〉與〈木蘭〉則因是他傳性質,以故「史詩」之中不免兼有「敘事詩」的性質,而對主角之人生印證不易。「史事」經他傳作者之渲染則變成「詩事」—即詩文所述之事實。然而,印證不易的主角人生,仍可分由兩途以資探索,一是透過歷史時代由外部構造進入內部構造以作解釋,二是透過詩文所述之完整「詩事」以作分析,內、外考證兼用,以史證詩、以詩證史與及以詩證詩交辯,「史事」與「詩事」互證,然後析而解之、詮而釋之,庶幾猶可有得。
我讀論者對諸詩之分析與詮釋,常覺得他們大都在對「史事」乃至「詩事」未求甚解之前,即對事情及其意義逕予論斷或詮釋,以故對諸詩不僅迄無定解,而且爭議叢生。此詮詩方法上的缺憾,縱使前人深於文史者如王安石與司馬光等大家亦然。我在新亞研究所之所以選曹詩為題撰寫論文,正由王、馬二人酬唱〈明妃曲〉所啟發。按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大意勸王昭君不要再年年思念漢朝與家人了,因為「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所以應該珍惜當下;但是昭君之去國,在胡真的快樂嗎?司馬光讀後,作〈和王介甫明妃曲〉,持論大唱反調,大意謂漢主要昭君「和番」是出於傷心無奈,因此她即使不能適應胡俗,在胡中不樂,欲有「終期寤人主」之心,然而還是要勸她效法「被讒仰藥更無疑」的太傅蕭望之,對人君應該忠心與服從。不過,昭君在胡中的孤寂以及不適應,溫公能體會嗎?夜靜一再誦詠,復覆按兩《漢書》,覺得二子不免忽視史實以及昭君的自主感受,未必得到昭君無辜入宮而負氣去國之意,遂代昭君草作〈答明妃曲〉以奉和,於今猶記得其辭略云: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衫鬢腳垂;縱然惹得帝驚看,落得清談飯後餘!
誰憐弱女氈城泣,此去空然無所得;夫子非愛兒非類,日夜思親徒焦急!
不意荊公開金口,作曲勸妾休回首;君在上邦奈妾何,為君再撥春風手:
身屬荊州南郡城,長在民間已娉婷;孰料天子春念動,虛度清秋掖宮庭。
入得禁內已無言,盼望君王垂眼憐;不意畫像看來醜,當時恨無十萬錢。
桓桓單于覲元首,馬躍龍騰京師走;漢家君臣齊失措,贈與侍女結長久。
去國心知難有為,嗟歎天漢世運低;遂教泱泱大國女,嫁了單于嫁若鞮。
此事焉能向誰語,君教妾身如何處?失意果然無北南,付與梨花春帶雨!
野闊天高兩茫茫,風吹草偃見牛羊;年年目送鴻雁歸,唯託琵琶訴衷腸。
幽咽難得留至今,後人不識前人心;出塞逸調唱千古,冷寂那堪告知音。
滄桑彈遍世人知,豐容靚飾不可恃。若能締結真緣份,天大幸福莫遲疑!
君不見乎:
玉環飛燕皆塵土,西施與妾已荒槁;縱然嬌豔動天地,到頭仍然難討好!
或許我也未得昭君之心,然而漢女不易適應胡人生活文化,卻可從蔡琰〈悲憤詩〉中體會。要之昭君的入宮去國、赴胡和番、夫死嫁子,以至親生子因非純種而遭排斥,最後被殺,在在束縛而無自由可言,其事尚可按諸史傳。不先究明其情其事即予論斷詮釋,則所言之志、所述之事終將有誤,可以無疑。此所以我對〈孔雀〉、〈木蘭〉兩篇,仍必須贅證其詩文所述之「詩事」也。
《禮記.經解》述孔子之言,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余素性急切,雖遍讀眾詩,但猶無得於詩教之化;只是若非好詩,則恐怕急切尤甚於今!余為二兒取名為中行、中和,典出《論語》與《中庸》,蓋盼吾兒毋效其父,而亦以自誡也。是為之序。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9折$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