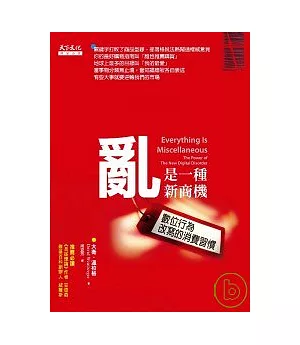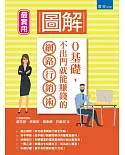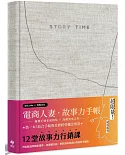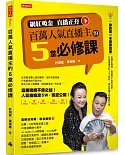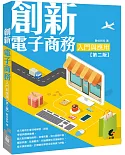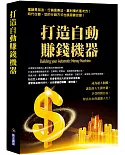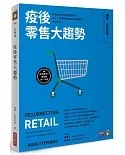序曲
空間裡的資訊
「絕不。」
顯然,我一開口就問錯了梅迪爾(Bob Medill)問題:「你難道不會把銷路最好的商品放在後面嗎?」他可能會覺得這個問題是在侮辱人,因為這是許多零售商故意與顧客做對的銷售伎倆,強迫消費者得穿梭過商家希望他們因一時衝動而買下的一些商品。然而,語氣溫和的梅迪爾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以前也有人問過他同樣的問題。而這是個菜鳥級問題。
「我們不會那麼做,」他看著他管理的史泰普(Staples)辦公文具店說道:「店面前方擺的是重點商品,因為這些是顧客說他們想要的東西。」他舉起手臂,由左而右依序點名位於商店迎客面的重點商品區:「紙張、數位影像產品、墨水匣和碳粉匣、事務機和影印區。」
當時是下午兩點,但是整個店裡就只有我們倆。即使有顧客上門想買些什麼,收銀台也不見半個人影。如果你需要購物上的協助,也找不到任何一個「夥伴」(史泰普內部對「店員」的稱呼)。梅迪爾並不擔心。因為這裡本來就應該如此。我們所在的地方是麻州佛拉明罕市(Framingham)某個辦公室園區裡的史泰普總部,這裡是他們的「雛型實驗室」(Prototype
Lab):一個和真實的史泰普商店一模一樣的模擬商店。
這裡可沒有任何電影布景。現場都是如假包換的真品,從標示特價的24磅紙到整齊並排掛好的透明包裝筆,各式商品一應俱全。這裡有八名全職員工,雖然少於真實商店典型的29人完整編制,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這些都是值得的:儘管現場可以看到一排排的筆類展售架和得用堆高機定位的置紙棧板,雛型實驗室其實和「資訊」有關。梅迪爾和他的手下每天都在研究突破實物和空間限制的策略,好讓顧客在瀏覽史泰普商店時,就像在瀏覽純資訊。
梅迪爾還有另一種看法。從他的觀點,雛型實驗室是如何讓顧客在史泰普更簡便購物的測試場。這是他成為零售商先鋒的武器。較典型的零售商會利用實體空間對付顧客,好讓顧客的花費超過原來的預算。零售商都深諳此道。超市會把牛奶和香蕉等熱賣商品放在店面後方,藉此利用實體空間的運作法則:讓你從A區到C走道必須經過B貨架,而那裡剛好有張海報寫著,某項原本不是你這趟打算要買的商品,現在正在打折。同理,狗零食所在的貨架位置會低於目光水平線,因為這是小孩比雙親更常放進購物車的商品。現在,梅迪爾卻談論著如何讓史泰普的顧客能更容易、更快速走出商店,彷彿是個以「誠意販售」為職志的革命家。
「顧客有兩種,」史泰普視覺陳列設計主任麥高雯(Liz
McGowan)說,「一種羞於開口求助,另一種則不會。」而和一般印象不同的是,這兩種顧客的區隔並不在於性別。麥高雯就說:「我媽媽是第一種人。」麥高雯熟知數據,所以她知道各種顧客的確切比例。「32%會詢問店員。24%會看指示牌。而本來就知道東西在哪裡的人則有40%。」店內的資訊陳列就是為了那60%需要幫助的人而設的。雛型實驗室稱之為「找路」(wayfinding),這是人類思考如何讓人體因應空間需求的交會點。
梅迪爾說:「我們是透過觀察顧客的視線來學習的。」顧客一上門,會先朝店頭裡走個9到12呎,然後他們就在那裡「站著掃視」。而這是為什麼史泰普不像大部分的商店會在入口處放太多指示牌的原因。史泰普反而會在最熱門的商品區放置海報,並在海報上列出次類別,就好像一張會進一步區分出各國、各州的地圖。梅迪爾指著設計簡潔的海報說:「一開始我們也會製作『聚焦點』」,這就是指那種寫著促銷訊息的醒目海報,「但是它們會妨礙視線」。在零售業,「聚焦點」的作用是打斷商店的邏輯順序,要你注意到一些出乎意料之外、但卻不能錯過的促銷商品。但「聚焦點」也是實物,因此不但攫取了你的注意力,實體上也遮蔽了商店資訊,這就像是在地圖上貼一張「麥當勞在這裡!」的標籤,會讓你忽視市區其他大部分地方的資訊一樣。這就是視覺的運作方式。看不到的海報不算資訊,因此貨架高度取決於人類視線的平均高度。梅迪爾說:「商店內的陳設如果大多置於低矮處,就易於掃視。」
視覺也決定了貨架上的產品標示牌要放入多少資訊,它們是商品自我介紹的名片。麥高雯解釋道:「左右眼視力2.0的人,也得在距離一呎半時才能讀這些標示,」她補充說:「因此標示內容條列三點還可以,五項就太多了。」人類的視力要是能好一點,標示牌就可能容納更多資訊;人類要是能混點長頸鹿的基因,貨架就可以有20呎高。貨架要是可以有20呎高,一家典型的史泰普商店就可以存放1萬5千件商品,而不是7,200件。但何必做這種白日夢呢?實體商店的陳設就是為了服務視線不超過離地六呎的人類。
在實體商店,接觸資訊的難易程度可以用計步器來衡量,每一步都彌足珍貴。「上門顧客來找印表機墨水匣的方法林林總總,」梅迪爾說,「有拿著舊墨水匣來比對的,也有從墨水匣貨號、印表機型號、包裝盒標籤著手的。」史泰普原本編製了一本包含各式印表機墨水匣的目錄,擺放在賞心悅目的專用櫃台,但卻只有7%的顧客用到它。「因為目錄的位置離墨水匣太遠了,」梅迪爾解釋道,「我們現在則把目錄拆開,搭配各項相關產品擺置。」如果你的印表機廠牌是愛普生(Epson),你會在墨水匣貨架的愛普生區旁邊看到該廠的墨水匣目錄。數字專家麥高雯說:「我們整合了目錄與產品後,使用目錄的顧客增加到20%。」
在實體世界裡,「兩樣物體無法同時占有同一個空間」,這個鐵一般的事實扭曲了雛型實驗室純粹提供資訊的陳設方式。我們在空間裡陳列物品時,也決定了拿取它們所需的時間。如果實體世界的這項根本定理要是消失,雛型實驗室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當然,我們可以想辦法把某項商品同時擺在店裡的許多地方。但是包括史泰普在內的大部分商店都不樂意那麼做。莫倫(Mike
Moran)是該公司負責推敲空間關係的人員,我要他說出一項會同時放在兩處以上的商品。他不假思索回答:「纜線。」他從消費者的觀點說:「纜線是用來做什麼的?連接印表機。」於是,纜線就和印表機放在一起,同時也放在獨立的纜線區。依照同一個邏輯,空白光碟片也應該同時陳列在許多地方才對,可是它們卻只出現在靠近梅迪爾所說的商店重點商品區邊的展售櫃。光碟片為什麼不和可以燒錄光碟的機器放在一起呢?既然光碟和紙都是紀錄的媒介,為什麼它們不放在一起?此外,既然軟體也是用光碟片販售,為什麼它也不與空白光碟片放在一起?同理,筆為什麼不和紙、筆記本、便利貼或空白標籤放在一起?莫倫說:「這是為了精簡營運。」
同時,如果在顧客希望找到光碟片的所有地方都放光碟片,商店就不可能確保每處的光碟都不缺貨。此外,這麼做會吃掉貨架空間;「貨架空間」是雜貨店和書店的「限量商品」,銷售商甚至要付費才能讓貨物排在較佳的貨架位置。重點商品區是唯一會出現重複擺設的地方,莫倫說,因為「如果顧客出店門時帶了印表機,卻沒有把纜線、紙張和墨水匣一起帶走,印表機還是不能用,最後他們就得氣急敗壞再跑一趟。」
「不得不再跑一趟」就是空間和時間的勝利,它戰勝了人類對事物關聯的記憶力。第一趟丟三落四而不得不跑第二趟時,許多人會冒起一股無名火。我們之所以會丟三落四是因為商店所呈現的資訊空間無法幫助我們聯想。但資訊很好解決。空間、時間和實物才難搞定。
梅迪爾的員工不這麼想,不過他們正陷入苦戰。實體的三度空間世界是他們不斷纏鬥的敵人。用軟體的話來說,雛型實驗室的人員在「駭客入侵實體世界」,他們想找出突破這種系統內建限制的妙法。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這些限制早已習以為常,甚至沒想過它們是種限制:實體空間裡的物品有遠近之分。這就是麥高雯要煩惱「找路」這件事的原因:她希望顧客能夠走最短的路,找到購物清單上的所有東西。
實體物品在任一時點只能放在一個地方。儘管對顧客而言,所有想要的東西都能伸手可及是最便利的,麥高雯和莫倫還是必須決定一個(最多兩個)商品陳設處。
實體空間會被物品瓜分,因此儘管顧客有不同的個人需求,店面擺設還是只有一種。如果你是輪椅人士,麥高雯精心排列出的適合一般身高顧客的標示,對你可能就沒什麼用處。如果你去史泰普主要是為了採購學校文具,你可能會覺得重點商品區裡的商品根本沒抓到重點,因為那裡既沒有蠟筆,也沒有「哈利波特圖案」三孔筆記本。
人體各項能力有限,呈現在眼前的資訊會受限於人的視覺能力;所以店內資訊標示不應該詳細到搶走商品本身的分層。店面擺設必須整齊有條理。放得亂七八糟的商品會讓人找不到;商店的實際陳設必須反映資訊的編排,編排方式必須盡量簡單。混亂的商店不但會失序,也會失敗。
以上這些限制意味著,不管梅迪爾和他的員工再怎麼盡職,史泰普商店裡的大部分事物就是會讓顧客覺得礙事。
如果我要上史泰普買15樣東西,商店裡的其他7,185項商品不但無關緊要,甚至還遮擋了我想要找的東西。我登門購物時,史泰普如果能很神奇的只擺出我要的那15樣東西(而且不管我哪次光臨、買的是什麼東西,它都能這樣),我就能走到店面前方的貨架,把我要的商品全部掃進購物籃,一次搞定。這麼一來,麥高雯根本不必鑽研什麼「找路學」,莫倫也不用精心推敲商品的排列順序。
既然我們都明白現實世界的運作法則,為什麼還要去想這種只可能發生在某個另類科幻世界的事呢?
因為,這個另類科幻世界真有其事。而且每過一天,我們就愈來愈常生活在其中。它叫做「數位世界」。
數位世界沒有占據空間的物質原子,而是由位元組成。
數位世界沒有長長的走道,只要點幾下滑鼠,所有東西都唾手可得。
在數位世界裡,商品的陳列不必一成不變,而且能夠依照個人喜好和個人當下的需求重新排列組合。
數位世界不受空間限制,也不受限於陳列商品項目的精簡營運原則,它能容納史泰普各式各樣的顧客可能想要的商品。
在數位世界裡,商品的陳列不必固定放在店裡某一區、偶爾可增加為某兩區,而且是可以歸入使用者認為應該可以找到它們的各種類別。
在數位世界裡看不到雛型實驗室裡井然有序的貨架,商品可以用數位形式隨意放置,在使用者需要時按照個人想要的搜尋方式整理排列。
以上是數位世界和實體世界的重大差異。不過,這些只是起點,它們還涉及了比店面陳設更重要的事。實體限制無聲無息的引導了辦公文具商店的陳列方式,也引導著企業、政府和學校的組織方式。
實體世界的限制更引導著(也限制了)我們整理知識的方式。從管理架構到百科全書,還有孩子接受的學習課程,甚至是對什麼事物值得相信的取決方式,我們都是根據受制於物理定律的世界而設計的原則,來組織我們的思想。
試想,現在是有史以來頭一遭,我們能夠在規避實體內隱限制的情況下組織概念。我們的思想、組織和知識會有何變化?這趟旅程將帶領我們走出亞里斯多德的世界,轉而拜入柏克萊大學裡一位性格沉靜、推翻了亞氏世界觀的心理學教授門下。我們要告別想方設法為生物分門別類的科學家,而去迎接那些認定資訊愈雜亂就愈容易搜尋的事業。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編纂者按照字母順序編排主題,卻因此被扣上「違反上帝所定秩序」的罪名;現在,我們就要來見識一下,世界上第一部沒有編輯群、沒有頁數限制、甚至沒有順序的百科全書。
欲知旅途究竟,這裡先提供一條線索:就在我們發明了新組織法則,以適用於這個不受實體限制的知識世界時,資訊自由是不夠的,資訊還得「雜亂」(miscellaneou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