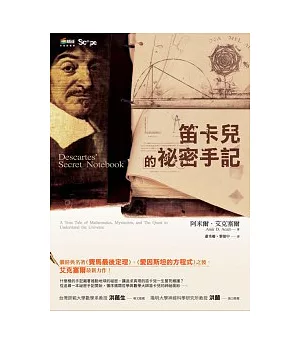理性與神祕交織的「笛卡兒」
洪萬生
無論數學史或科學史如何敘事,笛卡兒(1596-1650)無疑是十七世紀人類理性展現的典範!如此說來,為什麼本書作者AmirD. Aczel 企圖探索他與神祕主義(mysticism)的關係呢?
我最初認識笛卡兒,本來就是再「理性」不過的事。首先,他與費馬(Pierre de Fermat, 1601-1665)彼此獨立地發明了座標系統以連結幾何與代數,而開啟了今日高中學生所熟悉的解析幾何學。然後,在論述近代科學(modern science)興起一類的科學史著作中,我還進一步發現他的重要性經常與英國的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並列,他們兩人都為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提供了新的思想架構與研究進路。
這個全新的思想架構,就是所謂的「機械(論自然)哲學」(mechanical
philosophy)。其中,笛卡兒主張心物二元論(dualism),將實在(reality)嚴格區分為精神與物質兩種實體。此一結論應該源自他有關肉體功能之研究,譬如他發現動物並不擁有推理力與思考力,因此,動物只不過是缺乏智力與靈魂的機械,從而肉體(body)與靈魂(soul)各自存在,而這當然與文藝復興時期的靈肉一體之主張,徹底決裂了。科學史家Richard
Westfall說得好:笛卡兒「從物質本性剔除精神的每一絲痕跡,留下一片由惰性的物質碎片雜亂堆積而成、沒有生命的疆域。這是一個蒼白得出奇的自然概念,但是令人讚嘆的是,它卻是為近代科學的目的而設計。」
事實上,笛卡兒所以發現靈肉之別,應該是基於「我思故我在」這個真理。他說:「我知道,我能設想『我』沒有肉體,也能設想沒有宇宙存在,連『我』處身的地方都不存在,可是,我不能同樣設想『我』自己不存在;相反地,正因為我思想懷疑別的事物之真實性,很明顯地,很確實地結論了『我』的存在。」而「這個我,即靈魂,是我之所以為我的理由。他和肉體完全不同,也比肉體更易認識,而且,假使肉體不存在了,仍然不停止他本來的存在。」
同樣地,基於「我思故我在」,笛卡兒也推得「明顯」與「清晰」是任一命題所以為真的標準。他注意到:「在『我思故我在』中,無物可以保證我說了真理,只不過是我很『明顯』地看出,思維必須存在。我遂認為我可以以此作為總則,凡我們很明顯地、很『清晰』地對它有觀念之物,皆真實不誤。」顯然,笛卡兒通過系統的質疑,對每一種思想進行嚴格的檢驗,只要稍有不可靠之處,即加以排斥,直到獲得命題為止,這樣得出的命題,當然就不能再懷疑了。於是,在這樣的確定性基礎上,笛卡兒重建了一個僅僅依賴理性所建立的知識典範,為科學革命世紀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哲學架構。說得明確一點,正如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為他自己的宇宙論與物理學提供一個思想框架,笛卡兒的機械哲學也為他自己的科學研究乃至於牛頓物理學的偉大綜合,貢獻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思想憑藉。
上述這些,都出自笛卡兒的《方法導論》。其實,該書題名還包括「正確地引導理性並在科學中尋求真理」。這也解釋了此書三篇附錄〈折射光學〉、〈氣象學〉與〈幾何學〉之目的,因為笛卡兒利用它們展現了一般性思維之力量。以〈幾何學〉為例,笛卡兒所以引進座標概念,是希望我們在代數與幾何結合的基礎上,得以擺脫幾何圖形的束縛,並發揮代數符號的一般性(generality)力量。他認為「古代幾何與近代的代數,除了限於談論一些很抽象的問題外,似乎沒有什麼用處,前者常逼你觀察圖形,你若不絞盡腦汁,就不能活用理解力;後者使你限於一些規則與符號的約束之中,甚至將它弄成混淆含糊不清的一種技藝,不但不是一種陶冶精神的科學,反而困擾科學。」基於此,他所提出來的數學方法,就是想要達成下列兩方面的目的:一、通過代數的運算過程(步驟),將幾何從圖形的限制解放出來;二、經由幾何的解釋,賦予代數的操作運算意義。於是,代數與幾何從此可以合成一體的解析幾何,緊接著微積分相繼問世,數學的發展也就一日千里了。
不過,誠如Aczel所指出,笛卡兒不僅可能曾經參加一個祕密團體「薔薇十字會」,他的的《方法導論》也一再地出現與「神祕」有關的主題。在該書中,他還提及已經為某一個問題找到重要的「解決方法」。至於這個問題,就記錄在他的祕密手記之中。然則這一份總共有十六頁、由神祕的符號所構成的羊皮紙手稿,究竟有什麼驚人的發現,以致於笛卡兒終其一生不敢公諸於世呢?
這一個謎底直到本書倒數第二章(第二十一章),作者才為我們揭露。原來笛卡兒所發現的,就是用以刻畫多面體的頂點數(v)、稜線數(e)與面數(f)之關係的「尤拉公式」(Euler’s formula):v+f-e=2。由於利用此一公式,吾人極易證明只有五種柏拉圖多面體(Platonic solid)存在,而這五個正多面體,則與克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的宇宙模型直接相關。後者的宇宙論當然基於哥白尼學說,因此,笛卡兒若公布此一手稿,則可能被認定支持哥白尼學說,而遭遇如同伽利略一樣的宗教審判。我們不要忘了他臨時抽回《世界體系》之出版成命,此一恐懼陰影永遠如影隨形。儘管如此,Aczel還是認為笛卡兒的謎樣死亡與此有關。
總之,這是一本相當引人入勝的笛卡兒傳記!在高舉「理性」大旗的同時,作者Aczel運用了極成功的敘事手法,讓我們見識到笛卡兒知識活動的「神祕」面向。這種對比,不僅交織了笛卡兒一生的哀愁行旅,也見證了近代科學「理性」的複雜風貌。相對地,我在前文中絮絮叨叨地轉述了笛卡兒的機械哲學,彷彿複製了本書的手法,非要「賣關子」到底不可!不過,讀者大可跳過,好好欣賞本書的故事情節就行了。其實,本書的數學知識之實質內容,幾乎已經減到非常輕薄的程度,因此,作者的貼心「普及」考量,當然不在話下。儘管如此,有鑑於「柏拉圖」的重要性,我還是建議讀者培養一點好心情,細心研讀本書第十五章的所謂「提洛謎題」,如此,讀者或可體會柏拉圖數學哲學的源遠流長了。
(作者現為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