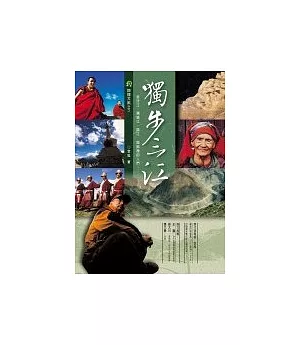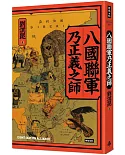推薦序
淨土一瞬────我讀《獨步三江》的一點感想 文/張大春
先說一個人,我的朋友周慶輝。他是專業的報導攝影家,經常要走南撞北,去來於兩岸之間,往往在闖訪行腳之餘,也用一閃一閃的快門攫取了值得珍視而往往被人輕忽的「人生一瞬」。近年來周慶輝每一次出門、返家或者是策劃開展,都會跟我提到另一個人:李旭。我跟李旭只見過一面,但是因為周慶輝的緣故,卻像是認識了很久的老朋友、老鄰居,感覺他經常造訪我的家、出現在我的面前。更有趣的是:一旦再回頭讀他多年來幾度穿行於三江並流區域的報導文字,更有一種亦步亦趨、跟著他往訪絕嶺叢山的親切之感。
李旭是第一批橫越三江並流區域的人,在這片一百七十萬公頃的土地上,非但有大自然巨力所扭塑的獨特地形,還有歷經無數歲月而鑄就的族群融壚,李旭用平易的文字、天真的熱情所做的每一頁記錄都勾動我「出發」的情緒,也時時令我想起自己年少時背著相機,到全省各地閒逛的旅行。
本質上就是閒逛──毋寧視之為一門深奧的學術;一次又一次進入他鄉,和生老於斯、繁衍於斯的住民交心接觸,體驗完全不同於現代社會一切資源及消費體系的人生和文明。李旭是個單純澄淨的人,這樣一位稱職的導遊可不只是提醒我們:世界上有這三江並流地區這麼一個已經快被世人遺忘的桃花源,他還示範了單純澄淨的好奇心,有助於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從近年來朝朝暮暮不可須臾離之的爆料文化中抽身而出,看一眼遠方遼闊的世界,還有乾淨的人間。
***********************************************
前言
徒步絕非我所擅長,但由地球上的一個點到另一個點之間,我最喜歡的交通方式還是步行。腳板踏在大地上總有很實在的感覺,這符合我的天性。而且,步行這種最原始的交通方式,使我得以最為充分、最為細緻地觀看我們這個世界,並深入我們這個世界上各種人群的各式生活。它沒有慢到讓你失去注意力,更沒有快到使你看不清一片樹葉的紋路和一隻蜻蜓的顏色。步行還便於你傾聽,既可以聽見各種動聽的鳥鳴、溪流的話語,以及變幻莫測的風聲和地球轉動的颯颯聲,更可以聽見自己的呼吸和心跳,甚至可以聽見血液在自己血管?流動的聲音。最重要的是,步行使我得以跟各色各樣的百姓老鄉親近。他們絕大多數時間也是用雙腳來縮短地球上的距離,接近賜予他們食物的土地,親近他們想親近的人和物。
從1986年起,我就在現在所說的三江並流地區行走了起來。當時連「世界遺產」這一名詞都沒聽說過。
大約四千萬年前,也就是恐龍在地球上滅絕之後,印度大陸板塊向北漂移,緩緩地衝擊碰撞到歐亞大陸板塊上,於是青藏高原從亙古汪洋?隆升,並高聳雲天成為世界屋脊,與此同時,青藏高原東南部邊緣的地殼被強烈擠壓扭曲,在地球上形成了幾道巨大皺褶,那些本來東西橫亙的大山忽然成了南北縱走的橫斷山脈,緊緊將發源於唐古喇山和喀拉昆侖山的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條大江夾住,形成了山高、谷深、水急的「三江並流」壯麗景觀。
四千萬年後的2003年7月,三江並流區域約一百七十萬公頃的大地、雪山和江河列入了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在地圖上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一片巨山大江縱向密集的獨特區域,在這?,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條大江之間最近的直線距離僅66公里多一點,而怒江與瀾滄江相距最近點不到19公里。三條大江之間為雲嶺山脈和怒山山脈分隔,又為高黎貢山等大山所挾持,擁有得天獨厚的地質地貌和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於是成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天然摹本。
完全出於巧合,或者說出於命運的眷顧,我早就分別走過這幾條大名鼎鼎的江河,甚至多次到過它們遠在青藏高原的源頭上游。它們的歷程、它們的故事都歷歷在目,匯集心頭。除了我的家鄉以外,三江並流這一區域大概是我走得最多、最勤的地方。有的地方我踏訪過不只五、六次,有的地方則生活過一年以上的時間。無論是從感情上還是從人生歷程上,我得說這就是我的第二故鄉。
屈指算來我已經在三江並流地區行走了近二十年。二十年相對四千萬年來說不過是滄海一粟,對我來說卻是短暫一生中最為寶貴的四分之一時光。我不會再有這樣的二十年了。我之所以在三江並流地區流連忘返,並把它書寫和攝影下來,並不因為它是世界遺產,而是因為我在這?所花的時間和度過的青春歲月,因為我與它之間建立的特殊關係。它幾乎耗盡我所有的熱情。
2003年秋季,在這一區域剛剛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之際,我曾經一口氣橫跨過它們。在以往,從最早的原住民到往這一帶逐漸遷徙的各民族先民,到後來各區域間的經濟文化交往,直至現代的公路交通,無一不是沿那南北走向像一個巨大「川」字的河谷或上或下,絕少有橫著走的。要橫著跨越過去,就意味著翻越橫斷山脈的幾條海拔超過4000米的山脊,也就是幾條大江各自的分水嶺,在二、三天的短短時間內,經歷從海拔1000多米到4000多米再到1000多米的落差,經歷春夏秋冬四季,經歷多個民族各不相同的生存區域,經歷多種文化的陶冶和洗禮……
那正是我喜愛的。我想不出還有比這更有意思的生活。這二十年來,行走已成為我的生活方式。也許是我那來自大山深處的心靈,也許是城市的日益擁堵、熙攘和喧囂,召喚我、迫使無所適從的我一次次回歸大山深處。注目大江大河的狂放奔騰,遠眺白雲的自由飄逸,讓我難以忍受現代文明的物欲橫流;凝視雪山的純淨偉岸,與純樸的山民無礙交流,更令我無法面對塵世的污濁混亂、烏煙瘴氣。現代人類似乎已經失去用簡單美好的東西來建構人生的能力,那些美好的東西只有在僻遠的大山深處才能找到。
我是個低調消極的人。生活中許多被人們視為人生樂趣的事我幾乎都不會,也從不將之作為樂趣。有時候我自己都納悶,我怎麼能如此有滋有味地活下來呢?這大概應該感謝世界上還有三江並流這樣的地方。在我年輕走得動的時候,還有那麼些沒被現代謀殺破壞的地方供我行走。今天的三江並流還沒有死亡,她的江河沒有被大規模污染,她的空氣還是那麼清新,她的動物還沒有滅絕,她的植被還那麼豐茂,那些鑲嵌在山水間的木舍土屋仍那麼親切而溫馨,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仍那麼溫和善良友好……,三江並流的勃勃生機似乎是一個人好好活下去的不錯理由。
許多人正在遠離自然和生活的本真。幸好我還有選擇的權利,幸好我還能按自己的意願和愛好去度過自己的人生。我願意跟更廣大的自然並行不悖,而不願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所謂的潮流或什麼「化」,更不願意改變自己,成為那潮流中的弄潮兒。我知道我太弱小了,我天性缺乏追趕和融入這個世界的能力。所以我只能依託山川大自然,或深入那些似乎比我更為弱勢的人群之中,獲得人生的美感和幸福。
我靈魂所求、快慰所寄的,就是那不被阻攔的江河,那清新的空氣,那聖潔的雪峰,以及藍天白雲下眾生的樸實人性。
我筆下、鏡頭中觸及的地方當然都是我的步履所及之處,涉及的內容都為第一手所得。我關注得更多的,是這一區域?獨特的人文風貌。要是沒有了生活於其間的人,三江並流就只是一個純自然的殼。我知道,三江並流是以其自然特性而獲得世界自然遺產的冠冕,但我更以為,正是這一區域突出獨有的自然風貌,養育並塑造了這?各民族豐富而奇異的人文性格。這?更有許多值得大書特書的東西。我想表達的僅僅是我的行旅途中所遭遇的現實,它們是客觀的、豐富的、切實的,有時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令人恐懼、令人憂慮的。它們有時顯現出美好的一面,有時又顯得令人痛心疾首。
也許,正如莎士比亞所說:「生命不過是行走的影子。」可我還是有一種本能的衝動:把這影子記錄下來。所以我同時也將相機鏡頭聚焦於我「行走的影子」。儘管文字是我半生以來學習和致力的主要方面,但我向來認為,有時候影像的力量大於文字。蘇珊‧桑塔格就說過:「攝影在決定我們對事件的記憶方面具有不可抑制的力量。」這十多年來,我在握筆的同時自覺地拿起相機,力圖以影像的力量來加強我對三江並流區域的印象和記憶。這不僅僅出於愛好,更是一種需要和責任。影像也許能為我們保留下更多的東西,使它們不至於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大自然用異軍突起的橫斷山脈將這三條大江安排在一起,我則用不斷跋涉了近二十年的步履、用我的文字和照片,將世代生息在三江流域的人們的生活串聯在一起。它們是那樣的異彩紛陳,但又有根本相通的東西。那些最樸素、最鄉土的東西,或許就是某種啟示性的智慧和稍縱即逝的福份。我的書?記述下了那些人類先民史詩般的歷程和早先在這一帶活動的人們的傳奇故事,我更寫了些尋常百姓的人們,他們為了每天的生存而鎮日辛勞,而與那巨山大川融為一體。我之所以要寫他們,是因為那些傳奇人物的事蹟本來就可歌可泣,只不過淹沒在了江河的洶湧聲?,而那些普通小人物,除了我,沒人問過他們的名字,沒人記得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活過,他們的生存應該有人講述。
山野似乎亙古未語,其實它們的呼吸和歌唱只是沒有被人們聽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