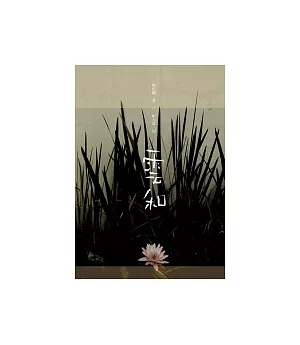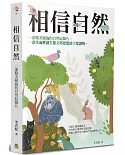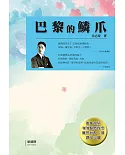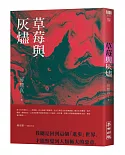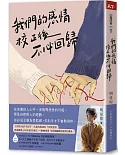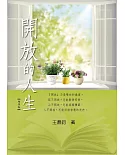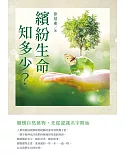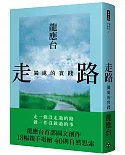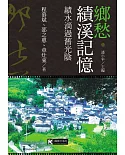心結
在紐約地圖中,自由女神和世貿遺址同樣名聲顯赫,但兩者形成強烈對比。很多遊客決定不要去看非看不可的自由女神,是因為很明白排隊膜拜那座雕像是找罪受──自由女神是不關痛癢的。很多人知道九一一事件現場承載歷史意義,卻偏偏迴避不想去看,是因為他們覺得廢墟召喚太多痛苦──世貿現場是牽引痛癢的。自由女神已經徹底商業化,像風景明信片一樣扁平,卻不再立體。世貿遺址卻是立體的,是人心裡的一個疙瘩,疙瘩裡糾結了神經線,沒有辦法乖妥收納在明信片裡頭。這個疙瘩是一個「心結」,在九一一之後重新定義了紐約的地圖。
剛才提及的世貿遺址,是心結的極端例子。我們日常遭遇的心結,不至於這番驚天動地,不至於這般全球化,反而還可能帶有一點甜蜜。
人都說,心結宜解不宜結。又說,解開心結,就是海闊天空。
可是我想問,人生怎麼少得了心結?又,一旦海闊天空,人心又將空懸何處?恐怕我們就是因為有心結,才有足以安身立命的支點,才得以抵抗向下拉扯的萬有引力。
許多人心裡,都有心結的場所。例如,故鄉的母校──初戀,體罰,模擬考,青春期,都在那裡發生。有些人每次回到故鄉,就一定要去母校走走,故意去看看;有些人卻一定要繞路避開母校,故意不去看。心結可能是甜美的,也可能是痛苦的。不管心結的場所被珍愛,還是被憎惡,此等強烈的愛憎情緒,都証明了心結有多要緊。心結的場所,是數學中X軸Y軸交叉的原點;有了原點,才畫得出座標體系。於此,我們才知自己身置哪一個座標格子裡,才覺得踏實。
對於心結的想法,並不是我的創見,而是讀了雜書之後的心得。有些心理分析學者認為,七情六慾是滑溜的,難以捉摸,就像是失手散落一地的鈕扣,或是斬不斷理還亂的絲線。然而,如果將絲線穿過鈕扣,緊緊縫住,打成一個結──即英文的「button tie」,法文的「point de
capiton」──那麼,這個結就馴服了絲線、鈕扣,變成沙發正中央或是襯衫袖口的一隻眼。這個結,就算終有一日被人笨手笨腳扯掉,畢竟可以讓情緒暫時塵埃落定。
這個結,讓人心的牽掛有所寄託──我譯作「心結」。心結是一支大頭針,可以把一張地圖釘在牆上。如果大頭針掉失了,牆上的地圖也就垮下來。
我談心結的地理面向,因為楊佳嫻的散文集《雲和》強烈展現了地理感。在跨國主義盛行的年代,台灣的咖啡館,德國的麵包店,以至於書名的「雲和街」,都是楊佳嫻的心結場所。佳嫻書寫愉悅的心結,是一支支大頭針,使得她的不規則形狀地圖得以張開伏貼在牆壁上。她手上的大頭針不只一支,因為她興致勃勃,要釘住的國度不只一個。
心結當然不只在地理場所發生。地理場所匯集了我們的情緒,往往是因為場所吸足了人的氣味。因為某些人,所以我們才在乎某些場所。既然有心結的場所,當然更有心結的人物。可以想知,最符合心理分析典型,也最符合台灣社會實況的心結角色,就是父母,或是「父親形象的人」、「母親形象的人」。無數的人早已坦承,他們之所以決定在學校攻讀某種學科,是為了迎合父母∕激怒父母。有些人說,他們寧可漂泊異鄉也不要回國,就是為了要迴避父母。有人終生試圖做出父母拿手的私家菜,卻也有人打死也不去父母愛去的飯館。很多人(故意,或不小心)找到的情人,偏偏吻合自己父母的形象──這已是老生常談。
不論父母是被愛的心結還是被恨的心結,我們都走不出心結的影子,無法遁入想像中的海闊天空烏托邦。正是因為有了心結,我們心中才畫得出一張地圖,我們才知道該將情緒投注在何處。心裡有了心結,我們才有試做私家菜的動機,才有漂泊異鄉不回頭的決心,才有抵抗或順應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動力。如果少了心結,我們的愛憎就失去了支點。
心結的場所,心結的人物,雖然可以引起當事人的強烈情緒,但是這些情緒很難「轉譯」給旁人體會。畢竟這些情緒根植於個人的成長記憶,不足為外人道也。芸芸眾生的心結場所是私人獨享的──例如一家尋常無比的小酒吧、一面牆上的普通塗鴉。如果不是當事人,在面對無可數計的小酒吧和塗鴉時,恐怕一點情緒也感覺不到,反而只看見平庸的浮面。然而有心結的人,卻可以看穿平庸的浮面,按中自己的麻穴。如果能讓旁人也看透日常生活而?中穴道,就需要工夫。
書寫私己的心結,不易引起讀者的同感。容我再提一次老生常談的普魯斯特軼事: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說,他鍾愛瑪德蓮貝殼狀蛋糕,因為他在品嘗這種蛋糕時,就會回返他美好的青春歲月。也就是說,瑪德蓮蛋糕是他的心結物件。這種心結物件已經成為文學愛好者的流行商品,甚至在文學不愛好者之間也享有市場:一代代的消費者食用這種蛋糕,企圖體會普魯斯特的私己快感。
楊佳嫻的散文集突顯了心結的場所,也埋藏了心結的人物。這些心結人事物,都根植於極個人的經驗,但是楊佳嫻卻有辦法將她的一顆一顆心結鮮活推介給讀者。這是她的大膽,也是她的大方。讀完這集散文之後,我竟也蠢蠢欲動,想要回頭檢視我自己的種種心結──為什麼我老是惦記加州的某一條高速公路?為什麼我想念新英格蘭鄉間小路的某一棵樹?為什麼我──一個在台北長大的人──卻已經鮮少回去台北看看?為什麼曾經在台灣大學念大學和研究所的我,幾乎再也不曾走進台大校園?不過,在自省之前,我想先去尋覓最正統的德國麵包,不然已經被蠱惑的我會耿耿於懷。
紀大偉∕台灣大學外文系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居美國東北角的新英格蘭鄉下。著有小說集︽膜︾等,曾獲聯合報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