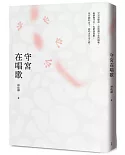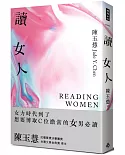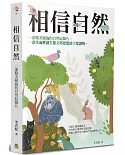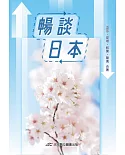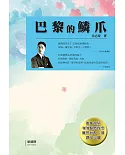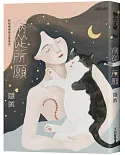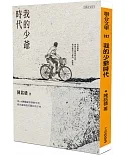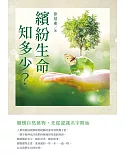我在劇團被管制多年,喪失人身自由的日子也是從劇團開始,可算得嘗遍酸甜苦辣。然而,舞臺和藝人始終是吸引我的,這吸引力還很強烈:看了電影《霸王別姬》,自己就想去編個“姬別霸王”;讀了小說《青衣》,也想去學著寫個中篇。連題目都想好了,叫“男旦”。
過去看戲是享受,是歡樂。而這些自以為享受過的歡樂,現已不復存在。如今所有的文化都是消費,一方面是生活走向審美;另一方面是藝術消亡。當然,我們的舞臺仍有演出,演新戲,演老戲或老戲新演,但大多是期待而去,失望而歸。中國文化傳統與革新之間的斷裂,在戲曲舞臺和藝人命運的身上是看得再清楚不過了。
別說是京劇、昆曲,我以為自上個世紀以來,整個文化是越來越迷失了方向。數千年積澱而成、且從未受到根本性質疑的中國文明,在後五十年的持續批判與否定中日趨毀損。去年,北京編演了一出有關梅蘭芳生平的新戲,僅看電視轉播,便驚駭萬狀。去聖已遠,寶變為石。晚清人士面對華夏文明即將崩塌之際,曾發出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驚呼,何以如此悲絕?
或許正如臺灣學者(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所言:“他們已經明白‘現代’所帶來的衝擊是如此摧枯拉朽,遠甚於改朝換代的後果。這也間接解釋何以民國肇造,有識之士儘管承認勢之所趨卻難掩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覺。他們在民主維新的風潮之後,看到一片龐大的文化、精神廢墟。‘憑吊’成為時代的氛圍。”如此看來,京劇《梅蘭芳》的演出也許是成功的,倒是個人的觀劇心理出了問題。
文化上何者為優,何者為劣,早已不堪聞問。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操控下,誰都難以成為獨立蒼茫的梅蘭芳。從老宅、年畫到京劇、皮影,任何對民間文化藝術的振興、弘揚似乎都是一種憧憬或空談。東西方文化相遇,某些方面可以交融、互補,而某些方面則完全是對立、衝突。幾個回合下來,博大精深的傳統藝術,正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走向衰微。
其從業者只能在背棄與承續、遺忘與記憶之間尋求折中之策、苟且之法。這大概也算得是文化現代性之兩難的生動顯現。那麼,我們還能做什麼?還有什麼可做?恐怕有朝一日,中國舞臺真的成了“《長阪坡》裡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裡沒有諸葛亮。” 當然,繼承傳統文化的難題也非中國所獨有。
藝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創造燦爛的同時,也陷入卑賤。他們的種種表情和眼神都是與時代遭遇的直接反應。時代的潮汐、政治的清濁,將其托起或吞沒。但有一種專屬於他們的姿態與精神,保持並貫通始終。伶人身懷絕技,頭頂星辰,去踐履粉墨一生的意義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復始。僅此一點,就令人動容。這書是記錄性的,是寫給不看戲的人看,故著墨之處在於人,而非藝。
知道的,就寫;知道多點,就多寫點。即所謂“有話則長,無話則短”。正因為奇特,他們也就有可能成為審視二十世紀中國式人生的一個觀察點。書中的?述與詮釋,一方面是為我的情感所左右,另一方面也是我所接觸材料使然。某種程度的偏見是有的。我喜歡偏見,以抗拒“認同”,可怕的“認同”。
書名就叫《伶人往事》吧。和耀眼的舞臺相比,這書不過是一束微光,黯淡幽渺。每晚於燈下憶及藝人舊事,手起筆落間似有餘韻未盡的悵然。它和窗外的夜色一樣,揮之不去。
有人說:你寫的東西,怎麼老是“往事,往事”的?是呀,人老了,腦子裡只剩下“往事”。歷史,故事矣。故事,歷史矣。我們現在講過去的故事,要不了多久,後人也會把我們當作故事來講述。恍然憶及從前逛陶然亭公園的情景。初春的風送來胡琴聲,接著,是一個漢子的歌吟:“終日借酒消愁悶,半世悠悠困風塵……”
我聽得耳熱,他唱得悲涼。
2005年11月於北京守愚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