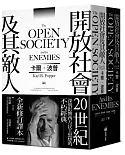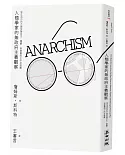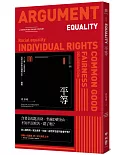序言 當務之急
建構國家體制(state-building)意謂著創設新的政府體制,並且強化現有的體制。本書將揭櫫一個理念:建構國家體制是當今國際社會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因為世界上許多最嚴重的憂患,都蔓延自積弱不振或病入膏肓的國家,從貧窮、愛滋病、毒品到恐怖主義,莫不如是。我同時也認為,人們對於建構國家體制雖然已知之甚詳,但有待探索的領域仍相當廣袤,尤其是如何將健全的體制轉移到開發中國家。我們知道如何以跨越國界的方式挹注資源,但是運作健全的公共體制有賴於某些心態習性的養成,其推動過程也相當複雜困難。對於這個領域,我們必須投入更多的心思、關注與研究。
有些人可能對此不以為然,認為今日的當務之急應該是限制或裁抑國家的角色,怎麼會是建構國家體制?畢竟過去一個世代以來,世界政治的潮流趨勢一直是批判「大政府」,並且將國家部門的活動轉移到私人企業領域或者公民社會。然而在某些地區,尤其是開發中國家,政府的孱弱、無能甚或無政府狀態,才是貽害無窮的禍因。
以愛滋病為例,非洲至少已經有兩千五百萬人罹病,死亡人數勢必直線上升至天文數字。愛滋病可以用抗反轉錄病毒(antiretroviral)藥物來治療,已開發國家就是如此。因此國際社會正積極募集愛滋病醫療經費,並極力要求大藥廠妥協,讓非洲與第三世界部分地區可以販售較便宜的學名藥。愛滋病的問題雖然有一部分是資源問題,但另一個重要部分在於政府推行公共衛生政策的能力。抗反轉錄病毒藥物不僅價格昂貴,而且服用方式複雜;不像疫苗接種能夠一針見效,這類藥物的療程漫長,劑量計算繁複,如果沒有遵照指示服用,反而可能會讓愛滋病毒趁隙突變並產生抗藥性,導致疫情更不可收拾。有效的治療需要健全的公衛基礎設施與公眾教育,並掌握特定地區的愛滋病流行病學知識。許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就算醫療資源已經到位,但是政府機構依然欠缺對抗疫情的能力(不過還是有些國家,例如烏干達的表現就鶴立雞群)。因此要真正解決愛滋病問題,我們必須幫助受害國家發展其政府機構的效能,以善用外界挹注的資源。
貧窮國家欠缺國家體制效能,一直是已開發國家揮之不去的夢魘。冷戰落幕之後,遺留下諸多衰頹不振的國家,從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中東、中亞到南亞。國家體制的崩解或凋敝,在一九九○年代導致一場又一場的人道與人權災難,肆虐索馬利亞、海地、柬埔寨、波士尼亞、科索沃與東帝汶。美國與其他國家原本還一廂情願,認為這些問題只侷限於局部區域,但是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充分證明,國家體制的孱弱已經形成一個艱鉅的戰略難題。極端的伊斯蘭教恐怖組織染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國家體制孱弱的問題雪上加霜,衍生出安全層面的深遠顧慮。美國以大軍進攻阿富汗與伊拉克之後,在當地挑起國家重建的重責大任。一時之間,強化或建立一個國家欠缺的某些效能與體制,儼然成為全球熱門議題,並且與許多重要區域的安全息息相關。因此對當事國與國際社會而言,國家體制孱弱的問題都是當務之急。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鋪陳出一個分析架構,藉以理解「國家性」(stateness)的多重層面,亦即政府的功能、效能以及合法性基礎。這個架構將解釋何以對許多開發中國家而言,問題在於積弱不振的體制,而非過度強勢。第二部分探討造成國家體制衰弱的原因,尤其要解釋為何儘管經濟學家不斷努力,公共行政仍然難以成為一門科學;這項缺憾也嚴重侷限了外界協助某些國家強化其體制效能的能力。本書最後一部分從國際社會層面討論國家體制孱弱的問題:衰弱的國家體制如何導致局勢不安、動搖國際體系中的國家主權原則;以及國際層面的「民主合法性」問題如何成為美國、歐洲與其他已開發國家對於國際體系的爭議焦點。
本書的藍本是二○○三年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間,我在紐約州綺色佳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梅森哲講座所做的演講。我非常感謝大學母校康乃爾以及前任校長羅林斯(Hunter Rawlings),他邀請我回母校主持這個夙負盛名的講座。我尤其要感謝康乃爾大學社會學系的倪志偉(Victor
Nee)教授,他盡心盡力主辦這一系列演講,讓我得以利用新成立的「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同時也要感謝中心副主任史偉德柏格(Richard Swedberg)。
第三章部分內容來自二○○二年八月間,我在澳洲與紐西蘭所做的兩場演講,分別是澳洲墨爾本的約翰.波尼松講座(John Bonyson Lecture)與紐西蘭威靈頓的羅納德.托特爵士講座(Sir Ronald Trotter Lecture)。感謝澳洲獨立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ependent Studies)與中心主任林賽(Greg
Lindsey),以及紐西蘭企業圓桌論壇(New Zealand Business Roundtable)的柯爾(Roger Kerr)先生與嘉德(Catherine Judd)女士,他們讓我和家人有機會造訪澳洲與紐西蘭。《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前任總編輯哈瑞斯(Owen Harries)對我的講座提供了寶貴意見。
本書諸多理念來自一門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所課程,是過去幾年我和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公共政策學院共同講授的,多年來李普塞特讓我獲益良多,本書正是題獻給他。
此外還有許多朋友與同事提供看法與意見,包括里茲(Roger Leeds)、艾恩紅(Jessica Einhorn)、史達(Fred Starr)、葛瑞里(Enzo Grilli)、曼德鮑姆(Michael Mandelbaum)、柯立特嘉德(Robert Klitgaard)、艾肯貝瑞(John Ikenberry)、伊格納帖夫(Michael
Ignatieff)、柏特克(Peter Boettke)、蔡斯(Rob Chase)、謝孚特(Martin Shefter)、拉布金(Jeremy Rabkin)、李維(Brian Levy)、哈默爾(Gary Hamel)、娃莉康佳絲(Liisa V�ikangas)、帕斯卡(Richard Pascale)、柯洛克(Chet Crocker)、古黛兒(Grace
Goodell)、普萊特納(Marc Plattner)、瑪庫兒絲(Karen Macours)。
作為本書藍圖的多場講座,有一部分曾經在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與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發表。我要感謝美洲開發銀行董事長伊格雷夏斯(Enrique Iglesias)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政策與計畫協調局的菲莉浦絲(Ann
Phillips)的費心辦理。本書第三章有一部分還曾發表於維吉尼亞大學密勒中心(Miller Center)、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SAIS)的跨大西洋中心(Transatlantic Center)、雪城大學的麥斯威爾學院(Maxwell
School)與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
我的幾位研究助理像馬西濟斯(Matthias Matthijs)、希絲姬(Krisztina Csiki)、密勒(Matt Miller)都貢獻了相當大的心力,為本書蒐集資料,尤其是德瑞塞爾(Bj�n Dressel)出力最多。另一位助理朵若蓋姬(Cynthia Doroghazi)則在成書的各個階段提供協助。一如以往,最後我要感謝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家人對我的支持。
推薦序
歷史終點的別名 文◎台大政治系教授 石之瑜
這本作者號稱不是要替美軍入侵伊拉克粉飾的著作,最終還是試圖要說明,為什麼美國要將現代化的進步體制移植到伊拉克,但同時也不避諱地根據種種歷史經驗指出,美國這個合情合理的良善意圖未必會成功。邇來國家的功能受到許多不同的評價,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家會干預市場,影響效率,因此認為國家的範圍要縮小,但在歷史事實上,國家所干預的範圍愈來愈大。法蘭西斯.福山新作《強國論》,對這兩種觀點俱陳,但情感上比較同情建立某種有效率的國家。在這樣一個情感傾向中,福山在書中分析現代國家體制與國家性質。
福山辯稱,現代國家體制是因應現代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公共管理基礎,缺乏這樣的現代體制,不但對效率與效能的提升形成掣肘,還會導致本社會流民移往歐美等由現代國家所管理的社會,造成歐美現代社會管理的困擾。他並觀察開發中國家的歷史經驗,看到政府體制發生關鍵作用,因此不贊成經濟學家一味地貶抑政府的積極功能。他比較細膩地依照統御範圍與統治能力,將國家的性質加以分類。國家統治能力強不見得代表干預嚴重,而國家統御範圍廣也不意味著統治能力強。他讚賞歐美那種統治能力強,但統御範圍有限的國家體制。
統治能力的建立需要很多條件配合,其中除了一般都會觸及的制度與資源問題,他特別提到文化的力量。換言之,制度的良莠不一定能解釋政府的效能,還要看是否有好的法治文化或領導文化。這就鋪陳出歐美國家當下面對的一個關鍵問題,即要不要輸出健康的國家體制到開發中國家。他受到九一一事件的刺激,認為恐怖主義的誕生與國家建制的性質有關。如果能將伊拉克重建成現代國家體制,其社會便不會孕育出恐怖主義。可惜他的研究在二○○五年暑假的紐澳良風災之前發表,因此對美國現代體制無法因應風災的現象,無法納入討論。不過,為了因應重建伊拉克國家體制的問題,福山呼籲必須就如何更有效地輸出現代化的國家建制進行深入研究。
他對國家干預程度與能力的研究,乃是資本主義市場降臨之後,知識界長久以來都在思索的問題,但這並不是天真無邪、純屬個人興趣的研究議程而已,因為這樣的設問,已經對人類的政治環境有了至少兩種規定。第一種規定是,先有社會,才有國家,唯有如此假定,國家的行動才能被視為是一種對社會的外來干預。第二種規定是根據第一種規定的邏輯推論所得,即國家干預範圍的擴大,是因應社會範圍的擴大,故國家干預的範圍不是國家建制所無中生有而來的。這個社會先於國家的前提,符合歐美社會的歷史經驗,但對遭遇殖民母國切割之後,於旦夕之間轉為主權國家的許多開發中地區而言,則是靠國家在營造社會。此何以在非歐美國家中,國家建制這個概念的意義,難以視為是由社會所決定;相反的,社會是由國家菁英由上而下在界定。國家先於社會,且國家統御範圍的擴大,帶動社會功能的擴大。
這是為什麼福山對於國家干預範圍由淺入深的標準,可能搬到開發中國家適用的話就會有困難。比如說,福山認為國防作為國家的功能,比教育更為基礎;但在一些開發中國家,國防並非最基礎的功能,因為統治者的敵人與盟友都是跨越疆界的族群,談國防似乎不合理,也不相關。又比如,福山認為財產權的保護比財富重分配是更基礎的國家功能;但在開發中國家卻常常必須因應群體文化,而以保障集體財產權為首先要著。另外,福山認為,現代國家體制在東亞的出現有些異於常態,卻是屬於成功的例子,而且這個成功的判斷未必全歸功於制度層面的國家體制建構,於是他同意文化與領導人的影響。他指出,不論是新加坡或是日本,都是這方面的例子,因為在那裡,國家體制建構對於市場與生產都是助力,而不是阻力。福山沒有引述另一種對此現象的有趣觀點則是認為,在東亞,國家與社會不存在先後問題,而是共生的一體兩面。
至於現代是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終極價值?現代化是不是一種文化改造?而文化改造是否就一定是值得無條件鼓勵呢?福山推崇杭廷頓對開發中國家的研究,認為對於其間現代國家體制建構相當關鍵,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不過,在進入後現代之後的歐美社會,有助於市場文化與生產效能的所謂現代制度,是否仍然那麼可欲呢?這個提問在流行的保育觀念中已經成為主流意識,現代化價值已是被質疑批判的對象,然而在國家體制尚未現代化的社群中,卻好像沒有機會進行這樣跨越歷史階段的反省,起碼福山顯然不打算鼓勵開發中國家這麼去檢討現代國家體制的建構,以至於現代國家體制對開發中地區的輸入或建構,仍舊以市場與經濟效率為評估的依據。假如這個依據是進入現代國家體制後必須重新思量的,則以現代國家體制為當前歷史發展目標的開發中國家,不就在走冤枉路了嗎?
福山過去一直推崇自由主義,指出歷史正緊靠著資本主義邁進終點,人類獲得了解放,已經免於受到集體的民族主義或法西斯所動員,也免於複製生物界那種男尊女卑的父權文化,這都是因為自由市場的競爭有效化解了暴力與宰制的慾望。自由主義之所以成為可能,正是由於已經沒有暴力在對人身進行威脅。九一一之後,他重新認識國家體制建構的作用,發現人類為了管理各種威脅,一方面需要有效能的國家,但二方面又希望是不會干預市場的現代國家。故他其實並沒有在本書中修正太多他原先的主張,或他對開發中國家的看法。所不同的是,他不再稱呼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歐美市場為歷史終點,現在,他稱呼它們為現代國家體制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