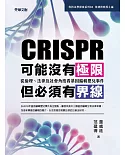序
翔往何方,歇於何處
拿破崙曾經有一次與歌德談到了悲劇的性質時指出,現代悲劇與古代悲劇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不再有一個人人臣服其下的命運,古代的命運已經由政治取而代之。因此在悲劇中必須將政治運用為新的命運,亦即那個體不得不順服的,環境中勢不可擋的力量。許南村,〈試論陳映真〉
本書的出版,最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大力協助,以及林宗翰先生的詳密校對,在此我要表達最深的謝意。書中蒐集了過去數年我在法理學與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洪遜欣教授曾指出,法理學是社會哲學的一部分。依照Ronald Dworkin的看法,法哲學則是政治哲學的一環。國際間最大的法理學學術團體IVR (Internationale Vereinigung fu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的名稱似乎支持著洪教授的說法,但是如果以IVR World Congress 2005 Granada, Spain, 所安排的主題演講等內容來看,似乎法理學與政治哲學、政治思想的關聯更大。其實這多少都有時代潮流趨勢的作用,IVR
最早的名稱是法律與經濟哲學學會,也許因為覺得涵蓋範圍不夠,因此後來改名為法律與社會哲學學會。但終究這些都是高度相關的學術研究領域。以歐美最權威的一份相關期刊 Ethics來看,其副標題就包含了社會、政治與法律哲學。
研究法理學是否可能不同時涉及對政治思想與政治哲學的研究呢?以現在這種高度分工化、專業化的的學術研究狀況來說,並不是不可能的。尤其以法實證主義與法唯實論的立場來看,不論是價值相對、價值不可知論、分離命題、實然化約論,似乎都隱隱含有法理學少碰政治思想的看法。Kelsen更是明白地指出各種政治思想都僅是意識型態。
不過我是不同意這種看法的。如果要以一種簡單的方式來說明我的看法,我會說:政治是一個存有的問題,存有是一個哲學問題,而-如果我們借用 Agamben的話-“philosophy is always already constitutively related to the law”。我無法在此詳細討論這個看法,但是我想我已經以本書的各篇文章來呈顯了此點。
雖然我在德國攻讀博士的時候,是以研究青年黑格爾的法政思想入手的,但是其實在大學讀書的階段,我主要研讀的政治思想對象是自由主義,而且是個有點「特殊」的自由主義(這點我後來才知道)-海耶克的思想。本書第一篇的三篇文章,都是研究黑格爾的著作。不過第三篇「自由主義」當中,則沒有特別研究海耶克的作品,反倒是以當代正統自由主義代言人,也就是羅爾斯的思想為主。畢竟海耶克雖然對我有相當多的影響,但是我始終無法被他真正的吸引。而哈伯瑪斯與羅爾斯兩人思想的精密度與體系性,吸引我投注更多細密的研讀。
但是要說吸引力,這兩位還是遠遠比不上黑格爾。畢竟,在歐洲漫漫兩千多年的思想史中,黑格爾絕對是兼具觀念原創、體系嚴謹,以及要素動感美的第一流思考者與書寫者。這點完全不需要我宣傳,因為黑格爾逝世後到今天的全球思想史早已經證成了此點。唯一想強調的是,黑格爾思想對我的影響,主要並非來自於《法哲學綱要》(雖然我也很喜歡此書),而是來自於青年黑格爾的著作,以及最重要的,他的《精神現象學》。雖然我不是個哲學家或純哲學研究者,但是《精神現象學》對我的思考卻起了無比深遠的塑造作用。我甚至曾經用它來寫影評。在某個意義上,黑格爾就像我精神上的父親一般。而我也是在近來的研讀中-主要是zizek-才了解「父」、象徵秩序,以及這兩者與法律的密切關係。
書寫是一種奇特的體驗。不論寫論文、散文、評論,還是寫日記,都不僅是一種頭腦思考的活動,更是一種身體與心靈的生命交融感。老實說,我往往在寫許多「非正式」的文章時,能夠感受到更深刻的生命交融。〈五四情懷父與子-浮探知識分子文本之類型學〉即為一例。該文原本僅是為中國時報開卷版所寫的書評,但是對我而言,卻是一段生命情懷的結算。而這種結算,總是帶有向大他者,或者父,的一種對決式割捨吧。
幕垂鴞翔,翔往何方,歇於何處,不論是Minerva
還是黑格爾,都不會知曉。可以確定的僅是即將來臨的夜,以及終將破曉的黎明。如果知識、權力與戰爭可以由同一位女神主宰,那書寫終究也僅能是非權力孤者的異鄉獨白。走過了許多不同的道路,有佇留,有止歇,但似乎總是沒有安居之所(ethos)。無所適從,此其義吧。沒有料到的是,不是因為無思而無所適,而正是因為思所開啟的存有裂縫,讓煩憂(Sorge ;
或牽掛)成了遊伴。契訶夫曾在一篇短篇小說裡如此描述:「以前在憂傷的時候,他總是用他想得到的任何道理來安慰自己,可是現在他顧不上什麼道理了,他感到深深的憐憫,一心希望自己誠懇、溫柔。LL 」也許憐憫、誠懇與溫柔,是最憂傷的道理吧。
顏厥安 2005年5月18日 謁岸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