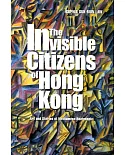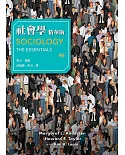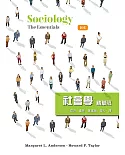班雅明說:「文藝復興探索宇宙,巴洛克探索圖書館。」探索宇宙太難了,探索圖書館太無趣了。而在圖書館和宇宙之間,還有歹戲拖棚的歷史。我只想在歹戲拖棚的歷史演到最不好看,最啼笑皆非的時候,可以碰巧讀到一些好笑的東西。所以,當我碰巧讀到卡夫卡的動物寓言,不覺啞然失笑!
芥川龍之介說:「人生不抵一行波特萊爾的詩。」我不覺得波特萊爾的詩有那麼好,但我發現台灣的歷史的確也不抵一則卡夫卡杜撰的無稽寓言。在這個「不如無書」的年代,這真是一個曠世幽默的詮釋學事件!一個靈感閃進我心:何不將台灣這阿貓阿狗胡搞瞎搞的一切命名為「鼠儒主義」,豈不妙哉?
相對於「犬儒」的現實與世故,「鼠儒」卻是極度功利市儈而又因為沒有文化,而非常孩子氣無厘頭。
西方的頹廢世紀末產生了虛無主義與犬儒主義。清末民初的中國亂世產生了魯迅所描述的阿Q精神。而台灣今時的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則在犬儒與阿Q之外,杜撰了一個全所未有的「鼠儒主義」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