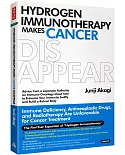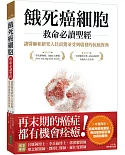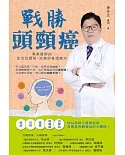難忘師生間的第一堂課
藍琴臺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段日子我們共同選修了一門生死學。
發生在我周遭連串的事
初識玲玲,是在民國九十二年九月新學年的上學期初。我在學校餐廳買便當,兩位女生迎面走來,沒有自我介紹,只見較為清瘦的那位掛著笑臉,有點怯意的問:
「您是教大體解剖學的藍老師嗎?我剛復學,還沒有去上課。我跟班上的學弟妹不熟、跟現在醫三的同學比較熟。」
或許是她的開場白不夠高明,或許是她的笑容太陽光,也或許是她身旁女伴裝扮太時髦、手提包太搶眼,我語氣略帶不悅的說:
「開學都已經過了兩三個星期囉,妳怎麼還在狀況外?我的骨骼系統都快上完了,妳要趕快追上進度呀!妳現在這個班級的同學,已經不是妳的學弟妹,妳最好還是趕快跟他們混熟才對,否則怎麼拿到講義、共筆(即為上課筆記,由學生推派的筆記小組負責撰寫,印製後全班同學均可分享)和上課錄音帶?大體解剖學那麼重,可不是鬧著玩的……」
又過兩星期,醫五的周建成同學來找我,說:
「老師您認識蔡玲玲嗎?她是我的直屬學妹,她從開學到現在都一直住在附設醫院,腎臟發炎一直好不了,不能來上課,請老師想想辦法幫助她。」
玲玲?!莫非是去年暑假傳出罹癌的大一女生?莫非是我在餐廳碰到的那位?我的心頭一震,感到非常歉疚。班上學生發生這麼重大的事故,為何我都無所悉、無所覺?當下立即將工讀生召集過來商討對策。
工讀生有四位:醫四的許育甄、醫三的李佳容、林怡萱和張志丞。
為了不影響他們的課業,也考慮到玲玲需要充分休養,我請他們每人每週給玲玲一個小時,帶著真人骨骼到醫院幫她上課。
然後又在醫二班級上,召募十來個自願者組成讀書小組,請他們每人認養一段章節,現學現賣,幫玲玲補習肌肉、關節與韌帶系統。再請科內張宏名與陳建榮兩位老師從旁協助,到醫院為玲玲舉行考試及實習測驗。就這樣子,按步就班、相安無事的過了期中考。
那時學校正在接受TMAC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也就是醫學系的教學評鑑,我難免公務纏身,加上啟用兩本新版的《神經解剖學》教科書,又必須要一邊與國外科研雜誌主編、評審打筆仗,真是忙得昏頭。
更有甚者,學生陸續發生一些棘手問題,有身心方面的,也有感情方面的,都找上門來;而因血癌在醫三時休學的李周憲同學,這時卻傳來病危通知。
我寫信給我新加坡的指導教授說,我覺得自己像個陀螺整天在轉,不停的說話、不停的上醫院,也不停的想哭,世間哪來的這麼多苦難?
一個在台灣被大愛包圍的女學生
那年的聖誕節前夕,隨著周憲病況轉危,我一班一班地跟醫學系學生說明,請他們發動「卡片接力賽」,讓周憲與玲玲隨時都能被大愛包圍、保護。
學生的愛心炙烈,這些赤子之心一旦被喚起、被強化,往往能夠發揮很大的力量。尤其他們日後都是站在醫療最前線的人、都是生命的守護者,俗話說得好:願有多大,力就有多大。TMAC的評鑑委員不是念茲在茲地要我們加強「人文醫學教育」嗎?人文醫學教育不應只是在課堂上,是要在行動上做心靈的善化與改革──就讓我們從關懷與照顧自己的同窗手足開始做起吧!
期末考的範圍是我教授的周邊神經系統。撲朔迷離、抽象難懂。學生說十二條腦神經不是條條通羅馬,而是最後糾結一起,變成一條,通向死胡同。這時候,連讀書小組都自身難保、招架不住了;玲玲迫不得已打電話來,希望我親自去醫院為她授課。
第一次到醫院上課,也是第一次正式見到玲玲(餐廳的那次不算,當時我只顧著訓誡人,對她一點印象都沒有),而且她跟我的想像完全不一樣。
我原本以為會看到骷髏造型,她卻比任何健康的人還要健康,我起先不甚明瞭,但事後細想才發覺是她的那股鬥志與樂觀,誠於中形於外,造成我剎那間的錯覺。
她的蘋果臉上經常掛著燦爛的笑容,不是那種淺淺的、茫然的、淒苦的笑,而是一笑起來就會滿室生輝的那種。
她會跟你詳細報告病情,沒有絲毫恐懼與悲傷;也會認真聽取別人的看法,像是參加醫學研討會一樣,充滿理性與睿智;倒是很少哭泣,應該不是淚早已流乾,而是天生就不會隨意浪費眼淚的人。我從她身上漸漸明白,原來可敬之人必有可愛之處,可悲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上課時,她顯得非常緊張,再三道歉自己沒有事先準備好,要勞煩我從頭講起;又處處留意我是否感到不自在,像是個失責的主人。
我沒見過這麼求好心切的人,也沒想到她還那麼年輕,就懂得凡事檢討自己、體諒別人。她那麼地維護我,甚至不惜「小蝦米vs大鯨魚」的跟一位主治醫師搶占會議室(當然不可能成功)。說來慚愧,我竟從她大無畏的表現上獲得某種程度的依賴和安全感。
我們開始角色互換
我離去的當晚,她就發燒了。因為她上課時太緊張,不敢多要求上廁所,結果稍一憋尿,腎臟就發炎了。我事後知道,感到非常懊惱,在此之前,我對於她本人一無所悉,對於她的病況也不甚明瞭。事實上,她並非像表面看來的那麼健康與強韌。
第二次去醫院,我就不急著上課了。我開始遠兜遠轉的跟她談自己,看她反應、跟她互動。結果發現,原來藏在理性背後的她,真正是個極端敏銳、感性的人。後來索性就不上課,一去醫院就純聊天。我從未如此貼近過一位癌症患者,即便我母親得的是「膽囊轉移的肝癌」,但母親從一發病到過世只短短二十天,而且大部分時間又都處於彌留狀態,因此我無從知曉癌症對於當事人的迎面衝擊和全面顛覆。
我們開始角色互換,她是師我是生,我向她學習死與生的課題。她一提到某本書影響了她,我就馬上買來看;她說起「情境轉折」,也常讓我感同身受。我慢慢地走入她的內心世界,漸漸地結上這一段緣。
年關近了,周憲的病況逐漸穩定準備出院,玲玲的情形卻始終樂觀不起來。她的腸陰道(Intestinovaginal fistula)長久不易閉合,泌尿系統也反覆發炎,在在顯示癌細胞潛藏在體內,伺機增生復發。我越是接近她,看著她義無反顧的規劃願景,越是暗自憂心:她為死亡做好準備了嗎?我能為她做些什麼?
直至過完年,她北上求醫,住進榮總,我認識了終日照顧她的六位愛心媽媽、無數幫助她的善心人士,還有川流不息的訪客,我這才知道我可以為玲玲做些什麼事情。是的,我想為玲玲還掉世間的人情債──善緣可結,債卻不可欠。雖然大多數人為善不欲人知,但是我們不能感恩不圖報,即便只能做到口頭稱謝,也要誠心誠意的公開講出來。所以無論是玲玲的「口述」,或是我寫的「週報」,對於該千恩萬謝的人與事,都是指名道姓、真人實事。
然而,要不是看了她的口述,我無從認識更深層的她──明知道自己最大的精神支柱是病中相伴的男友,她還是揮劍將人間最後底一絲依戀斬斷。她給了別人自由,也超脫我執與束縛。
她的口述裡唯一沒有指名道姓的就是男友──楊宗霖,這讓我更見識到她的另一種慈悲──她想保護當事人。楊也是我教過的學生,所以我一傳話過去,他就趕忙跑來報到。我徵詢他的意見,說:「玲玲的愛情故事恐怕是她這一生中最精華的部分,能不能讓它公諸於世?讓她直指其名、暢所欲言?」
楊回答得乾脆:「我絕對沒有問題,甚至老師還想補充什麼內容,我都可以提供更細節的資料。我跟玲玲之間是沒有任何隱瞞、也沒有任何溝通障礙。」
我再進一步確認:「有沒有考慮到以後你的女友或妻子可能藉此來跟你翻舊帳?那時候你就吃不完兜著走了。」
他靦腆的笑笑:「怕那些幹什麼呢?」嗯,好樣的。要相伴一生的人哪,不怕他把愛情給了別人,就怕他是個寡情的人,凡事總有個先來後到,對不對?
陪玲玲走過的心路歷程,多少改變了我的生命結構,這原不是我事先設計好的。有時候別人會問我所為何來?有時候我也會在內心詢問:「那些愛心媽媽又所為何來?」她們跟玲玲不是師生關係,她們更是拿不出理由來的。
其實也不過是一種責任感吧!當你認定那就是自己份內的事,不去做反而覺得良心不安。好比是自己的親人生病,你會放任著不去照顧他麼?曾經有一位醫師太太跟我說,最不喜歡在國內旅遊了,玩得正高興,一通電話就把先生召回去。事實上,我認識的很多醫師都是這樣子二十四小時待命,他們真正是做到「視病猶親」哪!人生在世,若是沒有分別心、排他性,那該有多好啊!
這會是一本大家的書,很多人在書中應該處處可見自己風塵僕僕的身影,記實著那段我們陪玲玲走過的日子。沒錯,就算光陰再逝去、年代再久遠,我們總會想起共同行經的路線──石牌的欒樹花開了又謝,捷運車窗外的小葉欖仁,剛抽出嫩綠的新芽又轉為濃綠繁茂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段日子我們共同選修了一門生死學,雖然最後不免曲終人散,但玲玲的風範卻讓大家低迴不已!
人生在世,若是沒有分別心、排他性,那該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