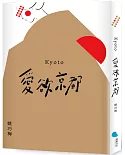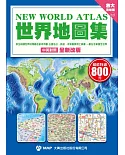導讀
詹宏志
航海人史洛坎
第一位實踐航行地球一周的人是誰?那是充滿想像力的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但他其實沒有完成願望,半途就死在菲律賓,是他的船員繼續前進,完成了繞行地球一周的航行。
另一位周遊地球三大洋五大洲的大探險家則是有名的英國航海家詹姆士.庫克船長(Capitan James Cook, 1728-1779),他幾乎是一個人完成了我們今日所了解的地球上陸地與海洋分佈的知識,也難怪你在世界各個奇怪的角落都要看到他的蹤跡,和許多以他為名的各種地理名詞(譬如說阿拉斯加的庫克內灣、紐西蘭的庫克海峽、南太平洋的庫克群島等等)。
但是,前兩位歷史名人都是艦艇成隊、水手成群的航海指揮官,你知道第一位「一個人」獨自完成環遊地球一周的人是誰嗎?我說的真的是「一個人」,隻手空拳,別無其他同伴或助手;我說的也只是「一艘船」,除了風帆別無其他憑藉或動力(沒有風或者闖入無風帶,它就要陷入停擺的窘境)。這艘手工木造船的全長不過三十七呎,也別無其他接駁或補給,在大洋之中不啻是所謂的滄海一粟,渺不可聞。這樣個人隻船的環球孤航,是何等的勇氣魄力,又是何等的技術成就?完成這項壯舉的是一位美國船人約書亞.史洛坎(Joshua
Slocum,1844-1909),他所使用的船隻命名「浪花號」(Spray),是一艘史洛坎自己設計、自己建造的單桅帆船。
史洛坎生在今天加拿大新斯科細亞(Nova
Scotia)的威爾莫特(Wilmot),父母親雙方的祖先都是海上討生活的人;但他的父親後來卻在陸地上開了修鞋店,十歲以後的約書亞.史洛坎就被要求輟學在家修鞋。似乎海洋仍是小史洛坎體內一種自然的召喚,十二歲時他就逃家上了近海捕魚的漁船。十六歲時他的母親過世,他更加心無牽掛,改走遠洋商船,流浪於歐、亞兩陸之間,足跡遍及巴塔維亞(即今印尼雅加達)、摩鹿加群島、馬尼拉、西貢、香港、新加坡等地。在船上,他學盡了各種行船的技能,十八歲就成了領有執照的船上大副。
一八六七年美國政府從俄羅斯手中買下阿拉斯加(後來──遲至一九五九年──才成為美國的四十九州),並鼓勵美國年輕人以西部拓荒精神前往開闢各種可能的經濟活動,史洛坎受了感召,也第一次得到船長職位,主持一場前往阿拉斯加捕鮭魚的探險之旅。史洛坎任船長的「華盛頓號」(Washington)因而成了第一艘航進庫克內灣的美籍船,他試驗性質的鮭魚網捕大獲成功,但船隻卻因為下錨失誤而損失了;史洛坎幹練地保住了漁獲,並為「華盛頓號」船主獲得鉅利。船主不怪他損失了船,反而讓他擔任另一艘船「憲法號」(Constitution)的船長。此後,他以船長身分,穿梭舊金山、澳洲、墨西哥、南海等地,累積了無數航海經驗,並賺得第一艘屬於自己的九十噸多桅帆船。
史洛坎後來的船人生涯讓我們看到兩件事,一、他顯然是一位出色的生意人,他不斷找到市場的新需求(捕魚、運木材),送到價錢最好的地方(足跡遍及馬尼拉、檀香山、長崎、上海、海參崴等埠),而且他一賺到錢就賣掉原來的船,買進更大更好的船;二、他似乎對寫作生涯發生了興趣,在航海旅程中他兼為舊金山蜂報(Bee)擔任特派員,一心想要成為一位作家(這件事當然與我們今天會讀到這本書有關)。
單桅船浪花號
也許我不能在此盡述史洛坎漫長、波折、多彩的海上人生,總之,他有了船,又失去了(一次船難就失去了全部),然後又有了船,然後又失去了。一八九二年,他已是歷經滄桑的老船人(四十八歲),人生又擱淺在陸地上一段時間,他正在盤桓思索是要重新替他人領船、還是在岸上船塢找個工作?一個因緣際會使他得到一艘必須大部分重修的小船,他因而發雄心親手重建打造,不料竟造就了一艘將在歷史上留下大名的單桅小船來。
後來的故事,想來你已經知道,這艘船就是伴隨他完成週遊地球壯舉的「浪花號」;史洛坎在波士頓鄰近港口費哈芬(Fairhaven)的岸邊,花了十三個月,從龍骨到油漆,一木一釘不假他人,親手打造了這艘長三十六呎九吋,寬十四呎二吋,船艙深四呎二吋的單桅帆船,淨重九噸,載重十二點七一噸,材料一共只花了他五百多塊。順便一提,費哈芬和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
1819-1891)小說《白鯨記》(Moby Dick)的舞台捕鯨港口新貝德福(New Bedford)只隔一條河,我曾經去過新貝德福,昔日港口的磚造倉庫,如今藏有一座非常好看的捕鯨博物館,水手以實瑪利去講道的教室也還在,而信步過了一座橋,就是昔日史洛坎手造浪花號的費哈芬。
史洛坎用這艘船捕魚載貨,過了一段日子。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那天風和日麗,按照作者的說法,他早就想要駕船環繞世界,看那天早上風好,遂起意揚帆出發,一副是要到附近公園散步的口吻。但這一天駛離波士頓港,再回來將是一千一百六十個日子以後(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他航返羅德島的新港),史洛坎此程一共航行了四萬六千哩(七萬四千公里),歷時逾三年,並創下單人揚帆環繞世界的紀錄來。
航行當然不是風平浪靜,也不是全無周折。事實上,他剛剛橫跨大西洋來到直布羅陀海峽,就遇上了意欲打劫的海盜,在千鈞一髮的追獵脫逃之間,他把心一橫,決定掉轉船頭,返回美洲,改從南美洲最南端通過,取道南太平洋,越過澳洲和印度洋,再經南非好望角,穿越大西洋向北折回美國。這種毫無計畫,全憑靈感與勇氣的行徑,讓人不得不驚訝而佩服。
憑著超越凡俗的航海技術與膽識,史洛坎在海上歷經海盜、颶風、大雨等困難,百劫歸來,成為大英雄。他把自己的經歷,自撰成書,先分兩年連載完畢,一九○○年正式出版,也就是本書《孤帆獨航繞地球》(Sailing Alone Around the
World);書出之後大受歡迎,一時洛陽紙貴,也完成了他成為大作家的夢想。他的故事,帶有勵志意味,因而載入美國孩童的教科書中,至今誦讀不歇,史洛坎也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名字。
史洛坎寫的書,出奇地淺白易讀,節奏明快,敘事幽默,讀來全不費力氣,令人驚訝於他根本沒受過多少正式教育,這可能是此書經過百年還能繼續再版、讀者不間斷的原因。
成名後的史洛坎,靠版稅買了他在陸地上第一個住家,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但是且慢,真實世界很少有這樣的結局。我們故事中的主人翁在演講、寫作之餘,仍然不能忘情於大洋,陸續還有幾次冒險犯難的單人航行(照他的說法,那是「冬天的度假」)。史洛坎一生航行有多次遇難,但都能逢凶化吉,安全歸來。一九○九年,他像往常一樣,看那日風好,獨自駕著「浪花號」出航,就像西方人所說的「好運有用完之時」,史洛坎和「浪花號」這一次一去不返,沒有人再看到他,沒有人知道這一次他去了那裡。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