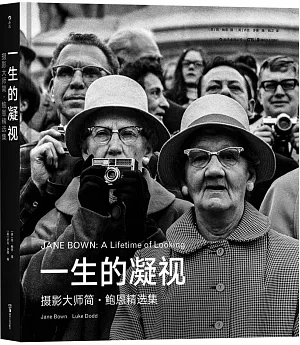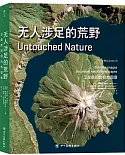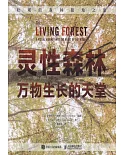從學生時代的濕版作品到生命裡拍攝的最後一張肖像照,本書回顧了英國攝影大師簡·鮑恩(1925—2014)一生的創作精華。在為老牌星期日報紙《觀察家報》擔任攝影師的65年裡,她直視過撒母耳·貝克特的敵意,面對過瑪格麗特·柴契爾的強硬,捕捉過若有所思的穆罕默德·阿里。她喜愛在自然光下拍攝人物放鬆的姿態,用黑白灰表達人物的精髓。
除了各界名人的肖像照,她還拍攝時常被忽視的人或事:郵局罷工、漁民的抗議、國王路上的朋克族、女性援助庇護所的兒童等等。本書由她的好友盧克·多德(Luke Dodd)精心編輯,從她一生的作品中精選了200餘幅照片。這些直抵人性深處,又不流於感傷,充滿尊重和溫暖的作品,奠定了簡·鮑恩的英國攝影大師地位。
作者介紹
簡·鮑恩,在曾由男性主宰的英國媒體界,簡·鮑恩是一個傳奇。1945年她從英國皇家女子服務隊退役後,在吉爾福德藝術學院參加當時全英國僅有的全日制攝影課程。從1949年起,她在《觀察家報》擔任攝影師。她動作迅速,行事低調,能讓拍攝物件卸下防備,回歸自我。用這樣的方法,65年間她從未空手而歸。
1985年和1995年,英國先後授予她大英帝國員佐勳章(MBE)和司令勳章(CBE),以表彰她在攝影方面的傑出貢獻。2000年,皇家攝影學會授予她榮譽高級會士(HonFRPS)。她出版過《溫柔的眼》(The Gentle Eye,1980)、《重要的女人》(Women of Consequence,1986)、《重要的男人》(Men of Consequence,1987)和《面孔》(Faces,2000)等多部攝影集。英國威斯敏斯特宮、國家肖像館、法爾茅斯藝廊等機構收藏了她的作品。
盧克·多德,本書編者,簡·鮑恩的好友,曾在攝影集《曝光》(Exposures)、《前所未見的鮑恩》(Unseen Bown)及影片《尋光:簡·鮑恩》(Looking for Light:Jane Bown)中與其協作。
錢衛,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攝影之友》雜誌長期譯者,譯有《荒野之歌:國際野生生物攝影年賽》《拆物專家:當代生活常用物件解剖》,另有數本譯著待出版。現為圖書編輯。
1985年和1995年,英國先後授予她大英帝國員佐勳章(MBE)和司令勳章(CBE),以表彰她在攝影方面的傑出貢獻。2000年,皇家攝影學會授予她榮譽高級會士(HonFRPS)。她出版過《溫柔的眼》(The Gentle Eye,1980)、《重要的女人》(Women of Consequence,1986)、《重要的男人》(Men of Consequence,1987)和《面孔》(Faces,2000)等多部攝影集。英國威斯敏斯特宮、國家肖像館、法爾茅斯藝廊等機構收藏了她的作品。
盧克·多德,本書編者,簡·鮑恩的好友,曾在攝影集《曝光》(Exposures)、《前所未見的鮑恩》(Unseen Bown)及影片《尋光:簡·鮑恩》(Looking for Light:Jane Bown)中與其協作。
錢衛,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攝影之友》雜誌長期譯者,譯有《荒野之歌:國際野生生物攝影年賽》《拆物專家:當代生活常用物件解剖》,另有數本譯著待出版。現為圖書編輯。
序
簡·鮑恩談到自己時,帶著一貫的自我貶低,自稱“賣照為生之人”。為《觀察家報》工作的六十多年間,她拍攝過生活的各個領域——從時裝秀到罷工,從狗展到考古挖掘,從選美大賽到名人審判。我在她的檔案中發現一套標注為“井蓋”的底片與印樣,那是三十六幅拍攝倫敦街道上的井蓋的特別作品。她作品中非凡的多樣性,往往會被她的英國肖像攝影大師的名聲掩蓋。她曾表示,自己被派去拍攝肖像是因為工作效率高,且不大驚小怪,至少在最初是這樣的原因。
“以前我從未對人產生過真正的興趣,後來才變了……。”為了拍攝肖像,簡被迫從邊緣走到中心,直面拍攝物件,但她從未放棄另一種更隱秘的工作方式。直到攝影生涯的最後……,在一個火車站裡徘徊,將不起眼的身形藏於川流不息的通勤人潮中,悄悄進行觀察。膠捲中最初和最後的幾張,總是簡在前往或結束工作的路上拍攝的個人作品。在這些照片裡,專注於世俗事務的個體于不知不覺間成為永恆。……
難用語言來形容在她最傑出的作品中到處流露的藝術敏感性。諷刺的是,從否定的角度描述她倒是容易得多——不喜歡人造光、暗房處理或道具;不用曝光表,而是通過感受落在手背上的光線來調整相機設置;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每次拍攝都不超過一個半膠捲;回避彩色攝影;希望在拍照前對拍攝物件只有零星瞭解,甚至一無所知;從不為了藝術效果而迫沖底片。對簡而言,出書或是辦展覽並非主要目的,拍照這個行為本身才是首要動機。
她隱蔽的工作方式和審美是為了保持謙遜。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她請過助手,找過經紀人,或者試圖通過商業畫廊出售自己的作品。在整個攝影生涯中,簡對自己的工作方式幾乎閉口不談,極少接受採訪。她的口頭禪是“攝影師既不該被看見,也不該被聽見”。沒有什麼能夠動搖這種沉默;準確地說,這反映了她來自直覺深處的工作方式。如果一張照片足夠優秀,何須攝影者多言呢?
……訓練非常嚴格:雖然膠片庫存是現成的,但湯瑪斯仍然教導學生如何在玻璃版上塗布感光乳劑,怎樣掌握甘多菲(Gandolfi)相機。簡的一幅濕版攝影作品保留了下來,那是一張怪異的無身玩偶靜物照。從簡的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湯瑪斯深受新客觀主義影響,強調形式、構圖和物質性。簡從學徒時代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使用的祿來福來(Rolleiflex)相機非常契合這種風格,反直覺的技術(取景器需自上而下觀看,顯示顛倒的影像)提供了抽象的手法,而中畫幅膠片則對細節有無比清晰的呈現。攝于1949年范堡羅航展的照片是簡在這個時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堪稱形式、內容與構圖的完美結合。
簡畢業後在倫敦向眾多攝影機構和工作室推銷自己時使用的作品集得以保留了下來——以靜物照與人像習作為主,用來展示她的攝影技術和全面性。雖然這只是早期階段,但簡的許多標誌性風格已經初現端倪:熱衷於拍攝兒童,偏愛自然光而非人造光,瞭解如何利用光線來強調心理層面的洞察力,以及和諧而精巧的構圖。
簡在漢普斯特德一家工作室裡短暫地工作過一段時間,以拍攝兒童肖像為主,之後得到了《觀察家報》首位圖片編輯梅希特希爾德·納維亞斯基的關注。根據簡的說法,納維亞斯基看到她為牛眼拍攝的超現實特寫後非常震驚,認定她在肖像攝影方面很有潛力。1949年1月,她委託簡為伯特蘭·羅素拍攝一張肖像。“一次可怕的經歷,”簡回憶道,“我連他是誰都不知道……但光線還不錯。”她很快便和《觀察家報》結下不解之緣,與邁克爾·佩托和大衛·西姆等人共同擔任該報的常駐攝影師。當時的《觀察家報》深受戰後經濟緊縮的影響。在8頁的大報裡,由於配圖稀少,照片有著非同小可的影響。最初幾年,簡的作品往往列於第7版的人物小傳旁邊。
這些作品很正式,大多數相對缺乏生氣,會被存檔,在日後反復使用。把簡在1950年和1993年為約翰·吉爾古德拍攝的照片進行對比,你會明顯感覺到新聞攝影的風格有了徹底的改變。在早年拍攝的半側身肖像中,一本正經的吉爾古德十分拘謹,右臂搭在台座上面的姿勢有意令人想起文藝復興時期的肖像。而在後來的照片中,他完全放鬆下來,溫柔的目光仿佛是周遭樹葉的延伸;這一次,正襟危坐的則是腳邊的一對石犬。
“以前我從未對人產生過真正的興趣,後來才變了……。”為了拍攝肖像,簡被迫從邊緣走到中心,直面拍攝物件,但她從未放棄另一種更隱秘的工作方式。直到攝影生涯的最後……,在一個火車站裡徘徊,將不起眼的身形藏於川流不息的通勤人潮中,悄悄進行觀察。膠捲中最初和最後的幾張,總是簡在前往或結束工作的路上拍攝的個人作品。在這些照片裡,專注於世俗事務的個體于不知不覺間成為永恆。……
難用語言來形容在她最傑出的作品中到處流露的藝術敏感性。諷刺的是,從否定的角度描述她倒是容易得多——不喜歡人造光、暗房處理或道具;不用曝光表,而是通過感受落在手背上的光線來調整相機設置;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每次拍攝都不超過一個半膠捲;回避彩色攝影;希望在拍照前對拍攝物件只有零星瞭解,甚至一無所知;從不為了藝術效果而迫沖底片。對簡而言,出書或是辦展覽並非主要目的,拍照這個行為本身才是首要動機。
她隱蔽的工作方式和審美是為了保持謙遜。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她請過助手,找過經紀人,或者試圖通過商業畫廊出售自己的作品。在整個攝影生涯中,簡對自己的工作方式幾乎閉口不談,極少接受採訪。她的口頭禪是“攝影師既不該被看見,也不該被聽見”。沒有什麼能夠動搖這種沉默;準確地說,這反映了她來自直覺深處的工作方式。如果一張照片足夠優秀,何須攝影者多言呢?
……訓練非常嚴格:雖然膠片庫存是現成的,但湯瑪斯仍然教導學生如何在玻璃版上塗布感光乳劑,怎樣掌握甘多菲(Gandolfi)相機。簡的一幅濕版攝影作品保留了下來,那是一張怪異的無身玩偶靜物照。從簡的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湯瑪斯深受新客觀主義影響,強調形式、構圖和物質性。簡從學徒時代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使用的祿來福來(Rolleiflex)相機非常契合這種風格,反直覺的技術(取景器需自上而下觀看,顯示顛倒的影像)提供了抽象的手法,而中畫幅膠片則對細節有無比清晰的呈現。攝于1949年范堡羅航展的照片是簡在這個時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堪稱形式、內容與構圖的完美結合。
簡畢業後在倫敦向眾多攝影機構和工作室推銷自己時使用的作品集得以保留了下來——以靜物照與人像習作為主,用來展示她的攝影技術和全面性。雖然這只是早期階段,但簡的許多標誌性風格已經初現端倪:熱衷於拍攝兒童,偏愛自然光而非人造光,瞭解如何利用光線來強調心理層面的洞察力,以及和諧而精巧的構圖。
簡在漢普斯特德一家工作室裡短暫地工作過一段時間,以拍攝兒童肖像為主,之後得到了《觀察家報》首位圖片編輯梅希特希爾德·納維亞斯基的關注。根據簡的說法,納維亞斯基看到她為牛眼拍攝的超現實特寫後非常震驚,認定她在肖像攝影方面很有潛力。1949年1月,她委託簡為伯特蘭·羅素拍攝一張肖像。“一次可怕的經歷,”簡回憶道,“我連他是誰都不知道……但光線還不錯。”她很快便和《觀察家報》結下不解之緣,與邁克爾·佩托和大衛·西姆等人共同擔任該報的常駐攝影師。當時的《觀察家報》深受戰後經濟緊縮的影響。在8頁的大報裡,由於配圖稀少,照片有著非同小可的影響。最初幾年,簡的作品往往列於第7版的人物小傳旁邊。
這些作品很正式,大多數相對缺乏生氣,會被存檔,在日後反復使用。把簡在1950年和1993年為約翰·吉爾古德拍攝的照片進行對比,你會明顯感覺到新聞攝影的風格有了徹底的改變。在早年拍攝的半側身肖像中,一本正經的吉爾古德十分拘謹,右臂搭在台座上面的姿勢有意令人想起文藝復興時期的肖像。而在後來的照片中,他完全放鬆下來,溫柔的目光仿佛是周遭樹葉的延伸;這一次,正襟危坐的則是腳邊的一對石犬。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