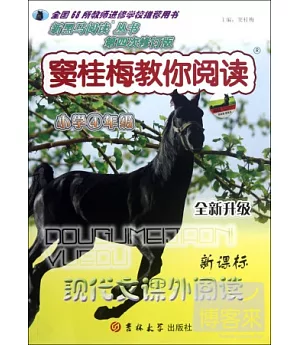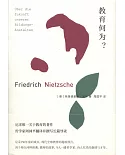每次能抽出時間回老家都是在冬天,而北方的冬天是被白雪包裹著。車子下了公路之後需要走3個小時的山路,才能抵達我大山深處的家。
車子在山路上顛簸著,頭上是白花花的太陽,田野里一片白色,連遠處的樹也穿著白色的衣裳巍然挺立,偶有幾只野雞在雪地上起舞,也是寂寞無聲的。每逢此時都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直抵我的心靈深處,我回來了!我回來了!我的心在一次次地吶喊,伴著這呼喊有淚水流下。
20年前,我提著行李走出這大山,身後浩浩蕩蕩地是送別的鄉親,他們如我年邁的父母一樣衣衫襤褸。他們熟情的呼喊聲和動情的眼神一直激勵著我自強不息。研究生畢業之後我才發覺我是如此普通,普通得與這城市里的甲乙丙丁沒有區別。我所有的壯志豪情都被城市的滾滾人流淹沒了。許多年過去了,我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坐標。我消沉絕望,連回家的勇氣都沒有。
母親進城看我,她粗黑的臉膛和濃重的方言讓我覺得很難堪。母親倒並不介意我投向她的眼神有何種含意,只顧一味熱情地把從老家帶來的梨和雞蛋分給我的同事們,說著客氣的好話,希望我們關系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