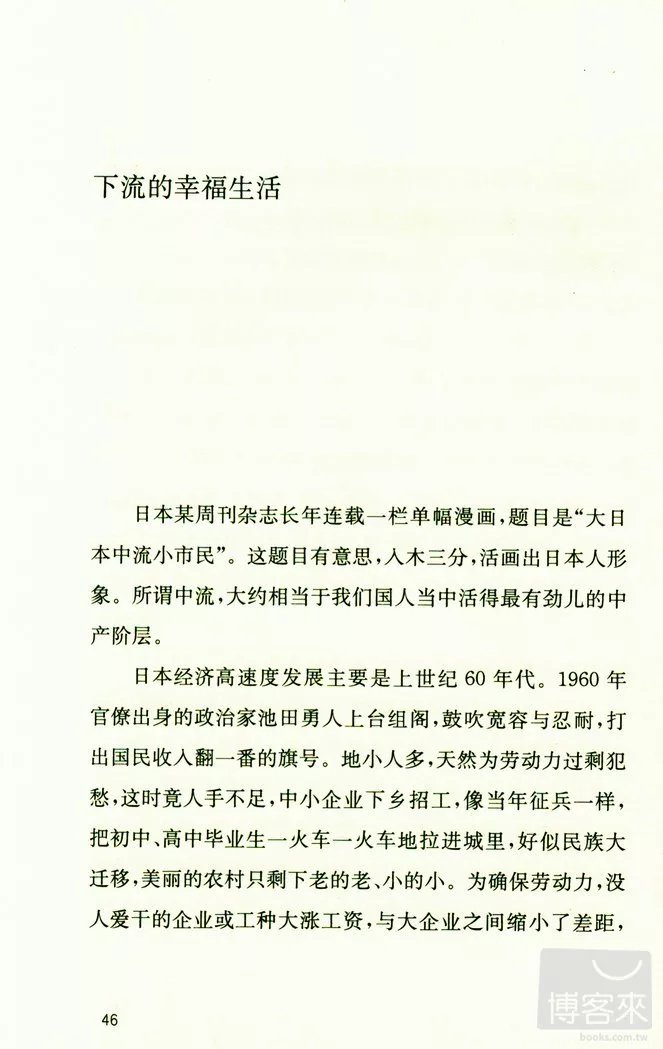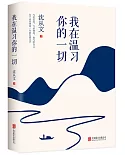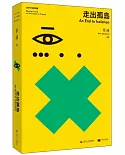本書為旅日作家李長聲先生關于日本文化、文學和書業情狀的隨筆集, 收錄《日本人與諸葛亮》、《江戶熱的死角》、《永井荷風的東京》等文字五十余篇,皆流暢可讀,亦見出作者眼力獨到之處。
本書為32開小精裝系列之一。
目錄
閑談蜀山人(代序)
日本人與諸葛亮
江戶熱的死角
古今糞尿譚
漢字的霸權
推理小說新本格
不領賞的日本作家
“另類”澀澤龍彥
在日
造詞兒
畫眼楮
千石的念法
人與人間
下流的幸福生活
2007年問題
熟年離婚
日本為何窮人多
塞車的學問
譯與不譯之間
新渡戶稻造和他的《武士道》
《今昔物語》的今昔
莫須有的日本文學全集
讀序隨想
讀日本人喝酒
作家的無聊故事
寫真異聞
混浴的感覺
日本文化的時間與空間
東野圭吾黑笑文學獎
本來多麼好的推理
偶遇西村京太郎
日向子畫鬼
《作家應該跟編輯睡覺嗎》
總理的漫畫及白字
一部日本小說與兩度世界危機
《討厭那孩子》
搞笑藝妓
米其林指南東京
漫畫與繪本
綜合雜志的終焉
小說的時問
青春的輕小說
讀書術
編輯造時勢
文字還是要讀的
風俗慎太郎
太宰治的臉
江藤淳遺書
無賴安吾
永井荷風的東京
馬悅然的俳句
作家與學歷
日本人與諸葛亮
江戶熱的死角
古今糞尿譚
漢字的霸權
推理小說新本格
不領賞的日本作家
“另類”澀澤龍彥
在日
造詞兒
畫眼楮
千石的念法
人與人間
下流的幸福生活
2007年問題
熟年離婚
日本為何窮人多
塞車的學問
譯與不譯之間
新渡戶稻造和他的《武士道》
《今昔物語》的今昔
莫須有的日本文學全集
讀序隨想
讀日本人喝酒
作家的無聊故事
寫真異聞
混浴的感覺
日本文化的時間與空間
東野圭吾黑笑文學獎
本來多麼好的推理
偶遇西村京太郎
日向子畫鬼
《作家應該跟編輯睡覺嗎》
總理的漫畫及白字
一部日本小說與兩度世界危機
《討厭那孩子》
搞笑藝妓
米其林指南東京
漫畫與繪本
綜合雜志的終焉
小說的時問
青春的輕小說
讀書術
編輯造時勢
文字還是要讀的
風俗慎太郎
太宰治的臉
江藤淳遺書
無賴安吾
永井荷風的東京
馬悅然的俳句
作家與學歷
序
東渡之初,還曾想專攻日本漢文學史來著。
這是有取巧之心。漢文學,哪怕是學走樣的或者與現實相結合的所謂變體漢文,對于中國人,也應該比現代日本語容易罷,當初就這麼想。記得多年前一位名聞讀書界的學者批評台灣某日本學專家把日文翻譯成中文有如“ 芭蕉的蛤蟆跳池塘”——不通,可其實,專家是照搬了變體漢文。譬如有這樣的七律︰“先生趣似東方朔,玩世年來面白游。一段機嫌酒疑浴,百篇狂詠筆如流。近鄉在町聞風起,遠國波濤結社稠。打犬兒童知寢惚,名高六十有余州。”詩中“面白”、“機嫌”等費解,原來是日本人別出心裁創造的詞語。古時候日本劃分六十八國,也叫州,江戶時代浮世繪大師歌川廣重 (1797—1858)畫有六十余州名勝圖。而詩中這位“寢惚”先生名氣真夠大,連招貓逗狗的兒童都知道,何許人也?
他就是蜀山人。此人和漢融通,雅俗兼具,為人瀟灑,處世達觀,像我們傳說唐伯虎一樣,他死後也變成一個傳說(有些說法就是從中國抄來的,例如舊僕賣紙燈籠,他揮毫題詞,于是乎遠近爭購),與一休和尚齊名。他卒于1823年,據現代文學家永井荷風說,死後一百年,江戶時代雷名一世的名士隨維新以來的時勢漸次被忘卻,唯獨蜀山人聲名依然如故,世人猶珍重其斷簡殘編。然而,又一場戰爭過後,蜀山人湮沒無聞。近年人們對江戶時代及文化感興趣,流為時潮,也幾乎未見蜀山人復出,恐怕原因只在于蜀山人是漢文的。雖然江戶時代最高級文化是漢文,但戰後漢文教育衰退,已經幾代人讀不來漢文。
近代文學家森鷗外的漢文老師依田學海為蜀山人立過小傳,漢文,有雲︰“大田覃,號南畝。幕府人士。好學,善文章,旁作游戲國歌。滑稽詼謔,雖村老野嫗莫不絕倒。世所謂蜀山先生者也。”他生于1749年,十九歲印行《寢惚先生文集》,一舉成名天下知。這個小文集里收錄“狂詩”二十七首。明治以前,說詩就是指漢詩,也叫做唐歌,即中國古典詩。蜀山人學詩,學的是荻生徂徠(1666—1728)一派。徂徠醉心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明朝古文辭派,以模擬為能事,傳到蜀山人,已經是末流,以至于變態。看似漢詩,卻是在搞笑,被稱作狂詩。把什麼都能拿來搞笑,是日本人的天性,但也可說是學詩不走正道。不過,能夠狂起來,玩語言游戲,也表明已然把漢詩文學到家,躍躍由雅倒向俗,借以緩解外來文化的壓抑,松動傳統體制的禁錮。狂詩是古已有之,蜀山人並非始作俑者,但豈止江戶,《寢惚先生文集》也沖擊京都和大阪,一時間狂詩盛行于世,以至定型為滑稽文學之一,所以稱他為鼻祖亦不為過。後來他又戲仿《唐詩選》里的一些詩,刊行狂詩集,例如李白詩《越中覽古》被拿來詠“越中裨”,一種有帶子(紐)的兜襠布(裨)︰“木虱如花滿縫目,只今惟有懷中紐。”狂詩是江戶文化由爛熟走向頹廢的產物,玩世不恭,或許有“以無意義對抗體制意義”的意義。作為時代的寵兒,蜀山人獨領世風,但井水犯河水,文壇領袖被誤植為學界權威,不免慘遭譏諷,譬如精于考據的大田錦城就不把他的漢文放在眼里。蜀山人懷恨,作詩回敬︰“一混巴人下里群,不能詩賦不能文。錦城上客如相許,五月薰風醉此君。”中國文學研究家青木正兒也曾貶斥蜀山人的狂詩是劣等手段的愚作。
狂詩畢竟是漢詩,賞玩者限于讀解漢詩文的知識人,讓“村老野嫗莫不絕倒”的不是狂詩,而是“狂歌”,即“游戲國歌”,也就是滑稽詼謔的和歌。狂歌也是古已有之,蜀山人1775年編纂刊行《萬載狂歌集》,用自己的才氣和熱情使這種游藝變成一種文藝樣式,並風行于世。永井荷風認為“蜀山人的狂歌確然冠古今”。民眾文化追求笑,18世紀中葉狂歌與浮世繪同時勃興,共同之點即在于笑。有如我們熱衷于小品,以富有機智的快活精神享樂文化。但小品是幾個人演給大家看,狂歌則是眾人參與,讀以及作,或許更近乎寫段子、傳段子。笑的文學是現實的文學,時過或境遷就笑不起來,只能讓江戶人自得其樂。用今天的文學尺度裁量,狂歌已不值得鑒賞,這也必定是小品的宿命。
蜀山人自負為天下狂歌名人,因狂歌而成為幕府貪官的嘉賓。“今年三百六十日,半在胡姬一酒樓”,乃至一擲千金,把妓女贖回家當妾。1816年用漢文為小山田與清著《擁書漫筆》作序,有雲︰“清人石龐天外集雲,人生有三樂,一讀書,二好色,三飲酒,此外落落都無是處,奈何奈何。余讀之,不覺擊節,日︰不圖此漢酒飯囊中有如是讀書種子也。”蜀山人追求這三樂,但後來作詩,只說讀書與飲酒之樂︰“欲知六十余年樂,萬卷藏書一酒樽。”原來年將不惑,掌權者更迭,所倚仗的貪官被處死,怕牽連,趕緊從花天酒地抽身,就此訣別了狂歌世界。老老實實當世襲的警衛步卒,每周出勤兩天,余閑則閉門攻讀聖賢書。科考合格,當上一介小文吏。數年後出差大阪官銅主管所一年,這是他生來第一次出門遠行。本來是名人,自然少不了唱和,在那里起了個雅號︰蜀山人。銅,別稱蜀山居士,據說出自清人《事物異名錄》。他還說“不知者以為真號,呵呵”,豈料這“假”名號最叫得響,留傳後世。
蜀山人一生鐘情于漢詩,孜孜不倦,寫下四千七百來首,但詩多好的少,恐怕在江戶時代也只能屬于二三流。七十二歲首次刊印漢詩集《杏園詩集》,序是多年前出差長崎時請一位叫張秋琴的清朝商人事先作好的,贊之為 “東都詩宗”,溢美而已。其中有一首悼長女夭折,可算是好的︰“抱罷明珠掌上空,苦沾雙袖淚痕紅。西窗一夜多風雨,猶似呱呱泣帳中。”與一流漢詩人相比,立見高下,譬如菅茶山——“蜀山人移家于學宮對岸,匾曰緇林,命余詩之”︰“杏壇相對是緇林,吏隱風流寓旨深。每唱一歌人競賞,有誰听取濯纓心。”
我愛讀的是蜀山人隨筆。二十多年前來日本,正好岩波書店在刊行《大田南畝全集》,在圖書館閑翻,竟生出研學日本漢文學史的念頭。美國的日本文學研究家唐納德‧金說︰“人一生之間能閱讀的作品量有限,而且近世隨筆從全體來看也未必能說有值得廣泛研究的高水準。”所以他撰著日本文學史,皇皇十八卷(日譯本),未觸及江戶時代的隨筆。我卻覺得隨筆有知識,有世態人事,比西方人視為正統的小說更有趣,特別是日本的漢文隨筆,讀來更有點孫猴子在人家園子里吃桃子的快活,還敢于指點好壞呢。以前我寫過牽牛花、山茶花之類,其實都是讀蜀山人引發的,他寫有“牽牛花發瓦盆中”、“新花百種斗牽牛”的詩句,還寫有“酌酒而醉,主人請名其居,因名椿亭。客有講本草之學者,難日︰是山茶也,非椿也,流俗承誤,莫知是正”雲雲。樂在讀,讀余也率爾操觚,如今用電腦,常常更率爾。
永井荷風說︰“余常以《伊勢物語》為國文中之精髓,以芭蕉和蜀山人的吟詠為江戶文學的精粹。”但當今日本,無人不知俳聖芭蕉,卻很少人知道蜀山人。研究蜀山人,永井是先驅者,他還把三樂之說抄譯在日記中,但 “石龐”誤為“石龐天”,編者不察,岩波書店版《荷風全集》就這麼印著。石龐,字天外,我也不明不白,所幸終于沒有搞什麼漢文學史,雖然有時也遐想,萬一真搞了,而今說不定也弄個碩導博導的于干。所謂黑了南方有北方,倒也不以己悲。
這是有取巧之心。漢文學,哪怕是學走樣的或者與現實相結合的所謂變體漢文,對于中國人,也應該比現代日本語容易罷,當初就這麼想。記得多年前一位名聞讀書界的學者批評台灣某日本學專家把日文翻譯成中文有如“ 芭蕉的蛤蟆跳池塘”——不通,可其實,專家是照搬了變體漢文。譬如有這樣的七律︰“先生趣似東方朔,玩世年來面白游。一段機嫌酒疑浴,百篇狂詠筆如流。近鄉在町聞風起,遠國波濤結社稠。打犬兒童知寢惚,名高六十有余州。”詩中“面白”、“機嫌”等費解,原來是日本人別出心裁創造的詞語。古時候日本劃分六十八國,也叫州,江戶時代浮世繪大師歌川廣重 (1797—1858)畫有六十余州名勝圖。而詩中這位“寢惚”先生名氣真夠大,連招貓逗狗的兒童都知道,何許人也?
他就是蜀山人。此人和漢融通,雅俗兼具,為人瀟灑,處世達觀,像我們傳說唐伯虎一樣,他死後也變成一個傳說(有些說法就是從中國抄來的,例如舊僕賣紙燈籠,他揮毫題詞,于是乎遠近爭購),與一休和尚齊名。他卒于1823年,據現代文學家永井荷風說,死後一百年,江戶時代雷名一世的名士隨維新以來的時勢漸次被忘卻,唯獨蜀山人聲名依然如故,世人猶珍重其斷簡殘編。然而,又一場戰爭過後,蜀山人湮沒無聞。近年人們對江戶時代及文化感興趣,流為時潮,也幾乎未見蜀山人復出,恐怕原因只在于蜀山人是漢文的。雖然江戶時代最高級文化是漢文,但戰後漢文教育衰退,已經幾代人讀不來漢文。
近代文學家森鷗外的漢文老師依田學海為蜀山人立過小傳,漢文,有雲︰“大田覃,號南畝。幕府人士。好學,善文章,旁作游戲國歌。滑稽詼謔,雖村老野嫗莫不絕倒。世所謂蜀山先生者也。”他生于1749年,十九歲印行《寢惚先生文集》,一舉成名天下知。這個小文集里收錄“狂詩”二十七首。明治以前,說詩就是指漢詩,也叫做唐歌,即中國古典詩。蜀山人學詩,學的是荻生徂徠(1666—1728)一派。徂徠醉心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明朝古文辭派,以模擬為能事,傳到蜀山人,已經是末流,以至于變態。看似漢詩,卻是在搞笑,被稱作狂詩。把什麼都能拿來搞笑,是日本人的天性,但也可說是學詩不走正道。不過,能夠狂起來,玩語言游戲,也表明已然把漢詩文學到家,躍躍由雅倒向俗,借以緩解外來文化的壓抑,松動傳統體制的禁錮。狂詩是古已有之,蜀山人並非始作俑者,但豈止江戶,《寢惚先生文集》也沖擊京都和大阪,一時間狂詩盛行于世,以至定型為滑稽文學之一,所以稱他為鼻祖亦不為過。後來他又戲仿《唐詩選》里的一些詩,刊行狂詩集,例如李白詩《越中覽古》被拿來詠“越中裨”,一種有帶子(紐)的兜襠布(裨)︰“木虱如花滿縫目,只今惟有懷中紐。”狂詩是江戶文化由爛熟走向頹廢的產物,玩世不恭,或許有“以無意義對抗體制意義”的意義。作為時代的寵兒,蜀山人獨領世風,但井水犯河水,文壇領袖被誤植為學界權威,不免慘遭譏諷,譬如精于考據的大田錦城就不把他的漢文放在眼里。蜀山人懷恨,作詩回敬︰“一混巴人下里群,不能詩賦不能文。錦城上客如相許,五月薰風醉此君。”中國文學研究家青木正兒也曾貶斥蜀山人的狂詩是劣等手段的愚作。
狂詩畢竟是漢詩,賞玩者限于讀解漢詩文的知識人,讓“村老野嫗莫不絕倒”的不是狂詩,而是“狂歌”,即“游戲國歌”,也就是滑稽詼謔的和歌。狂歌也是古已有之,蜀山人1775年編纂刊行《萬載狂歌集》,用自己的才氣和熱情使這種游藝變成一種文藝樣式,並風行于世。永井荷風認為“蜀山人的狂歌確然冠古今”。民眾文化追求笑,18世紀中葉狂歌與浮世繪同時勃興,共同之點即在于笑。有如我們熱衷于小品,以富有機智的快活精神享樂文化。但小品是幾個人演給大家看,狂歌則是眾人參與,讀以及作,或許更近乎寫段子、傳段子。笑的文學是現實的文學,時過或境遷就笑不起來,只能讓江戶人自得其樂。用今天的文學尺度裁量,狂歌已不值得鑒賞,這也必定是小品的宿命。
蜀山人自負為天下狂歌名人,因狂歌而成為幕府貪官的嘉賓。“今年三百六十日,半在胡姬一酒樓”,乃至一擲千金,把妓女贖回家當妾。1816年用漢文為小山田與清著《擁書漫筆》作序,有雲︰“清人石龐天外集雲,人生有三樂,一讀書,二好色,三飲酒,此外落落都無是處,奈何奈何。余讀之,不覺擊節,日︰不圖此漢酒飯囊中有如是讀書種子也。”蜀山人追求這三樂,但後來作詩,只說讀書與飲酒之樂︰“欲知六十余年樂,萬卷藏書一酒樽。”原來年將不惑,掌權者更迭,所倚仗的貪官被處死,怕牽連,趕緊從花天酒地抽身,就此訣別了狂歌世界。老老實實當世襲的警衛步卒,每周出勤兩天,余閑則閉門攻讀聖賢書。科考合格,當上一介小文吏。數年後出差大阪官銅主管所一年,這是他生來第一次出門遠行。本來是名人,自然少不了唱和,在那里起了個雅號︰蜀山人。銅,別稱蜀山居士,據說出自清人《事物異名錄》。他還說“不知者以為真號,呵呵”,豈料這“假”名號最叫得響,留傳後世。
蜀山人一生鐘情于漢詩,孜孜不倦,寫下四千七百來首,但詩多好的少,恐怕在江戶時代也只能屬于二三流。七十二歲首次刊印漢詩集《杏園詩集》,序是多年前出差長崎時請一位叫張秋琴的清朝商人事先作好的,贊之為 “東都詩宗”,溢美而已。其中有一首悼長女夭折,可算是好的︰“抱罷明珠掌上空,苦沾雙袖淚痕紅。西窗一夜多風雨,猶似呱呱泣帳中。”與一流漢詩人相比,立見高下,譬如菅茶山——“蜀山人移家于學宮對岸,匾曰緇林,命余詩之”︰“杏壇相對是緇林,吏隱風流寓旨深。每唱一歌人競賞,有誰听取濯纓心。”
我愛讀的是蜀山人隨筆。二十多年前來日本,正好岩波書店在刊行《大田南畝全集》,在圖書館閑翻,竟生出研學日本漢文學史的念頭。美國的日本文學研究家唐納德‧金說︰“人一生之間能閱讀的作品量有限,而且近世隨筆從全體來看也未必能說有值得廣泛研究的高水準。”所以他撰著日本文學史,皇皇十八卷(日譯本),未觸及江戶時代的隨筆。我卻覺得隨筆有知識,有世態人事,比西方人視為正統的小說更有趣,特別是日本的漢文隨筆,讀來更有點孫猴子在人家園子里吃桃子的快活,還敢于指點好壞呢。以前我寫過牽牛花、山茶花之類,其實都是讀蜀山人引發的,他寫有“牽牛花發瓦盆中”、“新花百種斗牽牛”的詩句,還寫有“酌酒而醉,主人請名其居,因名椿亭。客有講本草之學者,難日︰是山茶也,非椿也,流俗承誤,莫知是正”雲雲。樂在讀,讀余也率爾操觚,如今用電腦,常常更率爾。
永井荷風說︰“余常以《伊勢物語》為國文中之精髓,以芭蕉和蜀山人的吟詠為江戶文學的精粹。”但當今日本,無人不知俳聖芭蕉,卻很少人知道蜀山人。研究蜀山人,永井是先驅者,他還把三樂之說抄譯在日記中,但 “石龐”誤為“石龐天”,編者不察,岩波書店版《荷風全集》就這麼印著。石龐,字天外,我也不明不白,所幸終于沒有搞什麼漢文學史,雖然有時也遐想,萬一真搞了,而今說不定也弄個碩導博導的于干。所謂黑了南方有北方,倒也不以己悲。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