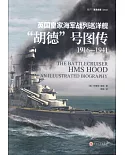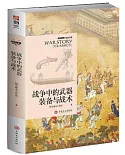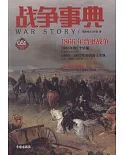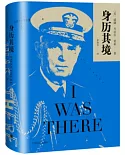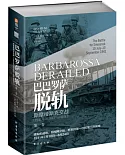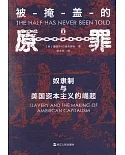本書為“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系列叢書”之一,是作者近十年來相關國際關系方面的論文匯集,共29篇。作者由于從科學的角度出發看待國際政治,其出發點和理論深度均高于國內大部分學者,論文反映了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領域的最新理論動態和研究方向。
張睿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關系碩士,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政治學博士。南開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博導,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國學會、天津政治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治學會理事;清華大學《國際政治科學》學術委員會委員暨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雜志編輯委員會成員;北京大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美國多米尼肯大學、韓國天主教大學客座教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訪問學者。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有︰國際關系理論與當代國際關系、美國外交政策與中美關系、社會科學方法論等。
目錄
逆水行舟三十載(代序)
冷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
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評《世界新秩序與新興大國的歷史抉擇》
也談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思想及其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
關于中國“入世”的政治思考
思想教育工作的他山之石
撲朔迷離看世界
丟掉幻想、自尊自強是對待中美關系的關鍵
關于我國政治學高等教育學科設置和劃分的幾點看法
鷹派崛起——美國翹起尾巴
“9‧11”如何改變了美國
“沉著應對”與“自廢武功”——就如何應對美國國家導彈防御計劃同時殷弘先生商榷
“藍軍”陰影下的布什對華政策
“人道干涉”神話與美國意識形態
保守主義的淵源及其在美國的演進
我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存在的若干問題
從“對日新思維”看中國的國民性和外交哲學
現實主義的持久生命力
美國霸權的正當性危機
美國大選與競選辯論
伊拉克的國際玩笑
我們為什麼不能接受中美關系“歷史最好”的說法?
中國究竟值不值得美國焦慮?
警惕西方列強以“人道干預”為名顛覆現行國際秩序
“美國世紀”真的玩兒完了嗎?
冷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
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評《世界新秩序與新興大國的歷史抉擇》
也談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思想及其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
關于中國“入世”的政治思考
思想教育工作的他山之石
撲朔迷離看世界
丟掉幻想、自尊自強是對待中美關系的關鍵
關于我國政治學高等教育學科設置和劃分的幾點看法
鷹派崛起——美國翹起尾巴
“9‧11”如何改變了美國
“沉著應對”與“自廢武功”——就如何應對美國國家導彈防御計劃同時殷弘先生商榷
“藍軍”陰影下的布什對華政策
“人道干涉”神話與美國意識形態
保守主義的淵源及其在美國的演進
我國國際關系學科發展存在的若干問題
從“對日新思維”看中國的國民性和外交哲學
現實主義的持久生命力
美國霸權的正當性危機
美國大選與競選辯論
伊拉克的國際玩笑
我們為什麼不能接受中美關系“歷史最好”的說法?
中國究竟值不值得美國焦慮?
警惕西方列強以“人道干預”為名顛覆現行國際秩序
“美國世紀”真的玩兒完了嗎?
序
我生不逢時,高中沒畢業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學業被迫中斷,人被送往農本寸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荒廢了人生中最寶貴的8年青春,這8年本來是可以為造就一個科學家奠定基礎的。不過比起那麼多早我10年倒霉、一生都被運動所毀的才華橫溢的年輕人,我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只被耽誤了10年,一代人的瘋狂(反右、大躍進、“文革”)結束時我還不到30歲,還來得及重新開始。對于太多的不幸者而言,一生的悲劇已經鑄成,變革來得太晚了。
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愚民的年代。知識不僅毫無用處——知識的社會價值非但被人為地貶低到零點以下,而且還可能給人帶來麻煩——“知識越多越反動”。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我當然對那個年代知識分子不斷無端遭受迫害有切膚之痛。然而,一方面出于一種與生俱來的求知欲,一方面出于一種期盼中國不會永遠如此的模糊信念,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最困難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堅持自學,義無反顧地往“臭老九”的隊伍里擠。那時自學最大的困難在于書籍的缺乏,圖書館的書燒的燒、封的封,除了少數例外,絕大多數人文社科類書籍都是禁書。我們想方設法,跟當時龐大而又復雜的“內部發行”、“內部閱覽”系統玩起危險而又刺激的捉迷藏游戲,或買、或借,千方百計地把一切有可能搞到的書搞到手,饑不擇食地讀完一切可以搞到手的書籍。就這樣,當我的絕大多數同齡人都在被迫虛度時光時,我不甘听憑命運的安排,頑強抗爭,精讀了大量文史哲和政治、經濟類著作,並堅持自學外語,決不放棄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機會。
艱苦不懈的努力終于贏得了回報。1979年我以優異成績考取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首屆碩士研究生。我必須說我很感謝改革開放之初的靈活招生政策,它允許我以同等學力報考。這樣,盡管從未上過大學,憑借我在“文革”十年中自學的積累,我自覺在文科基礎學科方面的學識不輸“文革”中畢業的所謂“工農兵大學生”,甚至堪比“文革”前人學的“老大學生”,所以才敢跳過大學本科直接報考研究生,以追回那段失去的歲月。這就是我的履歷上有研究生學歷卻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原因,以致後來無論國內國外,每次為人學、求職、提升等目的填表時,都要費事解釋何以大學本科是空白。
那時的研究生,跟現在真有天壤之別。高考恢復後的頭兩年里,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全國也不過區區數百人,不像現在動輒數以十萬計,連博士都是批量生產。物以稀為貴。當年的一個碩士研究生,比現在留洋的海歸博士都更稀罕、更金貴,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兩年之後畢業,留所工作,在美國研究室專攻美國經濟。再過兩年,被評為助理研究員(相當于高校講師),獲得了專業技術人員的中級職稱。那是“文革”結束後首次恢復職稱評定(上一次是1956年),所以相當隆重,全國高校及研究機構一體遵行。我當年拿到的“職稱證書”就是全國統一樣式的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人事部”大印的綠皮護照式證件,有人戲稱為“全國糧票”,以區別于後來將職稱評定權下放分散到省/直轄市教委和教育部直屬高校後的“地方糧票”。正因為後來權力下放,那一次就成了“文革”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全國統一職稱評定,而我的“國家”職稱證書也就成了有收藏價值的“絕版”。
那時的研究生稀罕,那時的教授也稀罕,還沒出現如今“教授多如狗、大師滿地走”的繁榮興旺局面。教授和研究生都稀罕,其他職稱自然也水漲船高,一個助理研究員或講師在當時還挺是個人物。當年,30剛出頭的時候,我就獲得了碩士學位(當時國內最高學位),評上了中級職稱,與我的同時代人相比(他們中的佼佼者也大多還在大學念本科),可以說是搶佔了先機,進入了快車道。記得那時參加一些全國性的學術會議,與會專家多為“文革”前參加工作四十出頭的人,學界在30 -45這個年齡段出現了專門人才的斷層,而我恰恰是這個年齡段里鳳毛麟角的漏網之魚,所以頗有些引人注目。尤其在一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是少數能用英語發言、直接與國外學者對話的中方學者,更帶了點“嶄露頭角”的意思;加上常在學術刊物和新聞媒體上發文,當時在美國經濟和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圈內還有了一點小小的知名度。一切跡象表明,如果我選擇留在國內發展,面前將是一條前程遠大的坦途。
可是我沒有。我毅然中斷了我那前景光明的學術生涯,選擇了去國外留學的艱難旅途。這還得從我打小的志向和我當時工作的性質說起。
我很小的時候,大概也就是剛上小學不久吧,就立志要當科學家。那時和後來很長時間里這件事在我看來是如此自然、如此理所當然,簡直就沒有想過還有別的生活道路。我以為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樣,都是想要成“家”的,不是科學家,至少也是個文學家、政治家之類。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有許多人從小壓根就沒想過當什麼家,他們的志向很樸實,就是當個工人、技術員、售貨員、老師什麼的,或者是轉個城市戶口,也就心滿意足了。我可不。打小我就愛看科學家傳記和科學發明的故事,憧憬著有朝一日也能在科學史上寫下自己的一頁。甚至連殘酷的“文革”都未能粉碎我這份夢想,雖然學業的中斷和自學的困難迫使我放棄了成為一名真正(即自然)科學家的奢望(自然科學很難自學成才)而轉向社會“科學”但成“家”的念頭卻從未泯滅。
……
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愚民的年代。知識不僅毫無用處——知識的社會價值非但被人為地貶低到零點以下,而且還可能給人帶來麻煩——“知識越多越反動”。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我當然對那個年代知識分子不斷無端遭受迫害有切膚之痛。然而,一方面出于一種與生俱來的求知欲,一方面出于一種期盼中國不會永遠如此的模糊信念,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最困難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堅持自學,義無反顧地往“臭老九”的隊伍里擠。那時自學最大的困難在于書籍的缺乏,圖書館的書燒的燒、封的封,除了少數例外,絕大多數人文社科類書籍都是禁書。我們想方設法,跟當時龐大而又復雜的“內部發行”、“內部閱覽”系統玩起危險而又刺激的捉迷藏游戲,或買、或借,千方百計地把一切有可能搞到的書搞到手,饑不擇食地讀完一切可以搞到手的書籍。就這樣,當我的絕大多數同齡人都在被迫虛度時光時,我不甘听憑命運的安排,頑強抗爭,精讀了大量文史哲和政治、經濟類著作,並堅持自學外語,決不放棄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機會。
艱苦不懈的努力終于贏得了回報。1979年我以優異成績考取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首屆碩士研究生。我必須說我很感謝改革開放之初的靈活招生政策,它允許我以同等學力報考。這樣,盡管從未上過大學,憑借我在“文革”十年中自學的積累,我自覺在文科基礎學科方面的學識不輸“文革”中畢業的所謂“工農兵大學生”,甚至堪比“文革”前人學的“老大學生”,所以才敢跳過大學本科直接報考研究生,以追回那段失去的歲月。這就是我的履歷上有研究生學歷卻沒有大學本科學歷的原因,以致後來無論國內國外,每次為人學、求職、提升等目的填表時,都要費事解釋何以大學本科是空白。
那時的研究生,跟現在真有天壤之別。高考恢復後的頭兩年里,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全國也不過區區數百人,不像現在動輒數以十萬計,連博士都是批量生產。物以稀為貴。當年的一個碩士研究生,比現在留洋的海歸博士都更稀罕、更金貴,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兩年之後畢業,留所工作,在美國研究室專攻美國經濟。再過兩年,被評為助理研究員(相當于高校講師),獲得了專業技術人員的中級職稱。那是“文革”結束後首次恢復職稱評定(上一次是1956年),所以相當隆重,全國高校及研究機構一體遵行。我當年拿到的“職稱證書”就是全國統一樣式的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人事部”大印的綠皮護照式證件,有人戲稱為“全國糧票”,以區別于後來將職稱評定權下放分散到省/直轄市教委和教育部直屬高校後的“地方糧票”。正因為後來權力下放,那一次就成了“文革”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全國統一職稱評定,而我的“國家”職稱證書也就成了有收藏價值的“絕版”。
那時的研究生稀罕,那時的教授也稀罕,還沒出現如今“教授多如狗、大師滿地走”的繁榮興旺局面。教授和研究生都稀罕,其他職稱自然也水漲船高,一個助理研究員或講師在當時還挺是個人物。當年,30剛出頭的時候,我就獲得了碩士學位(當時國內最高學位),評上了中級職稱,與我的同時代人相比(他們中的佼佼者也大多還在大學念本科),可以說是搶佔了先機,進入了快車道。記得那時參加一些全國性的學術會議,與會專家多為“文革”前參加工作四十出頭的人,學界在30 -45這個年齡段出現了專門人才的斷層,而我恰恰是這個年齡段里鳳毛麟角的漏網之魚,所以頗有些引人注目。尤其在一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是少數能用英語發言、直接與國外學者對話的中方學者,更帶了點“嶄露頭角”的意思;加上常在學術刊物和新聞媒體上發文,當時在美國經濟和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圈內還有了一點小小的知名度。一切跡象表明,如果我選擇留在國內發展,面前將是一條前程遠大的坦途。
可是我沒有。我毅然中斷了我那前景光明的學術生涯,選擇了去國外留學的艱難旅途。這還得從我打小的志向和我當時工作的性質說起。
我很小的時候,大概也就是剛上小學不久吧,就立志要當科學家。那時和後來很長時間里這件事在我看來是如此自然、如此理所當然,簡直就沒有想過還有別的生活道路。我以為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樣,都是想要成“家”的,不是科學家,至少也是個文學家、政治家之類。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有許多人從小壓根就沒想過當什麼家,他們的志向很樸實,就是當個工人、技術員、售貨員、老師什麼的,或者是轉個城市戶口,也就心滿意足了。我可不。打小我就愛看科學家傳記和科學發明的故事,憧憬著有朝一日也能在科學史上寫下自己的一頁。甚至連殘酷的“文革”都未能粉碎我這份夢想,雖然學業的中斷和自學的困難迫使我放棄了成為一名真正(即自然)科學家的奢望(自然科學很難自學成才)而轉向社會“科學”但成“家”的念頭卻從未泯滅。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