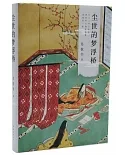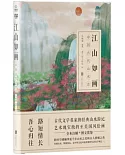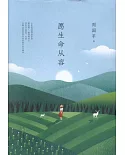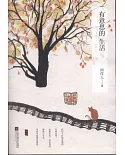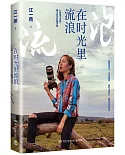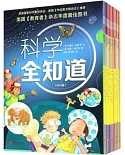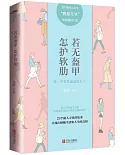這本書文字所及,其實就是我的生活。讀書、工作、閱城、觀劇,波瀾不興,不過如此。所可觀的大抵是其中尚有一些平常人生的悟得,還算「別致」,或能以此自為珠玉之沽,求善賈於一二同道共鳴者罷。
1999年底出過一本《無心小築初集》,到現在快十年了,以為「初集」成了「末集」。中間有數年擱筆,世風所向,本業拘泥,甚覺原先期期然於小文章無益、無用,近年拾筆重來,已知必得「回歸」,還是離不開,做文即生活,實在可給予我小世界里以大乾坤的。這本書所收多為近年工余所寫,其實算是「二集」,因以當年有關「初集」的一篇感想義字代序,就此續上我做文之前緣,或還貼切。
寫作漸由一種有心的醞釀變成生活的實在部分了,現在寫得自然,並不占很多「額外」日寸間,無需別蓄情緒。就像之於深圳,漸漸有些喜歡,因為熟習了罷,雖然還覺這里不夠多樣多情,有時會有故園之思,還有居身其間又將怨懟厭棄之作為時髦的隱約氛圍,但畢竟居久,知道這城市有她的好。假如我在別處,會是京城如海人叢中淹沒的一滴?滬上輕巧享樂里冷清的外人?抑或金陵滯緩節奏間不協的音符?連原本數欲「逃離」本城、對雲南心向往之的朋友后來也說,彼地日照尤烈、空氣太干,久居不可忍。於是現在竟也會想,「大抵以后永遠是這城市的人了」。
這本書所以想獻給深圳。
目錄
書前
「初集」的經驗(代序)
輯一 書事
誰家的舊時月色
某某輕佻
常識
讀書記感一則
食古
詩意在長夏
「一生為故國招魂」
長使英雄淚滿襟
書固風雅事
帶一本書出門
今古奇觀
道不同
羅曼蒂克
小說之「進城」
「銀魚」非魚
游於藝
喜歡這個「老頭」了
「第二手」禁書
小說夢
詠而歸
靈魂的安居
寫作著是美麗的
非一般肚腸
「很奇怪,現在的人連這一點都不理解」
子路
「認死理」
「香菇文化」
且將沉醉換悲涼
「少不宜讀近代史」
晚清的鐵路之議
想象賣燒肉粽的李安
過去的教師
《廣東新語》
果日
宮室之木
愛東坡
┅┅
輯二 城記
輯三 戲感
輯四 時議
輯五 游蹤
書後
「初集」的經驗(代序)
輯一 書事
誰家的舊時月色
某某輕佻
常識
讀書記感一則
食古
詩意在長夏
「一生為故國招魂」
長使英雄淚滿襟
書固風雅事
帶一本書出門
今古奇觀
道不同
羅曼蒂克
小說之「進城」
「銀魚」非魚
游於藝
喜歡這個「老頭」了
「第二手」禁書
小說夢
詠而歸
靈魂的安居
寫作著是美麗的
非一般肚腸
「很奇怪,現在的人連這一點都不理解」
子路
「認死理」
「香菇文化」
且將沉醉換悲涼
「少不宜讀近代史」
晚清的鐵路之議
想象賣燒肉粽的李安
過去的教師
《廣東新語》
果日
宮室之木
愛東坡
┅┅
輯二 城記
輯三 戲感
輯四 時議
輯五 游蹤
書後
序
我的一本書叫《無心小築初集》。這本「初集」出來,才真正體會到出書是做文之人的一大情結,解不開繞不過,一點也不能脫俗。所謂「敝帚自珍」,這種看似「寒酸」的情緒,現在變得可以理解。原先嘗於心下存着的一點「清高」,對他人切切地自出集子不以為意,看來未然。這是出這本書的第一收獲。
我看呂思勉先生的《呂著中國通史》,對人的社群性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人不可忘了這樣「群居」的本性,其實是極需要被了解與被理解,需要被承認與被接納的。唯此,便需要給別人了解與承認的機會,這不算落俗。他人可以選擇欣賞與理解很多人,通常不會去選擇一個「孤芳自賞」的人,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
很久以前也想象過出書之后的一些情形。譬如那時讀了被稱作「台灣第一ˉ才子」的張繼高先生的書,知道其一生堅守「三不原則」,即「不出書、不教書、不上電視」。我並非效顰,也曾在席上與同道揚言過自己出書的「三不」:不放相片、不簽名售書、不贈書。張繼高先生的書是身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他生前從政,也寫不少小文,因不是專門文章家,不甚講究文采格局,只表達思想見識,讀起來感覺卻非常好。我業余為文的狀態與其略有通處,所以可以有自己的「三不」。現在看來前兩項可以做到了,且順乎心意,並不勉強;后一項卻已失效。當日想到「不贈書」,並非出於一種「驕傲」,或覺這書將如何好,只是覺得今人已是「書非買不能讀」,關注之人自然會尋了來看;意不在此的,贈了也不會看,今后那書又不知會怎樣流落,徒增笑柄,不如「藏拙」的好。如今書出來,便知道不贈不可能,原先的主意竟也大變,想到此書於己最大的好處便是,自此有了一樣具有自己特定標識的東西,正可作饋贈親友的「禮物」。
此外還有「一不」,是私下里才有的意念,就是不請人作序。因想着請人作序,這人若是相識,寫好不是,寫壞也不是,替人着想,不去為難人家也罷。那些自己心向往之的學人,倒希得其提攜的,卻一無相識,求序何從。這「一不」既未先說,后來也就自變。聞姜威君為平江鍾叔河先生待作小友,因我向來對前輩學人存仰慕之心,遂央其向鍾先生求序。鍾先生早已公開聲明不再為人作序,卻回了一信,並同意以信代序。得了這信,我是極感幸運的。鍾先生做學問及做文章的品格與尺度,雖則我遠為小輩,也是引為靈犀相通的。我以為鍾先生的文章乃至待人處世,有一種老實與坦然,並不刻意隱藏或偽飾,作為一代學人,這是他們身上十分寶貴的東西。
幾年前我在澳洲一個影城坐了據稱是全世界最驚險的過山車。那時有很大的「胃口」要冒險和刺激。可是那過山車實在太驚險,我感覺自己被拋人了一個近乎瘋狂的境地,情況不由控制,只能堅持。這一次「歷險」幾乎摧毀了我的「胃口」,幾年來有很多次可以玩過山車,雖然相比之下要緩和很多,雖然有些只是兒童式的淺淺的游戲,也仍是害怕,害怕那種被甩出去的感覺.其實人生當中有很多事情就如登上這過山車一樣,關鍵之處只在上與不上那一刻的選擇,可能驚險性更有過之,卻不一定都可以有驚無險了。假如我們被甩出去,更多的可能只是聽天由命,或者隨遇而安。
這個比喻太緊要,不能用來形容出書的過程,不過出書一旦進人那個系統,很多情況也一樣是不由己控制了。原來在腦中勾畫出的若干理想的書的模樣,出來后常常迥異。這不是出書過程中的不好,而正是人生中許多事情的運行原則在出書上的一個印證。我出書前做了很多思想准備,甚至后來交給人家不理了,現在「初集」這本書的模樣不致使我不安,我已經覺得對自己可交代。
「初集」就像初戀,我看着這本書,知道里面的青澀滋味以后不會再有,那些文字形成中的認真與執著以后也不會重復。不再有也好,其實那樣的青澀滋味我是盡力要消除的,以后做文,我會讓自己與文章都舒展起來。
……
我看呂思勉先生的《呂著中國通史》,對人的社群性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人不可忘了這樣「群居」的本性,其實是極需要被了解與被理解,需要被承認與被接納的。唯此,便需要給別人了解與承認的機會,這不算落俗。他人可以選擇欣賞與理解很多人,通常不會去選擇一個「孤芳自賞」的人,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
很久以前也想象過出書之后的一些情形。譬如那時讀了被稱作「台灣第一ˉ才子」的張繼高先生的書,知道其一生堅守「三不原則」,即「不出書、不教書、不上電視」。我並非效顰,也曾在席上與同道揚言過自己出書的「三不」:不放相片、不簽名售書、不贈書。張繼高先生的書是身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他生前從政,也寫不少小文,因不是專門文章家,不甚講究文采格局,只表達思想見識,讀起來感覺卻非常好。我業余為文的狀態與其略有通處,所以可以有自己的「三不」。現在看來前兩項可以做到了,且順乎心意,並不勉強;后一項卻已失效。當日想到「不贈書」,並非出於一種「驕傲」,或覺這書將如何好,只是覺得今人已是「書非買不能讀」,關注之人自然會尋了來看;意不在此的,贈了也不會看,今后那書又不知會怎樣流落,徒增笑柄,不如「藏拙」的好。如今書出來,便知道不贈不可能,原先的主意竟也大變,想到此書於己最大的好處便是,自此有了一樣具有自己特定標識的東西,正可作饋贈親友的「禮物」。
此外還有「一不」,是私下里才有的意念,就是不請人作序。因想着請人作序,這人若是相識,寫好不是,寫壞也不是,替人着想,不去為難人家也罷。那些自己心向往之的學人,倒希得其提攜的,卻一無相識,求序何從。這「一不」既未先說,后來也就自變。聞姜威君為平江鍾叔河先生待作小友,因我向來對前輩學人存仰慕之心,遂央其向鍾先生求序。鍾先生早已公開聲明不再為人作序,卻回了一信,並同意以信代序。得了這信,我是極感幸運的。鍾先生做學問及做文章的品格與尺度,雖則我遠為小輩,也是引為靈犀相通的。我以為鍾先生的文章乃至待人處世,有一種老實與坦然,並不刻意隱藏或偽飾,作為一代學人,這是他們身上十分寶貴的東西。
幾年前我在澳洲一個影城坐了據稱是全世界最驚險的過山車。那時有很大的「胃口」要冒險和刺激。可是那過山車實在太驚險,我感覺自己被拋人了一個近乎瘋狂的境地,情況不由控制,只能堅持。這一次「歷險」幾乎摧毀了我的「胃口」,幾年來有很多次可以玩過山車,雖然相比之下要緩和很多,雖然有些只是兒童式的淺淺的游戲,也仍是害怕,害怕那種被甩出去的感覺.其實人生當中有很多事情就如登上這過山車一樣,關鍵之處只在上與不上那一刻的選擇,可能驚險性更有過之,卻不一定都可以有驚無險了。假如我們被甩出去,更多的可能只是聽天由命,或者隨遇而安。
這個比喻太緊要,不能用來形容出書的過程,不過出書一旦進人那個系統,很多情況也一樣是不由己控制了。原來在腦中勾畫出的若干理想的書的模樣,出來后常常迥異。這不是出書過程中的不好,而正是人生中許多事情的運行原則在出書上的一個印證。我出書前做了很多思想准備,甚至后來交給人家不理了,現在「初集」這本書的模樣不致使我不安,我已經覺得對自己可交代。
「初集」就像初戀,我看着這本書,知道里面的青澀滋味以后不會再有,那些文字形成中的認真與執著以后也不會重復。不再有也好,其實那樣的青澀滋味我是盡力要消除的,以后做文,我會讓自己與文章都舒展起來。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