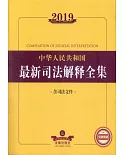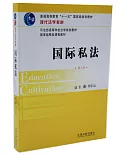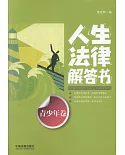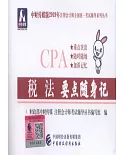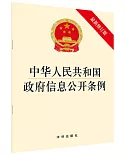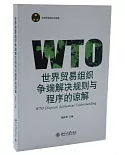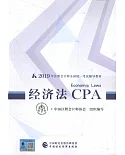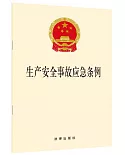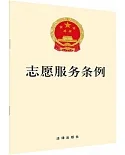隨著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有關文化交流方面的文章和書籍也日益增多。近日,上海政法學院教授田濤先生完成的《接觸與踫撞》一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這也是一部有關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書,但不同于以往的是側重于法律文化。人類在各自封閉的地域環境中發展著不同的法律文化,當西方人在16世紀發現了中國的時候,隨著接觸與踫撞,首先遇到的是法律沖突,于是東西方的法律從此走向整合。本書以獨特的視角揭示了這一沖突的過程,作者用百余幅鮮為人知的珍貴圖文資料,為我們描述了那一段被遺忘了的歷史。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田濤先生利用在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講學的機會,通過尋訪當地圖書館、檔案館以及大小藏書館,收集到很多有關描述中國法律的資料,這些資料記錄了十六世紀以來西方航海家、探險家、外交使節、畫家、商人、傳教士等等不同身份的人,在他們與東方接觸過程中以自己的視角看到的中國法律,以文字或美術作品的形式保存下來,有銅版畫、水彩畫、燈草畫等不同形式,畫面栩栩如生。西方人對當時中國法律的認知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這為我們法律史學研究提供了客觀而寶貴的資料。
本書按照時間脈絡向我們展示了中西方法律從早期的接觸、踫撞,逐步走向融合的過程,能夠為我們更全面地學習中國法律史和做好比較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錄
風從西邊來(代序) 田濤
接觸與踫撞之一
——當西方遇到東方(1 517 1793)
接觸與踫撞之二
——失之交臂的握手(1793 1911)
接觸與踫撞之三
——酷刑下的中國人
接觸與踫撞之四
威妥瑪與《文件自邇集》
接觸與踫撞之五
——死刑與私刑
後記
參考書目
接觸與踫撞之一
——當西方遇到東方(1 517 1793)
接觸與踫撞之二
——失之交臂的握手(1793 1911)
接觸與踫撞之三
——酷刑下的中國人
接觸與踫撞之四
威妥瑪與《文件自邇集》
接觸與踫撞之五
——死刑與私刑
後記
參考書目
序
小時候我住在北京的宣武門外,上學的路上必須要穿過宣武門城門洞,再向東沿順城街一直走到南新華街,出和平門才能到我就讀的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小學,在當時,這可是北京城里最著名的小學校了。因此,整個小學期間,一早一晚,我都要看到高大的宣武門和與之比鄰的天主教南堂。
宣武門是明朝永樂年間建造的,用巨大的石塊和青磚壘成城垣。城垣之上樓分兩層,綠色琉璃瓦蓋頂,金黃色琉璃瓦包邊,一抱多粗的木柱支撐著勾心斗角的大屋頂,斑駁陸離的門窗透著歷史的滄桑。離城樓不遠便是著名的天主教南堂,又叫做“無玷始胎聖母堂”,俗稱宣武大教堂。相傳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獲準在京居住,即以五百金,大概就是五百兩白銀,在宣武門外購地建屋,開始在此傳播宗教。不久利瑪竇又買下附近的“首善書院”,改建成一座天主教堂。“首善書院”原為東林黨人在京的以文會友之地,就是傳說中標榜“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那幫酸秀才們湊在一起侃大山的所在。至萬歷三十八年利瑪竇所建教堂落成。據明代劉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稱︰“堂在宣武門內東城隅,大西洋奉耶穌教者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神宗給廩,賜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狹長,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詭異,其國藻也。供耶穌像其上,畫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把渾天儀,右叉指若方論說次,指所說者。須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準,目容有矚,口容有聲,中國畫繪事所不及。所具香燈蓋幃,修潔異狀。右聖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兒,耶穌也。衣非縫制,自頂被體,供具如左。” [1]此後清順治七年(1650),皇帝御賜白銀一千萬兩準許傳教士湯若望重新修建該教堂。這是一座20 余米高的巴羅克式的教堂,教堂中設一高大的穹廬圓頂,上設十字架。建成後曾兩度被毀,並于康熙時再度重建,清代初期宣武門的南堂曾經是當時北京城里的最高的建築之一。
我听老輩人說過,想當初洋人蓋這個教堂的時候,國人紛紛反對,皇帝也不許教堂的高度超過當時宣武門的城樓。教堂蓋完之時,還沒有立上十字架,經人測算的結果是宣武門城樓高,一時龍顏大悅,百姓晏然,皆大歡喜。過了不久洋人又在教堂的屋頂悄悄地安了一個十字架,這下子可就超過了宣武門城樓,從此引發國人不滿。更為嚴重的還有人說,自從南堂洋人十字架高過宣武門,洋人就把國人給壓了下去。小時候我對此有些疑惑,但老輩人信誓旦旦地說,中國人自打那時候起就開始走背字,同時還告誡我“這是在論的”,不能有絲毫的疑惑。“在論的”是北京的一句土話,大意是說這是經過上面的人論證過的結論,是權威的、不容置疑的。至于經過了哪些權威的論證,因為不容置疑,所以從來沒有人去追究或者深思過。
然而我還是偷偷地用我的眼楮去觀察去比較。說來也怪,每當我站在宣武門內順城街的街頭自東向西看,結果是宣武門城樓明顯的要比教堂的十字架高;但當我換個位置,自西向東看,結果是教堂的十字架明顯高于宣武門城樓。我對此也曾百思不得其解,似乎中了什麼人的障眼法,看來看去就是斷不出一個究竟。過了不久,街頭一批帶著紅衛兵袖章的人爬到教堂上,將高大的十字架拆了下來,我看見滿街揮舞著紅色的旗幟,我听見無數個市民站在街頭歡呼,從此,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宣武門的城樓不但要高過教堂的穹頂,而且顯得分外的高大和雄偉。後來我響應號召上山下鄉,在無數人的振臂高呼和滿街揮舞的紅旗中,離開了自幼熟悉的北京。在饑餓、勞累與困苦中,我每天必須想到的是如何生存下去,此時無論是宣武門的城樓還是巴洛克式的教堂都被我忘得一干二淨。
20 世紀70 年代我從黃河之濱回到北京,結束了將近十年夢魘般的上山下鄉的生活,開始尋求我人生新的道路。這時的我自認為已經成熟了許多,自認為有了自己判斷的能力,于是我再度去尋訪宣武門,可惜18 世紀的法國掛毯制造商從中華帝國獲得靈感,本圖中描繪了高貴的統治者威嚴地坐在寶座上,萬物都匍匐在他的面前,寶座後面是一只裝飾華麗的大象。
宣武門高大的城樓和那滿目瘡痍的城垣全都不在了。為了修建地鐵工程和“備戰、備荒”的需要,城樓和城垣被一起拆除了,城磚運去修建防空洞了,綠色和金黃色的琉璃瓦也不見了蹤影。然而當初由西方傳教士修建的巴洛克式的教堂還在,光禿禿的穹頂上不見了高大的十字架,顯得不倫不類,像一口巨大的灰黑色的鐵鍋倒扣在上面,迎著太陽,反射出鐵灰色的幽暗的光。我無法比較孰高孰低,因為我失去了可以參照的標準。不見了雄偉的宣武門,不見了高大的十字架,不見了滿街飛舞的紅旗,不見了振臂高呼的人群,然而在內心深處,我卻更加陷入了新的躊躇與迷茫。
我終于明白了為什麼教堂的十字架要蓋得那麼高,明白了象征著封建皇權的城樓要建得那麼高,明白了廟里的浮屠要建得那麼高,明白了清真寺的尖塔要建得那麼高。所有的有資格建造這些的人,都有這樣的話語權,他們要麼是天之子,要麼就是天的使臣,他們可以和上天溝通,唯有他們能夠“與天為鄰”。
從此以後我開始尋找能夠衡量我自己人生的尺度,衡量我周圍所有社會現象的尺度。或者失去了的不會再重新擁有,或者在尋覓中發現新的收獲,我堅信應該有一個標準,一個能讓天下人信服的標準,一個重新塑造我們民族自信的標準。在日本東京郊區的山頂上,一座設計和裝幀分外精巧的廟宇中,懸掛著一口產自中國的古鐘,那上面鑄造著幾行清晰的文字 ︰“以我法為法,法即是法,法外無法。”顯然這是一種標準,與其說是佛學的標準,不如說是世俗社會的標準。我心下竊想,千余年以前,日本國“效仿唐法”時期,不僅以唐代律令為治國之本,還應該引進了源自中國的文化,甚至包括間接取自中國的宗教文化。當然這座日本式的廟宇是建在山上,廟中還有一座密檐式木結構的佛塔,塔頂上鎦金的法器在日光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在法國西南部聖城路德教堂旁邊,我看見沿途描述耶穌受難情景的曲折道路,向山頂上痛苦地延伸,山頂上建有高大的哥特式教堂,一座座用磚塊和石塊築成的尖塔努力地伸向天空,似乎要將這些尖塔化成一個個臂膀去撫摸空中的浮雲。有人說哥特式的教堂是一種唯美主義的建築風格,我不以為然,我以為一個個高聳的尖塔就是一種標準,顯示了一種崇高,一種能夠接近天堂,一種居高臨下的標準。
在美國我看到另外一種標準,在城市中心的downtown,人們可以看見一幢幢摩天大樓,它們是用鋼筋水泥和花崗岩塑造成的一種標準,這個標準是以財富資本作為尺度的,在玻璃幕牆的後面,資本和財富的擁有者制定著這一標準。有人說建造摩天大樓是為了節約土地,而在我心中卻不能排除這些高聳入雲的大樓顯示著與天堂溝通的權勢。
天在中國人的語境和思想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詞語,天表示至高無上的權威,天也表示無法回避而又無處不在的神明。天可以解釋所有的苦難和厄運,天可以預示無窮的希望和未來。天令人畏懼,令人崇拜,令人景仰。于是人們懷著這種畏懼、崇拜和景仰,拈香頂禮,讓裊裊升起的煙霧,帶著人間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一股腦地舉霞飛升。
上海政法學院在佘山腳下。佘山高不過幾十米,方圓不過幾百米,然而山頂上居然建成了一座略帶巴羅克和葡萄牙風格的天主教堂,當然有教堂的穹頂,有高大的十字架,有彩色玻璃的花窗,有象征耶穌受難時走過的曲折的痛苦之路。我在上海游學期間,就住在佘山腳下,每日推窗而觀,都可以看見這座教堂聳立在被稱作佘山的山上。在沒有摩天大樓時期的上海,佘山是整個上海離天最近的地方,因此在那里建成的教堂曾經是一種標準,一種與天為鄰的標準。現在的上海大約有數百幢摩天大樓,據說還要建成一幢高達400 米左右號稱“亞洲第一”的大廈,當然這些摩天大樓沒有建在佘山,我無法直觀進行比較孰高孰低,何況早在十幾年前,當我從鄉下返城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以資比較的標準。
沒有了標準,任何的判斷都將失去意義,哪怕做出判斷的人不斷地宣告判斷者手中握有真理。
在人類的歷史上,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創造了彼此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時,也建立起了他們的國家。因此,也就形成了彼此不同的法律和法律體系。早在幾千年以前,當人類只能夠用“巫術”解釋他們無法解釋的自然界秘密的時候,不同地域和民族與文化之間的差距似乎並不顯著。所以,我們有理由說東方與西方法律文化的區別,是人類在自身進化中逐漸產生的區別。包括法律在內的一切文化,都源于其自身發展的規律,不同的法律文化和產生這一法律文化的地理、民族、歷史、宗教乃至習慣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而彼此不同的法律文化的交流與溝通,也只能夠伴隨著地理的認知、民族的融合、宗教的傳播,甚至商業的交往和戰爭的爆發才能夠得以實現。因此,只有在發現和接觸乃至痛苦地踫撞之後,才能判斷出彼此的優劣,並且才能夠主動甚至是被動的作出改變。在沒有外因的條件下,在古代的中國,改變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改變由這種傳統文化派生出來的法律制度,絕無可能。因此,只有當東西之間的文化開始廣泛地接觸之後,並且又經過一番痛苦的比較,才能夠得到判別的標準,從而推動中國自身的法律制度的變革。
在絲綢之路與馬可波羅之後,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實驗科學的西歐,進入了被稱為“地理大發現”的近代史期。航海技術的發展,促進了東西方的交流,並且最終將地球的東西兩半連接起來。
16世紀20年代葡萄牙就開始進駐中國港口,1557年取得了在澳門的貿易許可。中國只是葡萄牙在亞洲的貿易市場之一,圖為日本畫家描繪的當時東方港口的貿易景象,中間端坐著的是明代中國盛行的“交椅”。
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歷史也在這個基礎上悄悄地開始,而且這種交流是在溝通不同的法系之間進行的,人類在其不同地域發展的歷史上,將包括法律文化在內的人類文化分割成帶有強烈地域色彩的各自表達方式,但最終歷史又將這種分割走向整合。當然,我們不能規定進行這種溝通的文化使者們的價值取向,甚至于那些先賢們當初並不具有今人的“當代意識”,但當我們回過頭去細心地審視那段歷史,或者會從中發現其中明顯的必然規律的軌跡。
20 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我與妻子在日本、美國、法國等國家游歷和講學,除了直觀地發現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同時也讓我們了解到法律的差異。于是我們開始注意搜集西方人對中國法律的了解和評價,這似乎讓我們走進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就如同我在年幼的時候站在街上用我那種不諳世事的眼光,努力地打量西方人在中國留下的教堂一樣,我想盡辦法去尋找西方人從他們的角度對我們的觀察和介紹,但是這樣的材料是很難收集到的。首先早期的文獻和美術作品,如今已經成了珍貴的善本,日本人稱之為“珍貴文化財”,借閱十分困難,更何況翻拍或者復制。我們開始在講學之余,流連忘返于各種各樣的公私收藏機構,甚至東京皇宮外面的神田神保町,在這個被稱為“文化街”上,有一家挨一家的書店,甚至還有專門出售中國古籍的山本書店、琳瑯閣、蘭花堂等,其中陳列著很多源于中國的明清古籍,這些“舶來本”的價格令我們感到囊中羞澀。在東京有好幾家專門出售歐洲古籍的書店,用羊皮包裝起來的歐洲古書,帶著一派富貴典雅的風貌,靜靜地陳列在華美的玻璃書櫃中。這些書籍可以隨時翻閱,但不能翻拍和復印,節衣縮食的結果使我們帶回早期用拉丁文著述的關于中國的資料,其中最有價值的是1662 年基歇爾的著作《中國圖說》、在日本橫濱發行的威妥瑪《文件自邇集》以及江戶時期雕版印制的《洗冤集錄》。1994年我應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黃宗智教授的邀請,前往加州大學做訪問學者,並成為黃教授的文獻助手。在美國西海岸洛杉磯有一家私人圖書館,這是一個如同公園一樣的所在,最初建設這家私人圖書館的主人是亨廷頓爵士,為了紀念他的成就,當地人稱之為“亨廷頓圖書館”。在曲徑通幽的園林里,錯落著一些風格迥異的東西方建築,在一幢雅典式的樓房中,我們看到大量珍藏的16 世紀至18 世紀的西方珍貴古籍,其中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關于早期傳教士在中國的發現和他們的通信。同時在我服務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還有一個“羅道夫圖書館”,這是由一位名字叫做羅道夫的美國人贊助建成的,在這個圖書館里我們也發現了一批早期西方人對于中國法律的描述,其中最主要的是發現一批用銅版畫、燈草畫、油畫等藝術方法,描繪的中國古代刑罰的場面。20世紀90 年代後期,我應法國著名漢學家魏丕信教授的邀請,前往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進行為期三年的訪問講學。期間在法國的國家圖書館里意外地發現法文版《中國的刑罰》,這是一部包括22 幅銅版畫在內的,系統地介紹清代乾隆時期中國刑罰的作品,其中不僅包含有笞、杖、徒、流、死的各種刑罰場面,還有官府審判、押解示眾等內容,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止不住心中的激動,就如同“他鄉遇故知”一般,壓抑不住心中的喜悅。在巴黎塞納河邊,有很多小販沿著河堤,擺放各種書攤,那上面陳列著各種語言文字和不同時期的書籍,對于像我們這樣的淘書人而言,真的是闖入錦陣花營,在那里我們搜集到一批歐洲17 世紀至20 世紀生產的銅版畫,這些美術品幾乎耗盡了我們在法國的大半收入,乃至于不得不放棄去阿爾卑斯山滑雪的機會。我的妻子李祝環女士陪同我經歷了這種游學的生涯,並且和我一起去傾囊搜集本書中讀者將會見到的那些珍貴的資料,因此,李祝環女士為本書的另一位作者,這部作品也就成了我們在海外游學的見證和紀念。
16 世紀中期葡萄牙人定居東亞,通過爪哇、滿剌加、澳門等貿易要塞,控制著強大的海上貿易。這些珍貴的文獻和美術作品,記錄了16 世紀以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而且是按照當時西方人的標準進行的描繪,雖然其並不能夠完整並且完全真實地反映出那一時期中國的法律和法律文化,但是重新審視這一段歷史,並且正面的評價和認知,卻仍然是我們今天作為一名中國人的義務和責任。
因此,我們著手寫一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並且將16 世紀以來西方人對中國法律的了解作為這部作品的上卷,最初擬名為《當西方遇到東方》。在下卷中將主要論述在地理大發現之後,直至鴉片戰爭敲開了封建王朝的大門,當時的中國朝野上下是如何看待和了解西方的法律,並且在這種接觸與踫撞之後,中國法律所作出的新的選擇,並擬名為《當東方遇到西方》。後來在朋友的建議下,將此書定名為《接觸與踫撞——16 世紀以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法律也進行了贊揚,他甚至批評西方人對中國的描述和介紹,在他的不朽名著《風俗論》序言一開始就說到︰“西方人所寫的關于幾個世紀以前的東方民族的事情,在我們看來,幾乎全都不像是真的;我們知道,在歷史方面,凡是不像真事的東西,就幾乎總是不真實的。” [2]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應該了解到古老的中國法律,曾經是世界法律發展史上獨具輝煌的一頁,但是當西方法律走向新的文明與變革之時,中國的法律卻停滯不前,並更加趨于固化,從此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間的距離日漸拉開。但是,在中世紀開始至西方的工業革命之前,所謂的西方法律同樣充滿著毫無人性的殘酷的對人的摧殘,而且宗教法庭中的任意性和殘忍,並不亞于當時的東方。就當時的西方宗教法庭而言,因為有人說地球是圓的,而被施以火刑的故事也在警示我們︰對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應當是架構在時間與空間相對平等的歷史境況之下,這樣的比較才可以得出更加客觀的,更有說明力的結論。
清朝末年,曾經在北京居住過較長時間的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Sarach Pike Conger)以她在中國的親身經歷和獨特的觀察,在她給其 兒的信件中曾經這樣寫道︰“每種外國思想都會與不相協調的中國思想相踫撞。當這種踫撞拋起雜音時,人們需要時間和細心的聆听才能捕捉到二者的共鳴……中國屬于她的人民,她的人民必須勵精圖治,站起來保護家園。他們可以風光體面地完成這項任務。天生的優雅加上不懈的努力,他們的這種長處肯定喚醒他們身上沉睡已久的力量。每個國家在自己的土壤內都播下了一粒思想的種子,然後她培育這粒種子,為它澆灌,為它指引生長方向,自始至終小心呵護著它,一旦其他國家踏入她的領土,多此一舉地替她再澆水,在不必要的地方修枝剪葉,然後——如果有果實的話——再把果實攫為己有,她就會反抗斗爭。為什麼不能讓中國自己去種植、培育、澆灌、修剪,然後獲取自己的豐收成果呢?”[3]
1911 年以後,曾經一度輝煌的大清帝國滅亡了,一個新興的中國開始在東方出現,但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所形成的慣性,令這個國家繼續沿著封建傳統的軌跡向前滑行,在沒有了皇帝的國家中,卻出現了幾乎任何人都想當皇帝的局面。但是畢竟歷史不會重演,最終必將是中西之間的法律走向新的交鋒與融合。
……
宣武門是明朝永樂年間建造的,用巨大的石塊和青磚壘成城垣。城垣之上樓分兩層,綠色琉璃瓦蓋頂,金黃色琉璃瓦包邊,一抱多粗的木柱支撐著勾心斗角的大屋頂,斑駁陸離的門窗透著歷史的滄桑。離城樓不遠便是著名的天主教南堂,又叫做“無玷始胎聖母堂”,俗稱宣武大教堂。相傳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獲準在京居住,即以五百金,大概就是五百兩白銀,在宣武門外購地建屋,開始在此傳播宗教。不久利瑪竇又買下附近的“首善書院”,改建成一座天主教堂。“首善書院”原為東林黨人在京的以文會友之地,就是傳說中標榜“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那幫酸秀才們湊在一起侃大山的所在。至萬歷三十八年利瑪竇所建教堂落成。據明代劉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稱︰“堂在宣武門內東城隅,大西洋奉耶穌教者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神宗給廩,賜第此邸。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狹長,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詭異,其國藻也。供耶穌像其上,畫像也,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把渾天儀,右叉指若方論說次,指所說者。須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準,目容有矚,口容有聲,中國畫繪事所不及。所具香燈蓋幃,修潔異狀。右聖母堂,母貌少女,手一兒,耶穌也。衣非縫制,自頂被體,供具如左。” [1]此後清順治七年(1650),皇帝御賜白銀一千萬兩準許傳教士湯若望重新修建該教堂。這是一座20 余米高的巴羅克式的教堂,教堂中設一高大的穹廬圓頂,上設十字架。建成後曾兩度被毀,並于康熙時再度重建,清代初期宣武門的南堂曾經是當時北京城里的最高的建築之一。
我听老輩人說過,想當初洋人蓋這個教堂的時候,國人紛紛反對,皇帝也不許教堂的高度超過當時宣武門的城樓。教堂蓋完之時,還沒有立上十字架,經人測算的結果是宣武門城樓高,一時龍顏大悅,百姓晏然,皆大歡喜。過了不久洋人又在教堂的屋頂悄悄地安了一個十字架,這下子可就超過了宣武門城樓,從此引發國人不滿。更為嚴重的還有人說,自從南堂洋人十字架高過宣武門,洋人就把國人給壓了下去。小時候我對此有些疑惑,但老輩人信誓旦旦地說,中國人自打那時候起就開始走背字,同時還告誡我“這是在論的”,不能有絲毫的疑惑。“在論的”是北京的一句土話,大意是說這是經過上面的人論證過的結論,是權威的、不容置疑的。至于經過了哪些權威的論證,因為不容置疑,所以從來沒有人去追究或者深思過。
然而我還是偷偷地用我的眼楮去觀察去比較。說來也怪,每當我站在宣武門內順城街的街頭自東向西看,結果是宣武門城樓明顯的要比教堂的十字架高;但當我換個位置,自西向東看,結果是教堂的十字架明顯高于宣武門城樓。我對此也曾百思不得其解,似乎中了什麼人的障眼法,看來看去就是斷不出一個究竟。過了不久,街頭一批帶著紅衛兵袖章的人爬到教堂上,將高大的十字架拆了下來,我看見滿街揮舞著紅色的旗幟,我听見無數個市民站在街頭歡呼,從此,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宣武門的城樓不但要高過教堂的穹頂,而且顯得分外的高大和雄偉。後來我響應號召上山下鄉,在無數人的振臂高呼和滿街揮舞的紅旗中,離開了自幼熟悉的北京。在饑餓、勞累與困苦中,我每天必須想到的是如何生存下去,此時無論是宣武門的城樓還是巴洛克式的教堂都被我忘得一干二淨。
20 世紀70 年代我從黃河之濱回到北京,結束了將近十年夢魘般的上山下鄉的生活,開始尋求我人生新的道路。這時的我自認為已經成熟了許多,自認為有了自己判斷的能力,于是我再度去尋訪宣武門,可惜18 世紀的法國掛毯制造商從中華帝國獲得靈感,本圖中描繪了高貴的統治者威嚴地坐在寶座上,萬物都匍匐在他的面前,寶座後面是一只裝飾華麗的大象。
宣武門高大的城樓和那滿目瘡痍的城垣全都不在了。為了修建地鐵工程和“備戰、備荒”的需要,城樓和城垣被一起拆除了,城磚運去修建防空洞了,綠色和金黃色的琉璃瓦也不見了蹤影。然而當初由西方傳教士修建的巴洛克式的教堂還在,光禿禿的穹頂上不見了高大的十字架,顯得不倫不類,像一口巨大的灰黑色的鐵鍋倒扣在上面,迎著太陽,反射出鐵灰色的幽暗的光。我無法比較孰高孰低,因為我失去了可以參照的標準。不見了雄偉的宣武門,不見了高大的十字架,不見了滿街飛舞的紅旗,不見了振臂高呼的人群,然而在內心深處,我卻更加陷入了新的躊躇與迷茫。
我終于明白了為什麼教堂的十字架要蓋得那麼高,明白了象征著封建皇權的城樓要建得那麼高,明白了廟里的浮屠要建得那麼高,明白了清真寺的尖塔要建得那麼高。所有的有資格建造這些的人,都有這樣的話語權,他們要麼是天之子,要麼就是天的使臣,他們可以和上天溝通,唯有他們能夠“與天為鄰”。
從此以後我開始尋找能夠衡量我自己人生的尺度,衡量我周圍所有社會現象的尺度。或者失去了的不會再重新擁有,或者在尋覓中發現新的收獲,我堅信應該有一個標準,一個能讓天下人信服的標準,一個重新塑造我們民族自信的標準。在日本東京郊區的山頂上,一座設計和裝幀分外精巧的廟宇中,懸掛著一口產自中國的古鐘,那上面鑄造著幾行清晰的文字 ︰“以我法為法,法即是法,法外無法。”顯然這是一種標準,與其說是佛學的標準,不如說是世俗社會的標準。我心下竊想,千余年以前,日本國“效仿唐法”時期,不僅以唐代律令為治國之本,還應該引進了源自中國的文化,甚至包括間接取自中國的宗教文化。當然這座日本式的廟宇是建在山上,廟中還有一座密檐式木結構的佛塔,塔頂上鎦金的法器在日光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在法國西南部聖城路德教堂旁邊,我看見沿途描述耶穌受難情景的曲折道路,向山頂上痛苦地延伸,山頂上建有高大的哥特式教堂,一座座用磚塊和石塊築成的尖塔努力地伸向天空,似乎要將這些尖塔化成一個個臂膀去撫摸空中的浮雲。有人說哥特式的教堂是一種唯美主義的建築風格,我不以為然,我以為一個個高聳的尖塔就是一種標準,顯示了一種崇高,一種能夠接近天堂,一種居高臨下的標準。
在美國我看到另外一種標準,在城市中心的downtown,人們可以看見一幢幢摩天大樓,它們是用鋼筋水泥和花崗岩塑造成的一種標準,這個標準是以財富資本作為尺度的,在玻璃幕牆的後面,資本和財富的擁有者制定著這一標準。有人說建造摩天大樓是為了節約土地,而在我心中卻不能排除這些高聳入雲的大樓顯示著與天堂溝通的權勢。
天在中國人的語境和思想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詞語,天表示至高無上的權威,天也表示無法回避而又無處不在的神明。天可以解釋所有的苦難和厄運,天可以預示無窮的希望和未來。天令人畏懼,令人崇拜,令人景仰。于是人們懷著這種畏懼、崇拜和景仰,拈香頂禮,讓裊裊升起的煙霧,帶著人間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一股腦地舉霞飛升。
上海政法學院在佘山腳下。佘山高不過幾十米,方圓不過幾百米,然而山頂上居然建成了一座略帶巴羅克和葡萄牙風格的天主教堂,當然有教堂的穹頂,有高大的十字架,有彩色玻璃的花窗,有象征耶穌受難時走過的曲折的痛苦之路。我在上海游學期間,就住在佘山腳下,每日推窗而觀,都可以看見這座教堂聳立在被稱作佘山的山上。在沒有摩天大樓時期的上海,佘山是整個上海離天最近的地方,因此在那里建成的教堂曾經是一種標準,一種與天為鄰的標準。現在的上海大約有數百幢摩天大樓,據說還要建成一幢高達400 米左右號稱“亞洲第一”的大廈,當然這些摩天大樓沒有建在佘山,我無法直觀進行比較孰高孰低,何況早在十幾年前,當我從鄉下返城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以資比較的標準。
沒有了標準,任何的判斷都將失去意義,哪怕做出判斷的人不斷地宣告判斷者手中握有真理。
在人類的歷史上,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創造了彼此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時,也建立起了他們的國家。因此,也就形成了彼此不同的法律和法律體系。早在幾千年以前,當人類只能夠用“巫術”解釋他們無法解釋的自然界秘密的時候,不同地域和民族與文化之間的差距似乎並不顯著。所以,我們有理由說東方與西方法律文化的區別,是人類在自身進化中逐漸產生的區別。包括法律在內的一切文化,都源于其自身發展的規律,不同的法律文化和產生這一法律文化的地理、民族、歷史、宗教乃至習慣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而彼此不同的法律文化的交流與溝通,也只能夠伴隨著地理的認知、民族的融合、宗教的傳播,甚至商業的交往和戰爭的爆發才能夠得以實現。因此,只有在發現和接觸乃至痛苦地踫撞之後,才能判斷出彼此的優劣,並且才能夠主動甚至是被動的作出改變。在沒有外因的條件下,在古代的中國,改變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改變由這種傳統文化派生出來的法律制度,絕無可能。因此,只有當東西之間的文化開始廣泛地接觸之後,並且又經過一番痛苦的比較,才能夠得到判別的標準,從而推動中國自身的法律制度的變革。
在絲綢之路與馬可波羅之後,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實驗科學的西歐,進入了被稱為“地理大發現”的近代史期。航海技術的發展,促進了東西方的交流,並且最終將地球的東西兩半連接起來。
16世紀20年代葡萄牙就開始進駐中國港口,1557年取得了在澳門的貿易許可。中國只是葡萄牙在亞洲的貿易市場之一,圖為日本畫家描繪的當時東方港口的貿易景象,中間端坐著的是明代中國盛行的“交椅”。
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歷史也在這個基礎上悄悄地開始,而且這種交流是在溝通不同的法系之間進行的,人類在其不同地域發展的歷史上,將包括法律文化在內的人類文化分割成帶有強烈地域色彩的各自表達方式,但最終歷史又將這種分割走向整合。當然,我們不能規定進行這種溝通的文化使者們的價值取向,甚至于那些先賢們當初並不具有今人的“當代意識”,但當我們回過頭去細心地審視那段歷史,或者會從中發現其中明顯的必然規律的軌跡。
20 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我與妻子在日本、美國、法國等國家游歷和講學,除了直觀地發現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同時也讓我們了解到法律的差異。于是我們開始注意搜集西方人對中國法律的了解和評價,這似乎讓我們走進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就如同我在年幼的時候站在街上用我那種不諳世事的眼光,努力地打量西方人在中國留下的教堂一樣,我想盡辦法去尋找西方人從他們的角度對我們的觀察和介紹,但是這樣的材料是很難收集到的。首先早期的文獻和美術作品,如今已經成了珍貴的善本,日本人稱之為“珍貴文化財”,借閱十分困難,更何況翻拍或者復制。我們開始在講學之余,流連忘返于各種各樣的公私收藏機構,甚至東京皇宮外面的神田神保町,在這個被稱為“文化街”上,有一家挨一家的書店,甚至還有專門出售中國古籍的山本書店、琳瑯閣、蘭花堂等,其中陳列著很多源于中國的明清古籍,這些“舶來本”的價格令我們感到囊中羞澀。在東京有好幾家專門出售歐洲古籍的書店,用羊皮包裝起來的歐洲古書,帶著一派富貴典雅的風貌,靜靜地陳列在華美的玻璃書櫃中。這些書籍可以隨時翻閱,但不能翻拍和復印,節衣縮食的結果使我們帶回早期用拉丁文著述的關于中國的資料,其中最有價值的是1662 年基歇爾的著作《中國圖說》、在日本橫濱發行的威妥瑪《文件自邇集》以及江戶時期雕版印制的《洗冤集錄》。1994年我應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黃宗智教授的邀請,前往加州大學做訪問學者,並成為黃教授的文獻助手。在美國西海岸洛杉磯有一家私人圖書館,這是一個如同公園一樣的所在,最初建設這家私人圖書館的主人是亨廷頓爵士,為了紀念他的成就,當地人稱之為“亨廷頓圖書館”。在曲徑通幽的園林里,錯落著一些風格迥異的東西方建築,在一幢雅典式的樓房中,我們看到大量珍藏的16 世紀至18 世紀的西方珍貴古籍,其中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關于早期傳教士在中國的發現和他們的通信。同時在我服務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還有一個“羅道夫圖書館”,這是由一位名字叫做羅道夫的美國人贊助建成的,在這個圖書館里我們也發現了一批早期西方人對于中國法律的描述,其中最主要的是發現一批用銅版畫、燈草畫、油畫等藝術方法,描繪的中國古代刑罰的場面。20世紀90 年代後期,我應法國著名漢學家魏丕信教授的邀請,前往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進行為期三年的訪問講學。期間在法國的國家圖書館里意外地發現法文版《中國的刑罰》,這是一部包括22 幅銅版畫在內的,系統地介紹清代乾隆時期中國刑罰的作品,其中不僅包含有笞、杖、徒、流、死的各種刑罰場面,還有官府審判、押解示眾等內容,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止不住心中的激動,就如同“他鄉遇故知”一般,壓抑不住心中的喜悅。在巴黎塞納河邊,有很多小販沿著河堤,擺放各種書攤,那上面陳列著各種語言文字和不同時期的書籍,對于像我們這樣的淘書人而言,真的是闖入錦陣花營,在那里我們搜集到一批歐洲17 世紀至20 世紀生產的銅版畫,這些美術品幾乎耗盡了我們在法國的大半收入,乃至于不得不放棄去阿爾卑斯山滑雪的機會。我的妻子李祝環女士陪同我經歷了這種游學的生涯,並且和我一起去傾囊搜集本書中讀者將會見到的那些珍貴的資料,因此,李祝環女士為本書的另一位作者,這部作品也就成了我們在海外游學的見證和紀念。
16 世紀中期葡萄牙人定居東亞,通過爪哇、滿剌加、澳門等貿易要塞,控制著強大的海上貿易。這些珍貴的文獻和美術作品,記錄了16 世紀以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而且是按照當時西方人的標準進行的描繪,雖然其並不能夠完整並且完全真實地反映出那一時期中國的法律和法律文化,但是重新審視這一段歷史,並且正面的評價和認知,卻仍然是我們今天作為一名中國人的義務和責任。
因此,我們著手寫一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並且將16 世紀以來西方人對中國法律的了解作為這部作品的上卷,最初擬名為《當西方遇到東方》。在下卷中將主要論述在地理大發現之後,直至鴉片戰爭敲開了封建王朝的大門,當時的中國朝野上下是如何看待和了解西方的法律,並且在這種接觸與踫撞之後,中國法律所作出的新的選擇,並擬名為《當東方遇到西方》。後來在朋友的建議下,將此書定名為《接觸與踫撞——16 世紀以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法律也進行了贊揚,他甚至批評西方人對中國的描述和介紹,在他的不朽名著《風俗論》序言一開始就說到︰“西方人所寫的關于幾個世紀以前的東方民族的事情,在我們看來,幾乎全都不像是真的;我們知道,在歷史方面,凡是不像真事的東西,就幾乎總是不真實的。” [2]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應該了解到古老的中國法律,曾經是世界法律發展史上獨具輝煌的一頁,但是當西方法律走向新的文明與變革之時,中國的法律卻停滯不前,並更加趨于固化,從此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間的距離日漸拉開。但是,在中世紀開始至西方的工業革命之前,所謂的西方法律同樣充滿著毫無人性的殘酷的對人的摧殘,而且宗教法庭中的任意性和殘忍,並不亞于當時的東方。就當時的西方宗教法庭而言,因為有人說地球是圓的,而被施以火刑的故事也在警示我們︰對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應當是架構在時間與空間相對平等的歷史境況之下,這樣的比較才可以得出更加客觀的,更有說明力的結論。
清朝末年,曾經在北京居住過較長時間的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Sarach Pike Conger)以她在中國的親身經歷和獨特的觀察,在她給其 兒的信件中曾經這樣寫道︰“每種外國思想都會與不相協調的中國思想相踫撞。當這種踫撞拋起雜音時,人們需要時間和細心的聆听才能捕捉到二者的共鳴……中國屬于她的人民,她的人民必須勵精圖治,站起來保護家園。他們可以風光體面地完成這項任務。天生的優雅加上不懈的努力,他們的這種長處肯定喚醒他們身上沉睡已久的力量。每個國家在自己的土壤內都播下了一粒思想的種子,然後她培育這粒種子,為它澆灌,為它指引生長方向,自始至終小心呵護著它,一旦其他國家踏入她的領土,多此一舉地替她再澆水,在不必要的地方修枝剪葉,然後——如果有果實的話——再把果實攫為己有,她就會反抗斗爭。為什麼不能讓中國自己去種植、培育、澆灌、修剪,然後獲取自己的豐收成果呢?”[3]
1911 年以後,曾經一度輝煌的大清帝國滅亡了,一個新興的中國開始在東方出現,但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所形成的慣性,令這個國家繼續沿著封建傳統的軌跡向前滑行,在沒有了皇帝的國家中,卻出現了幾乎任何人都想當皇帝的局面。但是畢竟歷史不會重演,最終必將是中西之間的法律走向新的交鋒與融合。
……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