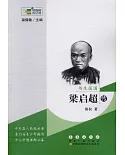黃宗羲是明末清初轉型時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兩部著作對於后世有很大的影響,一部是《明夷待訪錄》,一部是《明儒學案》。他的政治哲學理念,如《原君》所表達的思想,以及他對明儒像陳白沙、王陽明思想的述評,人多能言之。但他的思想的判准,他的心學,所謂「盈天地皆心也」,究竟實義是什麼,歷來學者並沒有作過系統的考察,觀念上是十分模糊的。我提議用一種例溯的方法,把握到他的思想的定位,然后對他的《明儒學案》有一深入的省察,以確定他在思想史上的貢獻與地位。
我治宋明儒學,受牟宗三先生的影響最深。他的三大卷的《心體與性體》,把這一門學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他義理精熟,解析入微,才可以把許多不容易講清楚的概念,賦以確定的內容。而絕非憑一時的感興,拆之於聯想,大發議論,這樣的毛病雖熊十力先生也不能免。他的造詣尤非那些只能在外部盤旋,作一些枝節的考據的人所能望其項背。讀者看完我這部書,就會知道我對他的說法所取特多,是有一定理由的。
目錄
緒言
第一章 黃宗羲對於蕺山思想的繼承
第二章 黃宗羲對於陽明思想的簡擇
第三章 黃宗羲對於朱子思想的批評
第四章 黃宗羲心學的定位
第五章 黃宗羲《明儒學案》義理的解析
第六章 黃宗羲在思想史上的貢獻與地位
附錄
論黃宗羲對於孟子的理解
論王陽明的最后定見
黃宗羲晚節不保?——「黃宗羲討論會」之后的省思
第一章 黃宗羲對於蕺山思想的繼承
第二章 黃宗羲對於陽明思想的簡擇
第三章 黃宗羲對於朱子思想的批評
第四章 黃宗羲心學的定位
第五章 黃宗羲《明儒學案》義理的解析
第六章 黃宗羲在思想史上的貢獻與地位
附錄
論黃宗羲對於孟子的理解
論王陽明的最后定見
黃宗羲晚節不保?——「黃宗羲討論會」之后的省思
序
我的《黃宗羲心學的定位》一書出版轉眼不覺已二十年。我的基本思路並沒有變,但概念表達要更精准,就必須作出必要的調整。梨洲思想無疑是心學的一支,梁任公說他是「王學的修正者」,庶幾得之。我的書已提出充分的論據說明,梨洲一生忠於乃師蕺山的誠意慎獨教;他的思想雖缺乏原創性,但還能持宋明儒學的睿識。故我把他當作此一思緒的殿軍。清儒如顏元、戴震已完全喪失了宋明儒學對於「天道性命相感通」與超越天道的體證與向往,以致造成了「典范轉移」的變化。
由這樣的視域着眼,朱子的理學與陽明的心學都毫無疑問是聖學的分支。相對於朱子理氣二元不離不雜的思想,陽明的思想明顯地展示了一種強烈的「內在一元的傾向」,主張超越的「理」具現在內在的「氣」之中。我一貫堅持無論陽明、蕺山、梨洲都維持了對於超越天道的向往,故此把他們的思想說成「內在一元論」,是不免誤導的。此一詞嚴格說來,只能用於王廷相、顏習齋、戴東原,當然也可以用於梨洲同門陳確的思想。從梨州與陳確二人的書信往來相互辯難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乾初已否定了超越天道的層面,而提出一種「內在一元」的論旨。我現在明白區分開「內在一元的傾向」與「內在一元論思想」的不同涵義,這樣應該可以避免以前因用詞不夠精准所引起的不必要的誤解。
二十年來,對於宋明儒學的研究,無論在資料或論述方面,都已有了長足的進步。舉例說,由沈善洪、吳光主編的《黃宗羲全集》十二冊,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1985年出第一冊,到1994年出齊;由吳光等編校的《王陽明全集》二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2年出版;由戴璉璋、吳光主編的《劉宗周全集》五冊,由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於1996年在台北出版。這些年來研討會的舉行、論文集與專著的出版,成果豐碩,此處不贅。
重點著作除了增補必要的資訊之外,在內容方面並不需要作重大的修改。但由於受到學者討論的刺激,我又寫了幾篇有相當分量的論文。現在趁着我的書出簡體字本的機會,挑選了兩篇文章列在附錄之內,一為《論黃宗羲對於孟子的理解》,二為《論王陽明的最后定見》,並略加解釋如下。
梨洲自述為何作《孟子師說》一書時曾經指出,蕺山對於《大學》、《中庸》、《論語》都有著述,獨《孟子》無成書,所以竊取其意,成書七卷,以補未備。但無論如何,這是梨洲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他如何通過《劉子遺書》吸收了其睿識,經過消化之后成為他自己的思想。香港學者鄧立光認為,梨洲晚年因受到乾初思想的影響而有所改變,並以梨洲此書成段抄襲乾初《性解》一文不加聲明,有剽竊之嫌。我駁斥了這樣的觀點。因梨洲希望闡明的是師說,那個時代學者沒有出版研究的壓力,根本缺乏「抄襲」的動機。而我認定梨洲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乾初這段話雖合乎師說,但他所得於蕺山者在梨洲看來不過十之二三,故隱其名,免得給人留下一個好像乾初深入蕺山思想的印象。就內容而言,梨洲沿襲蕺山所作的《孟子》解,明顯有內在一元的傾向,雖校正了朱子以二元思想釋《孟子》之非,也未必就合乎《孟子》的原義,所以才會受到牟宗三先生的斥責。
而梨洲對陽明、龍溪雖然有較乃師更為同情的理解,但仍篤信蕺山以陽明為因病立方、權實互用的說法,以至產生了一些一直未為人充分注意到的詭異現象,所謂陽明「學三變,教亦三變」的說法早已為人耳熟能詳。錢德洪《刻文錄敘說》所謂「教亦三變」的三個階段是:「知行合一」、「靜坐」與「致良知」。這應該是最有權威性的說法。令我感到驚奇的是,《明儒學案》行世二百多年來,竟然讓我這樣一個不擅長考據的人在無意中發現,梨洲對於這一說法作了十分微妙的改易。梨洲謂陽明學成之后又有三變,這三個階段是:「默坐澄心」、「致良知」,最后乃是「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致良知」由第三階段變成了第二階段,最后一個階段無關教法。有關陽明最高境界體證描繪的文字系取自龍溪的《滁陽會語》。然龍溪講述陽明悟后的變化,並未划分階段,故「學成之后三變」證實無疑是梨洲自創的說法。我進一步探究,為何梨洲要作出這樣的改易呢?我的推測是,梨洲把「致良知」往前推一個階段,這樣可以騰出位置來把蕺山的誠意慎獨教代替陽明的空靈境界的體證當作「終教」來安排。但我認為這是一種曲解。陽明的「致良知」就是他的「終教」。他既明說「四句」教徹上徹下,那就是他最后的見解。龍溪倡「四無」教雖非無據,但的確有所盪越,而蕺山「歸顯於密」顯然是另一條不同的線索。但由此可以證明梨洲的確忠於蕺山的思想,不能像牟宗三先生那樣割裂蕺山與梨洲。許多糾結實來自蕺山,包括「盈天地問一氣也」那種內在一元的傾向。牟先生固未否認蕺山思想有些地方並不明徹,卻給予了同情的了解。故我不贊同他過分貶斥梨洲為氣化論者的說法,客觀掌握的證據可以顯示,梨洲思想畢竟不同於內在一元論,這由他與乾初的辯難就可以看得出來。梨洲認同蕺山「氣質之性」外無「義理之性」的論旨,但反對乾初將之滑轉成為「天理正從人欲中見」的說法,而批評乾初「所見為天理者,想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正因為梨洲還能堅持「天理」、「人欲」的分別,故我以之為宋明儒學之殿軍,應該是言之有據的說法。就主觀的願望言,雖然梨洲亟望蕺山之教昌明於天下,但事與願違,他開創的思想實際指向閻若璩的考證,顏、李的實用主義,東原的達情遂欲,在清初造成了「典范轉移」,故我才斷定他是一悲劇性的人物。
當然梨洲生命的悲劇也展示在他不得不接受明代覆亡的事實,他自己終其生拒絕事清,但容許弟子萬斯同以布衣身份參修《明史》,兒子百家也有分參與。最令人驚詫的是,近年竟然發現他為孫兒黃蜀應考加以關說的信函,還稱當時的統治者(康熙)為「聖王」,這不免如白璧之玷。但有人攻擊梨洲「晚節不保」,我覺得這樣的批評不免過分了,曾寫一短文予以回應,即《黃宗羲晚節不保?——黃宗羲討論會之后的省思》,作為附錄之三收入本書新版之內。
由原著以及新加的三篇附錄大體可以看出我對梨洲思想通盤的了解。此書出簡體字本,由吳光教授作序,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黃進興教授幫助取得原出版者台北允晨文化公司無償授權,都是我所衷心感謝的。
在本書即將在大陸出新版之際,正逢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與余姚市人民政府再次合作在余姚舉辦「黃宗羲民本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將會討論黃宗羲「民本」思想的性質問題,並邀請本人作為特邀代表出席會議。因此,我想再補充說幾句話:梨洲當鼎革之世,著《明夷待訪錄·原君篇》這樣的大文章,痛批私天下的禍害。梁啟超在清末把《明夷待訪錄》當作宣傳品支持改革,在本土找資源,說《明夷待訪錄》是幼稚的民主。其實《明夷待訪錄》的理論基礎與《民約論》截然有異。《民約論》基於權利的考慮,正是梨洲否定的東西。梨洲是要回返古代聖王之治。啟蒙理性霸權在后現代受到嚴厲批評,現代西方見利忘義、政商勾結,罔顧細民死活,造成貧富懸殊,正是《明夷待訪錄》批評的對象。但梁啟超因歷史的誤會借此書吹響了改革的號角,讓傳統突破「民本」的規模,走向民主、自由、開放的大道,還是可以大書特書的一件事情。
劉述先
2005年8月18日識於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由這樣的視域着眼,朱子的理學與陽明的心學都毫無疑問是聖學的分支。相對於朱子理氣二元不離不雜的思想,陽明的思想明顯地展示了一種強烈的「內在一元的傾向」,主張超越的「理」具現在內在的「氣」之中。我一貫堅持無論陽明、蕺山、梨洲都維持了對於超越天道的向往,故此把他們的思想說成「內在一元論」,是不免誤導的。此一詞嚴格說來,只能用於王廷相、顏習齋、戴東原,當然也可以用於梨洲同門陳確的思想。從梨州與陳確二人的書信往來相互辯難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乾初已否定了超越天道的層面,而提出一種「內在一元」的論旨。我現在明白區分開「內在一元的傾向」與「內在一元論思想」的不同涵義,這樣應該可以避免以前因用詞不夠精准所引起的不必要的誤解。
二十年來,對於宋明儒學的研究,無論在資料或論述方面,都已有了長足的進步。舉例說,由沈善洪、吳光主編的《黃宗羲全集》十二冊,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1985年出第一冊,到1994年出齊;由吳光等編校的《王陽明全集》二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2年出版;由戴璉璋、吳光主編的《劉宗周全集》五冊,由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於1996年在台北出版。這些年來研討會的舉行、論文集與專著的出版,成果豐碩,此處不贅。
重點著作除了增補必要的資訊之外,在內容方面並不需要作重大的修改。但由於受到學者討論的刺激,我又寫了幾篇有相當分量的論文。現在趁着我的書出簡體字本的機會,挑選了兩篇文章列在附錄之內,一為《論黃宗羲對於孟子的理解》,二為《論王陽明的最后定見》,並略加解釋如下。
梨洲自述為何作《孟子師說》一書時曾經指出,蕺山對於《大學》、《中庸》、《論語》都有著述,獨《孟子》無成書,所以竊取其意,成書七卷,以補未備。但無論如何,這是梨洲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他如何通過《劉子遺書》吸收了其睿識,經過消化之后成為他自己的思想。香港學者鄧立光認為,梨洲晚年因受到乾初思想的影響而有所改變,並以梨洲此書成段抄襲乾初《性解》一文不加聲明,有剽竊之嫌。我駁斥了這樣的觀點。因梨洲希望闡明的是師說,那個時代學者沒有出版研究的壓力,根本缺乏「抄襲」的動機。而我認定梨洲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乾初這段話雖合乎師說,但他所得於蕺山者在梨洲看來不過十之二三,故隱其名,免得給人留下一個好像乾初深入蕺山思想的印象。就內容而言,梨洲沿襲蕺山所作的《孟子》解,明顯有內在一元的傾向,雖校正了朱子以二元思想釋《孟子》之非,也未必就合乎《孟子》的原義,所以才會受到牟宗三先生的斥責。
而梨洲對陽明、龍溪雖然有較乃師更為同情的理解,但仍篤信蕺山以陽明為因病立方、權實互用的說法,以至產生了一些一直未為人充分注意到的詭異現象,所謂陽明「學三變,教亦三變」的說法早已為人耳熟能詳。錢德洪《刻文錄敘說》所謂「教亦三變」的三個階段是:「知行合一」、「靜坐」與「致良知」。這應該是最有權威性的說法。令我感到驚奇的是,《明儒學案》行世二百多年來,竟然讓我這樣一個不擅長考據的人在無意中發現,梨洲對於這一說法作了十分微妙的改易。梨洲謂陽明學成之后又有三變,這三個階段是:「默坐澄心」、「致良知」,最后乃是「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致良知」由第三階段變成了第二階段,最后一個階段無關教法。有關陽明最高境界體證描繪的文字系取自龍溪的《滁陽會語》。然龍溪講述陽明悟后的變化,並未划分階段,故「學成之后三變」證實無疑是梨洲自創的說法。我進一步探究,為何梨洲要作出這樣的改易呢?我的推測是,梨洲把「致良知」往前推一個階段,這樣可以騰出位置來把蕺山的誠意慎獨教代替陽明的空靈境界的體證當作「終教」來安排。但我認為這是一種曲解。陽明的「致良知」就是他的「終教」。他既明說「四句」教徹上徹下,那就是他最后的見解。龍溪倡「四無」教雖非無據,但的確有所盪越,而蕺山「歸顯於密」顯然是另一條不同的線索。但由此可以證明梨洲的確忠於蕺山的思想,不能像牟宗三先生那樣割裂蕺山與梨洲。許多糾結實來自蕺山,包括「盈天地問一氣也」那種內在一元的傾向。牟先生固未否認蕺山思想有些地方並不明徹,卻給予了同情的了解。故我不贊同他過分貶斥梨洲為氣化論者的說法,客觀掌握的證據可以顯示,梨洲思想畢竟不同於內在一元論,這由他與乾初的辯難就可以看得出來。梨洲認同蕺山「氣質之性」外無「義理之性」的論旨,但反對乾初將之滑轉成為「天理正從人欲中見」的說法,而批評乾初「所見為天理者,想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正因為梨洲還能堅持「天理」、「人欲」的分別,故我以之為宋明儒學之殿軍,應該是言之有據的說法。就主觀的願望言,雖然梨洲亟望蕺山之教昌明於天下,但事與願違,他開創的思想實際指向閻若璩的考證,顏、李的實用主義,東原的達情遂欲,在清初造成了「典范轉移」,故我才斷定他是一悲劇性的人物。
當然梨洲生命的悲劇也展示在他不得不接受明代覆亡的事實,他自己終其生拒絕事清,但容許弟子萬斯同以布衣身份參修《明史》,兒子百家也有分參與。最令人驚詫的是,近年竟然發現他為孫兒黃蜀應考加以關說的信函,還稱當時的統治者(康熙)為「聖王」,這不免如白璧之玷。但有人攻擊梨洲「晚節不保」,我覺得這樣的批評不免過分了,曾寫一短文予以回應,即《黃宗羲晚節不保?——黃宗羲討論會之后的省思》,作為附錄之三收入本書新版之內。
由原著以及新加的三篇附錄大體可以看出我對梨洲思想通盤的了解。此書出簡體字本,由吳光教授作序,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黃進興教授幫助取得原出版者台北允晨文化公司無償授權,都是我所衷心感謝的。
在本書即將在大陸出新版之際,正逢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與余姚市人民政府再次合作在余姚舉辦「黃宗羲民本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將會討論黃宗羲「民本」思想的性質問題,並邀請本人作為特邀代表出席會議。因此,我想再補充說幾句話:梨洲當鼎革之世,著《明夷待訪錄·原君篇》這樣的大文章,痛批私天下的禍害。梁啟超在清末把《明夷待訪錄》當作宣傳品支持改革,在本土找資源,說《明夷待訪錄》是幼稚的民主。其實《明夷待訪錄》的理論基礎與《民約論》截然有異。《民約論》基於權利的考慮,正是梨洲否定的東西。梨洲是要回返古代聖王之治。啟蒙理性霸權在后現代受到嚴厲批評,現代西方見利忘義、政商勾結,罔顧細民死活,造成貧富懸殊,正是《明夷待訪錄》批評的對象。但梁啟超因歷史的誤會借此書吹響了改革的號角,讓傳統突破「民本」的規模,走向民主、自由、開放的大道,還是可以大書特書的一件事情。
劉述先
2005年8月18日識於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