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在一定意義上,是不可譯的。一首好詩是種種精神和物質的景況和遭遇深切合作的結果。產生一首好詩的條件不僅是外物所給的題材與機緣,內心所起的感應和努力。山風與海濤,夜氣與晨光,星座與讀物,良友的低談,路人的咳笑,以及一切至大與至微的動靜和聲息,無不冥冥中啟發那凝神握管的詩人的沉思,指引和催促他的情緒和意境開到那美滿圓融的微妙的剎那;在那里詩像一滴凝重、晶瑩、金色的蜜從筆端墜下來;在那里飛躍的詩思要求不朽的形體而俯就重濁的文字,重濁的文字受了心靈的點化而升向飛躍的詩思,在那不可避免的驟然接觸處,迸出了燦爛的火花和鏗鏘的金聲!所以即最大的詩人也不能成功兩首相同的傑作。
這集子所收的,只是一個愛讀詩者的習作,夠不上稱文藝品,距離兩位英法詩人的奇跡自然更遠了。假如譯者敢有絲毫的自信和辯解,那就是這里面的詩差不多沒有一首不是他反復吟詠,百讀不厭的每位大詩人的登峰造極之作,就是說,他自己深信能夠體會個中奧義,領略個中韻味的。這些大詩人的代表作自然不止此數,譯者愛讀的詩和詩人也不限於這些;這不過是覺得比較可譯或偶然興到試譯的罷了。
至於譯筆,大體以直譯為主。除了少數的例外,不獨一行一行地譯,並且一字一字地譯,最近譯的有時連節奏和用韻也極力摹仿原作——大抵越近依傍原作也越甚。這譯法也許大笨拙了。但是譯者有一種暗昧的信仰,其實可以說迷信:以為原作的字句和次序,就是說,經過大詩人選定的字句和次序是至善至美的。如果譯者能夠找到適當對照的字眼和成語,除了少數文法上地道的構造,幾乎可以原封不動地移植過來。譯者用西文譯中詩是這樣,用中文譯西詩也是這樣。有時覺得反而比較能夠傳達原作的氣韻。不過,譯者得在這里復說一遍:因為限於文字的基本差別和譯者個人的表現力,吃力不討好和不得不越軌或易轍的亦不少。
-

己亥:余世存讀龔自珍
$355 -

小泉八雲精怪故事集
$35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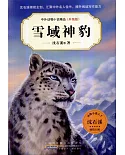
中外動物小說精品(升級版):雪域神豹
$115 -

樂死人的文學史(魏晉篇)
$198 -

這樣寫出好故事:描寫與背景
$19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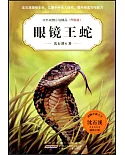
中外動物小說精品(升級版):眼鏡王蛇
$1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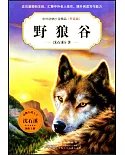
中外動物小說精品(升級版):野狼谷
$115 -

宋文學史(圖文版)
$15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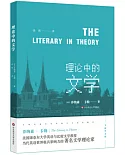
理論中的文學
$251 -

中國文學史(圖文版)
$208 -

剪刀與女房東
$251 -

小說的方法
$180 -

從美感兩重性到情本體--李澤厚美學文錄
$412 -

詩的時光書:當你老了
$219 -

漢文學史小講
$616 -

舞蹈與舞者
$219 -

中外動物小說精品(升級版):66號警犬
$1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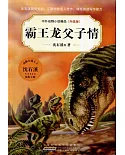
霸王龍父子情
$115 -

文學思想研究與文學語言觀透視
$298 -

文學批評的應許與期許
$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