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聽了准會一怔。我這一輩子還沒活完(也不知道我還剩多大一截兒!),哪兒又冒出個兩輩子來?是不是瞎起哄,要麼就是人還沒活到八十六,就糊塗啦?
您別急,我的好讀者。雖說我記性興許差啦,常丟三落四,轉身就忘,所以常站在屋子里抓瞎轉磨;可謝天謝地,我一點兒也還不糊塗。不信,我吃着飯您硬把碗搶走,我准不答應;走道兒要是碰個坑兒崗兒的,我准老遠就躲開;要是跟我話里有話,我還准聽得出來。要是有架機器能考驗人還清不清醒,我准及格,興許還來個滿分兒。您說,要是沒這麼點兒本事,我還能活到今天嗎?那麼哪兒來的這兩輩子呢?
您聽我說。倒退二十九個年頭兒——您就甭算啦,反正就是到咽氣的那會兒,我也忘不了的一九六六年。我連日子也沒忘:八月二十三日的晚上。那時候北京城(大概全中國吧)可大渾地暗啦!太陽沒影兒啦,世界變成了冰窖兒啦。平常老實人忽然也齜起牙來——因為要是不,別人就朝你齜。滿市街搶着大刀,甩着屎棒。向來最惜命的我,最后也頂不住啦。我把偷偷攢下的一瓶安眠藥全從嗓子眼兒倒下去。得!那麼一來,我就沒氣兒啦,隨你們折騰我那屍首去吧,反正只要我還有口氣兒,就不能讓戴紅箍兒的這麼隨便兒折騰下去。
-

人間告白
$260 -

塵世的夢浮橋
$348 -

若無盔甲,怎護軟肋:做一個智慧通透的女子
$239 -

我從來不感到孤獨
$251 -

植物大戰僵屍2.武器秘密之你問我答科學漫畫:安全與避險卷
$146 -

在時光里流浪
$27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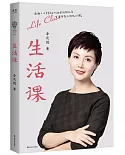
生活課
$208 -

每個生命都要結伴而行(全新修訂版)
$251 -

嚮往的生活
$208 -

矮大緊指北.1:文青手冊
$270 -

腳客
$208 -

蔡瀾說書法:靜下心來寫寫字
$312 -

人是天地間多彩的雲
$355 -

科學全知道(套裝共24冊)
$1,56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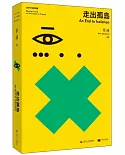
單讀(24):走出孤島
$271 -

廬隱散文集
$124 -

畢淑敏的心靈課(畢淑敏“心靈四書”系列)
$188 -

山居七年
$303 -

我們總是孤獨成長
$235 -

蔡瀾說好物:我喜歡的是欣賞
$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