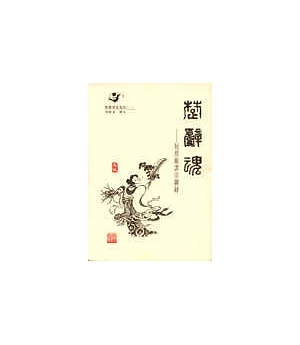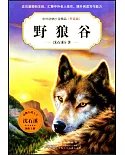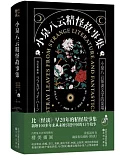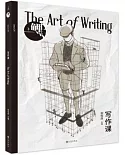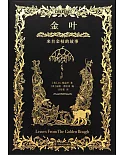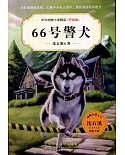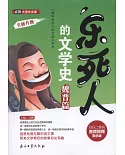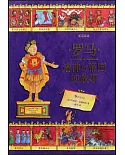內容簡介
《楚辭源流選集》盡管只是一部作品選,但這「選
」的本身就是一門不可造次的大學問。本書的編輯宗旨主要立足於通俗,以一般的楚辭愛好者為主要讀者對象,提供一種閱讀欣賞、貪圖騷體文學面目的廣西,故用橫排簡體,本書所收作品的分類問題突出的是「騷體詩」與騷體賦「的分野。本書的注釋,基本是在多種版本相比較的基礎上來選用前人成果的,對於未有定論的探索性一家之言均未采用。楚辭的「源」與「流」問題,關乎本書的出版價值與編輯思想。
目錄
前言
總序
東方荷馬 百代文宗
屈原辭全譯
屈原辭句注
屈原辭圖錄
從屈原到阿赫瑪托娃
離騷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游
卜居
漁父
招魂
大招
屈原之死與他的悲劇人格
屈原的「海灣型情感」與「水仙情結」
總序
東方荷馬 百代文宗
屈原辭全譯
屈原辭句注
屈原辭圖錄
從屈原到阿赫瑪托娃
離騷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游
卜居
漁父
招魂
大招
屈原之死與他的悲劇人格
屈原的「海灣型情感」與「水仙情結」
序
楚辭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獨步肇開的歷史地位,而且在世界文苑中也堪稱獨秀群芳的一枝奇葩。李澤厚先生就講過:在中國二千多年的文學史上,至今也許只有《紅樓夢》可與之比美;金開誠先生則認為屈原的辭作「作為 『風』
『騷,傳統的兩大典范之一,確曾衣被百世,啟益后人」。「屈原是世界上最早對超現實想象進行了自覺運用的文化創作者。」而梁啟超先生則認為:在世界文學史上的韻文中,除了但丁的《神曲》外,恐怕還沒有能與之相比的。在古今楚辭文論中,古代的學者大多認為,
自屈宋以降,后世辭賦皆祖屈原;近現代學者大多認為,楚辭一直影響了中國文學二千多年,這已是古今不爭之論。為樹木者其枝葉愈繁,其根柢必愈厚重;為江河者,其流脈愈長,其源頭必愈深廣。文學作品尤其如此,凡影響愈大者,地位愈崇者,非植根於深厚的歷史文化之土壤中,則無以一峰突起而百代不衰。楚辭就是深深植根於楚文化和先秦文化母壤中,才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范本。它的影響作用自漢以降遠遠超過了《詩經》。
《騷》雖繼《詩》而起,但楚辭絕非是《詩經》的簡單衍變,《詩經》與楚辭當稱是中國文學園地中的一對姊妹花。從總體上看,楚辭是三代以降的先秦文化首先是楚文化母體培育出來的嬰兒。對於楚辭影響最大的是先秦楚地的民歌、祭詞;再次是《詩經》;再次是先秦諸子的文章,尤以老子、庄子為首屈;再次是《戰國策》、《國語》中的行人說辭。而有關的神話傳說和寓言、史料等,則為楚辭提供了創想的天地和創作材料。
楚地的民歌、巫祭歌詞是楚辭最直接的母壤。楚辭之所以具有不可復制性,就像是后人們只能用克拉拉大理石來仿造古希臘的藝術品,而不可能再造出那個時代的青銅雕像一樣,就因為它所使用的楚詞、楚語、楚調,具有不可復制性,所以后人大多只能借用其形式,描摹其形態,甚至可得其神韻之一、二,但永遠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楚辭。不過,楚辭絕不僅僅是楚文化的產兒,否則便無以如此地流被深廣。因而,不能把楚辭看成是地域文化作品。它確實吸收了代表北方文化特征的《詩經》與先秦諸子政論、歷史文學等多種文學體式中的許多養分。《詩經》中的許多詩已明顯的帶有后來楚辭所運用的語言、句式特色。在風、雅、頌中都有對四言的打破,甚至對五、七言的成功運用。也有了對於「小」的突破,許多篇什都相當有規模。還有賦、比、興手法的嫻熟運用,這些對於楚辭的形成都有其借鑒觀照作用。先秦諸子中,老子、庄子的作品更可以看出許多楚辭的先聲。且這二位都與楚國有着不可分割的淵源,史料明確地稱老子為楚人,庄子籍貫雖為宋國蒙人,但也有稱其為楚人的說法,其足跡大抵於楚居多。尤其是其汪洋恣肆的文風與想像力和寓言式的表述手段對楚辭有極大的影響。在《左傳》中會找到許多類似楚辭的短詩。至於《國語》、《戰國策》中一些賦、比、興手法的運用與行人說辭,也對楚辭與漢賦有着深遠的影響。后世選家們便有把二者中的一些篇目直接歸類到「騷」中去的。劉師培先生曾講道:「詩賦之學,亦出入行人之官。」「欲考詩賦之流別者,盍溯源於縱橫家哉。」而章炳麟先生則講道:《戰國策》「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為紛葩;期於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 「策」與「賦」之別,唯「有韻,無韻雲爾」。《國策》、《國語》中大多為說者行人之辭,駢辭儷句、渲染述賦通篇皆是。還有關於人類遠古及三代以降的傳說、史料、神話,中原文化與荊楚、吳越等南方區域文化的交流、整合等都為楚辭的產生提供了必然條件。這是從總體而言,先秦文化中的不同成分都在不同的側面為楚辭的形成提供着不同的底蘊。而楚辭的不同類型作品又分別吸收着不同的養料。
屈辭中的作品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天問》、 「二招」、{橘頌}大體上師祖《詩經》與古四言韻文;《九歌》基本上是楚調巫祭之歌,大體上直接發韌於楚地的各類民歌,並受先秦祭頌之作的影響;《卜居》、《漁父》皆為小賦,大體受了先秦諸子中「問對」類文章的影響;其余諸篇大多為不歌之詩,基本上源自於古之詩與歌,並吸收了古之謠諺、韻文、小賦的養料i宋玉的作品則師承屈辭。向「文人詩」的方向跨進了一大步。但在楚辭中,尤其是屈原的作品,對於先秦諸文化樣式中優秀成分的兼收並蓄,絕不是模仿或承襲,而是一種在前人和同時代、同區域文化基礎上的一種以超現實的想像力所進行的全新創造,這正是楚辭的藝術魅力與生命力之所在。你只能說在先秦各種文學體式中找到它的底蘊,你卻很難說它像哪一種。可是,在屈原以后的作品中,你不僅到處可以看到屈辭中的語言、詞匯、文體、手法的痕跡,甚至可以直接在屈原作品中找到它們的師祖篇目及形式。所以,到了魏晉以后,仍有「一世之士,皆祖屈原」之說。 諸如:《天問》篇在后世形成了一種「天問體」詩賦;《遠游》篇在后世形成了一種「游仙體」詩賦; 《橘頌》篇在后世形成了詠物抒情類的詩賦;「二湘」、《山鬼》在后世則影響到許多言情懷人詩賦;《國殤》、「二招」則影響到后世的廟堂文學、祭悼、戰爭類詩賦和誄文、墓志銘的風格;《哀郢》、《抽思》實為后世去國懷鄉作品之鼻祖;《涉江》、《湘夫人》、《悲回風》則「皆開后世詩文寫景法門,先秦絕無僅有」 (錢鍾書語);《離騷》與《九章》中的一些篇目則開了后世之自傳體詩作與哀怨自傷文學作品的先河; 《卜居》、 《漁父》與《招魂》流變為后世之賦文。而屈原與宋玉作品中的艾怨自傷成分,則作為一種傳統直接影響、流變為漢及以后的騷體詩賦,尤其是對漢代的影響更為直接和深刻。
楚辭對后世文學在方方面面的影響,尤其是對古詩深遠的革命式之影響,古今楚辭學者們多已盡論。不僅在五、七言詩方面肇開先河,而且在藝術手法上對古典文學具有廣泛深刻的影響。我們不能不承認,楚辭自漢以降,漸趨式微,但楚辭的直接流脈,至今仍清晰可見,概言之,大體有二:其一,直接衍變為各類騷體詩;其二,直接化生為騷體賦。尤以騷體詩流延最為綿長,入兩漢、越魏晉、跨唐宋、逾明清而至近現代。二者與楚辭形成了明顯的騷體文學體系主干。楚辭之所以后世漸為不顯者,概因文學品種、門類、數量與日倍增,楚辭流脈作品皆散於其中。歷代選家至多把騷體作品列為一類而已。宋朱熹輯有《楚辭后語》50余首,實集后世騷體文學之作不及滄海一栗;而宋人晁補之先此所輯《續楚辭》、《變離騷》兩集156篇作品,版本早巳失傳於世,不得復見。明清的紹騷作品集不少,但成規模的,只有清代廖元度先生的《楚風補》。雖此,仍足以說明一直到有宋,楚辭流脈仍舊綿延不息。直到元、明、清乃至現當代,治楚辭者之眾遠愈此前,而擬作直到明清亦從不曾有絕。
楚辭從一誕生開始,就是一種「文人文學」,並不擁有大眾讀者,但凡經典文化不得以實用之斗筲而一概量之。而后世之仿作,雖續貂者居多,然無之亦無可窺全豹,故亦不可作蛇足觀而棄之。無其流而不見江河之壯美,棄其源而江河無以流;無枝葉而不成其林木,無根本而枝葉無所依。故此,作者對歷年披閱典籍之所得資料進行編譯整理,輯而為《楚辭源流選集》五卷:其一,屈原作品輯為《楚辭魂》為全書之核心,故列於首;其二, 由屈宋而上溯相關詩文輯為《楚辭源》,試尋楚辭與騷體詩賦之淵源;其三, 自漢以降之歷代騷體詩輯為《楚辭流》;其四, 自漢以降騷體賦輯為《楚辭余》,兩卷所輯皆為楚辭之衍變與流脈,而分稱「流」、「余」乃為別詩、賦;其五,古今歷代名家學者的楚辭文論詩贊輯為《楚辭論》, 以加深對楚辭源流的理性認知。全書共收入作品2000余篇,並配有近500幅珍貴的圖片。盡管所輯也仍不過是騷體文學、楚辭文論中的九牛一毛,盡管在所選篇目、分類編次上都會存在諸多不足與舛謬,但該書的出版,相信自有其價值, 當會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與楚辭學的發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003年是屈原逝世二千二百八十年,也是他榮獲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殊榮六十周年的紀念年份。此書的出版也當是對紀念我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一份芹獻。
《騷》雖繼《詩》而起,但楚辭絕非是《詩經》的簡單衍變,《詩經》與楚辭當稱是中國文學園地中的一對姊妹花。從總體上看,楚辭是三代以降的先秦文化首先是楚文化母體培育出來的嬰兒。對於楚辭影響最大的是先秦楚地的民歌、祭詞;再次是《詩經》;再次是先秦諸子的文章,尤以老子、庄子為首屈;再次是《戰國策》、《國語》中的行人說辭。而有關的神話傳說和寓言、史料等,則為楚辭提供了創想的天地和創作材料。
楚地的民歌、巫祭歌詞是楚辭最直接的母壤。楚辭之所以具有不可復制性,就像是后人們只能用克拉拉大理石來仿造古希臘的藝術品,而不可能再造出那個時代的青銅雕像一樣,就因為它所使用的楚詞、楚語、楚調,具有不可復制性,所以后人大多只能借用其形式,描摹其形態,甚至可得其神韻之一、二,但永遠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楚辭。不過,楚辭絕不僅僅是楚文化的產兒,否則便無以如此地流被深廣。因而,不能把楚辭看成是地域文化作品。它確實吸收了代表北方文化特征的《詩經》與先秦諸子政論、歷史文學等多種文學體式中的許多養分。《詩經》中的許多詩已明顯的帶有后來楚辭所運用的語言、句式特色。在風、雅、頌中都有對四言的打破,甚至對五、七言的成功運用。也有了對於「小」的突破,許多篇什都相當有規模。還有賦、比、興手法的嫻熟運用,這些對於楚辭的形成都有其借鑒觀照作用。先秦諸子中,老子、庄子的作品更可以看出許多楚辭的先聲。且這二位都與楚國有着不可分割的淵源,史料明確地稱老子為楚人,庄子籍貫雖為宋國蒙人,但也有稱其為楚人的說法,其足跡大抵於楚居多。尤其是其汪洋恣肆的文風與想像力和寓言式的表述手段對楚辭有極大的影響。在《左傳》中會找到許多類似楚辭的短詩。至於《國語》、《戰國策》中一些賦、比、興手法的運用與行人說辭,也對楚辭與漢賦有着深遠的影響。后世選家們便有把二者中的一些篇目直接歸類到「騷」中去的。劉師培先生曾講道:「詩賦之學,亦出入行人之官。」「欲考詩賦之流別者,盍溯源於縱橫家哉。」而章炳麟先生則講道:《戰國策》「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為紛葩;期於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 「策」與「賦」之別,唯「有韻,無韻雲爾」。《國策》、《國語》中大多為說者行人之辭,駢辭儷句、渲染述賦通篇皆是。還有關於人類遠古及三代以降的傳說、史料、神話,中原文化與荊楚、吳越等南方區域文化的交流、整合等都為楚辭的產生提供了必然條件。這是從總體而言,先秦文化中的不同成分都在不同的側面為楚辭的形成提供着不同的底蘊。而楚辭的不同類型作品又分別吸收着不同的養料。
屈辭中的作品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天問》、 「二招」、{橘頌}大體上師祖《詩經》與古四言韻文;《九歌》基本上是楚調巫祭之歌,大體上直接發韌於楚地的各類民歌,並受先秦祭頌之作的影響;《卜居》、《漁父》皆為小賦,大體受了先秦諸子中「問對」類文章的影響;其余諸篇大多為不歌之詩,基本上源自於古之詩與歌,並吸收了古之謠諺、韻文、小賦的養料i宋玉的作品則師承屈辭。向「文人詩」的方向跨進了一大步。但在楚辭中,尤其是屈原的作品,對於先秦諸文化樣式中優秀成分的兼收並蓄,絕不是模仿或承襲,而是一種在前人和同時代、同區域文化基礎上的一種以超現實的想像力所進行的全新創造,這正是楚辭的藝術魅力與生命力之所在。你只能說在先秦各種文學體式中找到它的底蘊,你卻很難說它像哪一種。可是,在屈原以后的作品中,你不僅到處可以看到屈辭中的語言、詞匯、文體、手法的痕跡,甚至可以直接在屈原作品中找到它們的師祖篇目及形式。所以,到了魏晉以后,仍有「一世之士,皆祖屈原」之說。 諸如:《天問》篇在后世形成了一種「天問體」詩賦;《遠游》篇在后世形成了一種「游仙體」詩賦; 《橘頌》篇在后世形成了詠物抒情類的詩賦;「二湘」、《山鬼》在后世則影響到許多言情懷人詩賦;《國殤》、「二招」則影響到后世的廟堂文學、祭悼、戰爭類詩賦和誄文、墓志銘的風格;《哀郢》、《抽思》實為后世去國懷鄉作品之鼻祖;《涉江》、《湘夫人》、《悲回風》則「皆開后世詩文寫景法門,先秦絕無僅有」 (錢鍾書語);《離騷》與《九章》中的一些篇目則開了后世之自傳體詩作與哀怨自傷文學作品的先河; 《卜居》、 《漁父》與《招魂》流變為后世之賦文。而屈原與宋玉作品中的艾怨自傷成分,則作為一種傳統直接影響、流變為漢及以后的騷體詩賦,尤其是對漢代的影響更為直接和深刻。
楚辭對后世文學在方方面面的影響,尤其是對古詩深遠的革命式之影響,古今楚辭學者們多已盡論。不僅在五、七言詩方面肇開先河,而且在藝術手法上對古典文學具有廣泛深刻的影響。我們不能不承認,楚辭自漢以降,漸趨式微,但楚辭的直接流脈,至今仍清晰可見,概言之,大體有二:其一,直接衍變為各類騷體詩;其二,直接化生為騷體賦。尤以騷體詩流延最為綿長,入兩漢、越魏晉、跨唐宋、逾明清而至近現代。二者與楚辭形成了明顯的騷體文學體系主干。楚辭之所以后世漸為不顯者,概因文學品種、門類、數量與日倍增,楚辭流脈作品皆散於其中。歷代選家至多把騷體作品列為一類而已。宋朱熹輯有《楚辭后語》50余首,實集后世騷體文學之作不及滄海一栗;而宋人晁補之先此所輯《續楚辭》、《變離騷》兩集156篇作品,版本早巳失傳於世,不得復見。明清的紹騷作品集不少,但成規模的,只有清代廖元度先生的《楚風補》。雖此,仍足以說明一直到有宋,楚辭流脈仍舊綿延不息。直到元、明、清乃至現當代,治楚辭者之眾遠愈此前,而擬作直到明清亦從不曾有絕。
楚辭從一誕生開始,就是一種「文人文學」,並不擁有大眾讀者,但凡經典文化不得以實用之斗筲而一概量之。而后世之仿作,雖續貂者居多,然無之亦無可窺全豹,故亦不可作蛇足觀而棄之。無其流而不見江河之壯美,棄其源而江河無以流;無枝葉而不成其林木,無根本而枝葉無所依。故此,作者對歷年披閱典籍之所得資料進行編譯整理,輯而為《楚辭源流選集》五卷:其一,屈原作品輯為《楚辭魂》為全書之核心,故列於首;其二, 由屈宋而上溯相關詩文輯為《楚辭源》,試尋楚辭與騷體詩賦之淵源;其三, 自漢以降之歷代騷體詩輯為《楚辭流》;其四, 自漢以降騷體賦輯為《楚辭余》,兩卷所輯皆為楚辭之衍變與流脈,而分稱「流」、「余」乃為別詩、賦;其五,古今歷代名家學者的楚辭文論詩贊輯為《楚辭論》, 以加深對楚辭源流的理性認知。全書共收入作品2000余篇,並配有近500幅珍貴的圖片。盡管所輯也仍不過是騷體文學、楚辭文論中的九牛一毛,盡管在所選篇目、分類編次上都會存在諸多不足與舛謬,但該書的出版,相信自有其價值, 當會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與楚辭學的發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003年是屈原逝世二千二百八十年,也是他榮獲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殊榮六十周年的紀念年份。此書的出版也當是對紀念我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一份芹獻。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