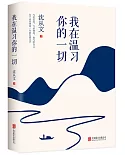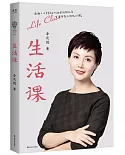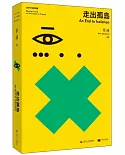本書系著名學者李歐梵先生最新散文集,分為「浪漫之余」、「讀書的心路歷程」、「布拉格心影」、「愛樂·電影·懷舊「四個部分,本稱為「浪漫的反叛,摩登的華麗」,是一本非常耐讀的文集。
浪漫的反叛,摩登的華麗。歐梵先生的這些文字,看似平淡,還帶點調炯和自嘲,內里卻有一個身處現代--後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博大深沉的人文關懷。在廣泛的閱讀、聆聽、游覽和思考中,歐梵先生縱情介入,展示文筆,飛揚機智,批評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眾多文化現象,不媚俗,不因循,不斷吸收新知,不斷審視自己,獨到的學術見解與鮮明的個人風格得到了巧妙地融合。
目錄
序
一、浪漫之余
康橋踏尋徐志摩的蹤徑
徐志摩的朋友
美國的「中國城」
——唐人街隨筆
父親的日記
重游康橋小記
人間四月「殘酷」天
——重讀《愛眉小札》
爛漫余情人似玉
二、讀書的心路歷程
心路歷程上的三本書
重訪「荒原」
有情的頑石:保羅·安格爾的詩
變形記
重讀卡夫卡札記
在香港教卡夫卡
文學解藥?
——在香港重讀卡繆的《瘟疫》
紀念薩依德
韓南教授的治學和為人
三、布拉格心影
哈維爾《給奧爾嘉的信》
「東歐政治」陰影下現代人的「寶鑒」
——簡介昆德拉的《笑忘書》
昆德拉的「弦樂四重奏」: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布拉格一日
——歐游心影
重游布拉格札記
今天在布拉格
布拉格的明信片
——續也斯同名作
四、音樂·電影·懷舊
音樂的遐思
聽芝加哥交響樂團
聽《大地之歌》
《九月》,夏日的遐思
「愛之喜」·「愛之悲」
——悼念父親李永剛先生
追憶馬里奧蘭莎
這樣的武俠片要不得
杜魯福和《蛇蠍夜合花》
人生難以承受的輕
——重看杜魯福電影雜憶
不了情:張愛玲和電影
憶金銓
——他的遺憾
跋語
附錄一:我的丈夫李歐梵
附錄二:浪漫的反叛,摩登的華麗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榮譽博士李歐梵贊辭
一、浪漫之余
康橋踏尋徐志摩的蹤徑
徐志摩的朋友
美國的「中國城」
——唐人街隨筆
父親的日記
重游康橋小記
人間四月「殘酷」天
——重讀《愛眉小札》
爛漫余情人似玉
二、讀書的心路歷程
心路歷程上的三本書
重訪「荒原」
有情的頑石:保羅·安格爾的詩
變形記
重讀卡夫卡札記
在香港教卡夫卡
文學解藥?
——在香港重讀卡繆的《瘟疫》
紀念薩依德
韓南教授的治學和為人
三、布拉格心影
哈維爾《給奧爾嘉的信》
「東歐政治」陰影下現代人的「寶鑒」
——簡介昆德拉的《笑忘書》
昆德拉的「弦樂四重奏」: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布拉格一日
——歐游心影
重游布拉格札記
今天在布拉格
布拉格的明信片
——續也斯同名作
四、音樂·電影·懷舊
音樂的遐思
聽芝加哥交響樂團
聽《大地之歌》
《九月》,夏日的遐思
「愛之喜」·「愛之悲」
——悼念父親李永剛先生
追憶馬里奧蘭莎
這樣的武俠片要不得
杜魯福和《蛇蠍夜合花》
人生難以承受的輕
——重看杜魯福電影雜憶
不了情:張愛玲和電影
憶金銓
——他的遺憾
跋語
附錄一:我的丈夫李歐梵
附錄二:浪漫的反叛,摩登的華麗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榮譽博士李歐梵贊辭
序
李歐梵去年提前自哈佛大學退休,決定今後大部分時間以香港為家。這個決定並不突然,因為他曾在多篇文章中透露過,他對香港情感深厚,早已把自己看作半個香港人,他亦因此覺得至少有一半的資格給香港人作逆耳之言。不同身份的人,對一個地方的觀感,真的大異其趣。1985年阿城第一次過訪香港,在《閑話閑說》中寫下了這幾句話:「當下就喜歡,就是喜歡里面世俗的自為與熱鬧強旺。……香港人好鮮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貪言中華文化,正是唐代式的健朗」。
事隔二十年,今天阿城再來香港,觀感如何,自然無法臆猜,但最少當年他喜歡的世俗香港面貌,還是風姿依然。他所稱道的「唐代式的健朗」,在我看來有幾分接近李歐梵在《今朝有酒今朝醉》所言的「動感」。動感是沖刺力,欣欣向榮的跡象,可惜在他看來香港社會缺乏一種「堅持理想的執著」去支撐,因此動得快,散得也快。
港人「唔好執輸、拼搏到盡」的表現,看在阿城眼里,竟是大唐一代的風貌,而在李歐梵看來,這正是「急功近利」的症候。兩位「英雄」所見不同,因為身份有異。「半個香港人」的自覺使李歐梵對香港的風風雨雨有貼身的感受。他從前是過客,現在是concerned citizen。正因香港社會短視,急功近利,他的「唐吉訶德式」的傻勁才可以發揮出來。他在《文學解藥?——在香港重讀卡繆(Albert Camus)的(瘟疫)》一文提到,在非典型肺炎蔓延期間,他用了卡繆這本名著作教本,意在讓香港青年感受一下貫穿全書有關「人心存在」和「內省、勇氣和行動」給我們的啟示。
文學是否可以充「解藥」?我想李歐梵自己也沒有答案。戴天認為他這種「浪漫』』想法,簡直與對牛彈琴無異,因為「大多數香港人根本不看書,即使看亦以工具書、『心靈雞湯』之類與瓊瑤、亦舒的言情小說為主,而不少人對書的概念,更只限於各種連環圖」。
李歐梵盡管浪漫,也應該明白戴天所說的是實話。生性浪漫的人,拿他自己的話來說吧,是屬於「反抗型的人物」。他認為即使大多數香港人不愛讀書,但也應該還有「少數人要讀書,而且還要讀相當難讀的文學經典」。於是「反抗」成性的李教授覺得義不容辭,認為這時「不拔刀相助,是否有愧職守」?
「浪漫」一詞,乍聽容易以為是從romantic翻譯過來的,其實中文早有此意。「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游」,語出蘇軾。以此語境引申,「浪漫」相當於「任意」、「自由自在」、「灑脫」和「無拘無束」。西方的浪漫主義是十八世紀在歐洲興起的思潮,在文學、藝術和哲學等范疇上對新古典主義層層的制約作出反抗。浪漫精神強調感情自然流露,偏愛想象力活潑新奇。浪漫主義者談情說愛,因此也比古典主義者轟轟烈烈,多彩多姿。
李歐梵一輩子跟浪漫主義結了不解緣,端的是人如其名。「歐」是風情萬種的歐洲。「梵」依辭典的解釋,泛指印度一般事物,「常冠以梵字,以示與中華有別」。依國人世俗眼光看,一個兼有哈佛大學教授和中研院院士頭餃的學者,應讓人有望之巍巍然的感覺,覺得這樣才配合形象和身份。但在這方面我們的李教授確顯得「與中華有別」。他不吃這一套。他不羞於在人前流露真性情,包括被新婚夫人呵癢時倒在地上哈哈大笑。
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歐梵是台灣新竹中學的初中生。年紀雖小,情竇卻開得繽紛燦爛。其時馬里奧蘭莎(Mario Lanza)在幕後配音的影片《學生王子》在國民大戲院上映。歐梵冒了逃課被記大過之險,跑去看了六次。這一段前塵舊事他在《追憶馬里奧蘭莎》一文有分教:「當他唱出第一句歌詞的時候,我不禁心花怒放,差一點從座位上站起來隨著他唱:『夏天在海德堡,處處是美景,年輕女郎花枝招展……』,接著是那首膾炙人口的『飲酒歌』——飲、飲、飲!我心情異樣地振奮,真的是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忘我境界!」
多年以後,當年的初中生華發漸生,但激情未減。2003年的春節,他在家請客,飯後放上一張馬里奧蘭莎的唱碟,把音量調得震天價響,李教授也隨著歌聲唱和,慢慢覺得「自己眼眶濕了,於是更加瘋狂地指揮起來,全身抖動,如入無人之境」。
這種奔騰情感的傾瀉,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正是英國浪漫詩人華茲華斯(Williarn Wordsworth,1770—1850)拿來凸顯浪漫精神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特征。浪漫的人感情豐富,因此特別容易泄氣。幸好他們對人生憧憬不絕,一個希望落空了,新的接上來,及時堵住犬儒思想之蔓延。歐梵這兩年在香港充當唐吉訶德,夠累了,這可從他最近在《明報月刊》發表的文章《在廢墟中打滾》看出來。可幸他對香港這「廢墟」仍有憧憬,不然他不會向我們宣誓:「我仍然願意住在這個城市,作背水一戰。因為我覺得香港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十分豐厚。」
果然不錯。「老兵不死」,浪漫的老兵更不會fade away。香港有幸留得住這個唐吉訶德。
事隔二十年,今天阿城再來香港,觀感如何,自然無法臆猜,但最少當年他喜歡的世俗香港面貌,還是風姿依然。他所稱道的「唐代式的健朗」,在我看來有幾分接近李歐梵在《今朝有酒今朝醉》所言的「動感」。動感是沖刺力,欣欣向榮的跡象,可惜在他看來香港社會缺乏一種「堅持理想的執著」去支撐,因此動得快,散得也快。
港人「唔好執輸、拼搏到盡」的表現,看在阿城眼里,竟是大唐一代的風貌,而在李歐梵看來,這正是「急功近利」的症候。兩位「英雄」所見不同,因為身份有異。「半個香港人」的自覺使李歐梵對香港的風風雨雨有貼身的感受。他從前是過客,現在是concerned citizen。正因香港社會短視,急功近利,他的「唐吉訶德式」的傻勁才可以發揮出來。他在《文學解藥?——在香港重讀卡繆(Albert Camus)的(瘟疫)》一文提到,在非典型肺炎蔓延期間,他用了卡繆這本名著作教本,意在讓香港青年感受一下貫穿全書有關「人心存在」和「內省、勇氣和行動」給我們的啟示。
文學是否可以充「解藥」?我想李歐梵自己也沒有答案。戴天認為他這種「浪漫』』想法,簡直與對牛彈琴無異,因為「大多數香港人根本不看書,即使看亦以工具書、『心靈雞湯』之類與瓊瑤、亦舒的言情小說為主,而不少人對書的概念,更只限於各種連環圖」。
李歐梵盡管浪漫,也應該明白戴天所說的是實話。生性浪漫的人,拿他自己的話來說吧,是屬於「反抗型的人物」。他認為即使大多數香港人不愛讀書,但也應該還有「少數人要讀書,而且還要讀相當難讀的文學經典」。於是「反抗」成性的李教授覺得義不容辭,認為這時「不拔刀相助,是否有愧職守」?
「浪漫」一詞,乍聽容易以為是從romantic翻譯過來的,其實中文早有此意。「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游」,語出蘇軾。以此語境引申,「浪漫」相當於「任意」、「自由自在」、「灑脫」和「無拘無束」。西方的浪漫主義是十八世紀在歐洲興起的思潮,在文學、藝術和哲學等范疇上對新古典主義層層的制約作出反抗。浪漫精神強調感情自然流露,偏愛想象力活潑新奇。浪漫主義者談情說愛,因此也比古典主義者轟轟烈烈,多彩多姿。
李歐梵一輩子跟浪漫主義結了不解緣,端的是人如其名。「歐」是風情萬種的歐洲。「梵」依辭典的解釋,泛指印度一般事物,「常冠以梵字,以示與中華有別」。依國人世俗眼光看,一個兼有哈佛大學教授和中研院院士頭餃的學者,應讓人有望之巍巍然的感覺,覺得這樣才配合形象和身份。但在這方面我們的李教授確顯得「與中華有別」。他不吃這一套。他不羞於在人前流露真性情,包括被新婚夫人呵癢時倒在地上哈哈大笑。
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歐梵是台灣新竹中學的初中生。年紀雖小,情竇卻開得繽紛燦爛。其時馬里奧蘭莎(Mario Lanza)在幕後配音的影片《學生王子》在國民大戲院上映。歐梵冒了逃課被記大過之險,跑去看了六次。這一段前塵舊事他在《追憶馬里奧蘭莎》一文有分教:「當他唱出第一句歌詞的時候,我不禁心花怒放,差一點從座位上站起來隨著他唱:『夏天在海德堡,處處是美景,年輕女郎花枝招展……』,接著是那首膾炙人口的『飲酒歌』——飲、飲、飲!我心情異樣地振奮,真的是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忘我境界!」
多年以後,當年的初中生華發漸生,但激情未減。2003年的春節,他在家請客,飯後放上一張馬里奧蘭莎的唱碟,把音量調得震天價響,李教授也隨著歌聲唱和,慢慢覺得「自己眼眶濕了,於是更加瘋狂地指揮起來,全身抖動,如入無人之境」。
這種奔騰情感的傾瀉,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正是英國浪漫詩人華茲華斯(Williarn Wordsworth,1770—1850)拿來凸顯浪漫精神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特征。浪漫的人感情豐富,因此特別容易泄氣。幸好他們對人生憧憬不絕,一個希望落空了,新的接上來,及時堵住犬儒思想之蔓延。歐梵這兩年在香港充當唐吉訶德,夠累了,這可從他最近在《明報月刊》發表的文章《在廢墟中打滾》看出來。可幸他對香港這「廢墟」仍有憧憬,不然他不會向我們宣誓:「我仍然願意住在這個城市,作背水一戰。因為我覺得香港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十分豐厚。」
果然不錯。「老兵不死」,浪漫的老兵更不會fade away。香港有幸留得住這個唐吉訶德。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