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大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面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世說新語》
抄書一段,有點像寫這些東西的意思。原本只一條兩條,過兩天又一條兩條,日子稍長,成了幾十條的數目。有天鄒荻帆兄來坐,為詩刊索詩。詩倒沒有,把這幾十條拿去了,也發表了出來,而且給起了這個怪題目。
後來他們大概覺得這不是詩吧?我自己也明白這當然不是詩,雖原來不是為詩刊而寫的,倒似乎是真的一下子停住了。
有熟人和生人來信問為什麽不寫了,細想自己又不是正經寫書的,便這樣的回答各們:大概是因為沒有興致了吧?......
-

唐宋館驛與文學
$465 -

聊齋的狐鬼世界
$261 -

文學思想研究與文學語言觀透視
$298 -

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論叢(第一輯)
$355 -

宋代文學論考
$459 -

這樣寫出好故事:描寫與背景
$199 -

朗誦中國
$396 -

己亥:余世存讀龔自珍
$35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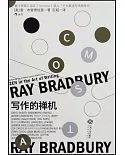
寫作的禪機
$18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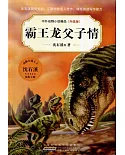
霸王龍父子情
$115 -

樂死人的文學史(魏晉篇)
$198 -

小泉八雲精怪故事集
$355 -

敘事的虛構性:有關歷史、文學和理論的論文(1957-2007)
$418 -

圖話經典:羅馬諸神與帝國的故事
$355 -

元好問與中國詩歌傳統研究
$417 -

中外動物小說精品(升級版):荒野駿馬
$1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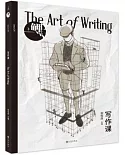
鯉·寫作課
$287 -

中國文學史(圖文版)
$208 -

中國文學思想讀本:原典·英譯·解說
$66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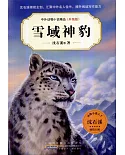
中外動物小說精品(升級版):雪域神豹
$115

